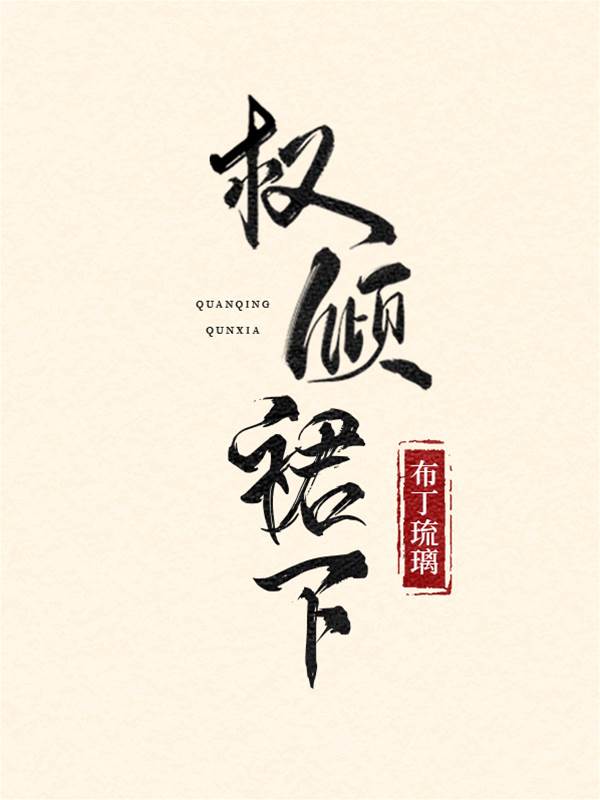《反派同窗他命帶錦鯉》 第7章
當今盛寵不衰的兵部尚書之,淳貴妃。膝下只有一個兒子,便是七殿下。
也是書中的男主角,程宵。
更是池京禧恨之骨的敵。
小炮灰跟他有嗎?答案是有的。
自小養在貴妃邊的程宵子開朗,風流意氣,當初在書院見小炮灰凍得快要暈過去,便了惻之心,將大氅給了。
自那以后,小炮灰便傾心于程宵,一直到蹲進大牢,仍對程宵癡心不改。
先前小炮灰為了跟程宵走得近一些,主做了不事惹人笑話,且被人議論說是想攀附七皇子。
因為此事,小炮灰了很多欺負,就連學院有名的夫子也親自來敲打。
實際上小炮灰跟程宵沒什麼關系,程宵幫不過是因為他心腸好。但他卻并沒有把一個商人之子放在心上。
聞硯桐思來想去,覺得這個問題不能表現得那麼謹慎,于是便故作隨意道,“七殿下份非凡,怎會同小民有。”
池京禧聽后也沒什麼反應,只是眼眸中蓄起了迷蒙的霧,讓人覺得高深莫測。
這人最可怕的就是這一點。他心思很多,腦子也很聰明,只不過平日里不愿意計較那麼多,所以總有人傳聞小侯爺位高權重,卻魯莽無腦。
但池京禧能為書中最大的反派且跟程宵對峙到了最后,靠得不僅僅是手頭上的權利和莽夫一樣的沖勁。
聞硯桐越發覺得馬車里的危險,決定主出擊,跟邊的憨憨搭話。
“牧爺是將軍府長大的,平應當很厲害吧。”
牧楊愣了一下之后,頗有些不好意思的撓撓頭,“我六歲便開始練弓,但是沒什麼天賦,所以平也并不出眾。”
“果真是虎父無犬子,牧爺真厲害。”聞硯桐真心夸道。
“我昨日去學院補了武測,三箭沒有一箭中靶心……”他抬眼看了看聞硯桐,“聽說你有一箭中了靶心,不妨說說你平日是如何練習的。”
聞硯桐聽后了脖子,打著哈哈道,“牧爺說笑了,平日連書都讀不完,哪還會練習平,那日我不過是湊巧而已,湊巧而已。”
牧楊十分失,反手把藥包給了,“那你還上來做什麼,一問三不知半點用都沒有,趕下去吧。”
聞硯桐抱著藥包愣了一下,而后當即站起來,轉要走,但卻被程昕攔了下來,“馬車尚在路上,你莫要,仔細跌倒。”
又悻悻的坐回去,看來這五皇子是鐵了心要把送到書院門口了。
好在剩下的路程車上的人都沒有在為難,直到馬車停在頌海書院大門之,程昕才客套了一句,讓下車小心。
聞硯桐提著的心終于放回肚子里,沖車上的三位爺道了謝之后,才進了書院。
回去的路上,一直琢磨著池京禧的態度。
現在的他應當還沒喜歡上主角,自然也不是程宵的敵,所以對程宵的敵意并沒有那麼深。
而且池京禧能同意上馬車,也就說明他對“聞硯桐”這個同窗沒什麼厭惡。
總的來說,目前的況還算是穩定,只要計劃順利,過不久便可以離開頌海學院,回到長安做聞家千金了。
聞硯桐提著一包藥興顛顛的回了寢房,就見同寢的張介然在背書。
聞硯桐的這個室友子很向,以前小炮灰害怕自己的被發現,跟同寢的張介然很說話,有幾回張介然主示好想與拉進關系,都被小炮灰兇走了。
雖然小炮灰是為了保護自己的,但對張介然來說可太委屈了,還因為不好關系哭了幾回。
聞硯桐穿越過來之后倒沒那麼在意,主跟張介然說了好幾次話,兩人的關系才慢慢溫熱起來。
湊上前笑嘻嘻道,“張介然,我記得你家也是長安的,對吧?”
張介然把頭從書中抬起來,有些靦腆的點點頭。
“那你平日回家坐的是誰家的馬車呢?”聞硯桐假裝用嘮嗑的語氣說道。
“自己家的。”張介然答道。
聞硯桐哦了一聲,這才想起來張介然也是個富二代來著。
道,“那朝歌城有沒有什麼馬車出行穩妥的?”
“我聽聞途安馬行倒是不錯。”張介然愣了一下,道,“這才開學,你就要回家嗎?”
“哪能啊。”聞硯桐笑著說,“是我有一遠方親戚想去長安,托我給他們尋馬車呢。”
張介然沒多想便信了,點頭道,“途安馬行是需要提前預定的。”
“啊,還需要預定?”聞硯桐驚詫,連朝歌都路都不準,怎麼找去途安馬行?
許是看出了聞硯桐的難,張介然道,“正巧我明日出去一趟,便順路給你預定上吧,你那遠方親戚什麼時候出發?”
聞硯桐驚喜道,“越快越好,那就麻煩你了。”
張介然有些臉紅的頷首,“我們都是同窗,幫些小忙也是應該的。”
“沒錯,日后你有什麼難我定然也不會坐視不管。”聞硯桐微笑道。
哼著小曲兒拎著藥包去膳堂,瞧見里面只有一個約四五十歲的婦人,便甜了幾句,向借用膳房的灶臺煎藥。
誰知那婦人見聞硯桐瘦瘦小小,想起了自己在外念書的孫子,不由覺得心。接了聞硯桐的藥包攬了煎藥的活,還讓回去睡著,待藥煎好之后給送去。
幸福來得太突然,砸蒙了聞硯桐。
有些不大好意思的推辭了幾番,但婦人十分堅持,甚至抹著眼淚說起了自己的孫子,聞硯桐于心不忍只好應答。
回到寢房睡覺去了。
躺進被窩的時候還咂琢磨:這幾日的運氣是不是太好了?
藥只煎了兩刻鐘,聞硯桐都還沒來得及閉眼。
婦人十分心,把藥倒進碗里等著溫熱了才端來。
聞硯桐看見這碗黑乎乎的藥時,就知道這個書院里又多了一個傷心的人。
被中藥的氣味沖得兩眼一黑,接過碗的手都抖起來。
婦人見了之后慈的笑道,“著鼻子一口氣喝完,就不覺得苦了。”
聞硯桐想著自己好歹也是二十好幾的人了,怎麼可能會被這點苦難打到?于是二話不說住鼻頭往里灌藥。
苦味口的一剎那,才意識到自己低估了中藥的威力,險些反嘔。
幸好憑借著年人強大的自制力,著頭皮把中藥喝完,苦得眉眼睛都皺了一坨。
婦人便塞了一塊餞到里,多緩解了些。聞硯桐對婦人激不盡,拿出了袖子里裝的兩塊銀子,放在婦人手中。
雖然婦人起初拒絕,但聞硯桐相當堅持,并且擺幫忙煎往后兩日的藥,婦人才勉強收下。
聞硯桐告別婦人,喝了藥之后便躺進被窩里繼續睡,一覺睡到第二日清晨,頭也不痛了,鼻子也通順了。
而且連帶著后窩也覺不到疼了。
聞硯桐舒舒服服的了個懶腰,就連公的打鳴也覺不那麼討厭了。
日子仿佛在一日一日的變好。
只是讓沒想到的是,真正倒霉的事馬上就要來了。
猜你喜歡
-
完結90 章
若春和景明
那時的他高高在上,不可碰觸;她狼狽尷尬,一無所有。在努力,也是命數,讓她看見他的夢,夢中有她的未來。跨越傲慢和偏見,他們做下一個約定——“有生之年,我一定要看到新的時代和紀年。我要看到海上最高的浪潮!哪怕窮盡一生,也決不放棄!”“好啊,我陪你一起!”他們腳下,車之河流海浪般顛簸流淌。而他們頭頂,星空亙古浩瀚,見證著一切。那一年,尚年少,多好,人生剛開始,一切皆能及,未來猶可追。
31.3萬字8.18 6145 -
完結95 章

過野
巷子吹進了末冬的冷風,一墻之隔,林初聽到幾個男生在拿她打賭—— “執哥,能跟她談滿兩個月不分就算贏。” 幾天后,他頭流著血跟她擦肩而過 她踏進巷子向他伸出了手,“請問,你身體有什麼不適嗎?” 又幾天,游戲場所外,他喊住她。 “喂,做我女朋友怎麼樣?” 林初考慮了幾天。 4月9號,她應了他。 6月9號,高考結束。 兩個月,是他的賭,亦是她的賭。 在林初心里,陳執想做的事會想法設法做到,隨心所欲,卻心思縝密。 所以,她步步為營,卻沒料到他毫不防備。 “過了這個野,你就是勝者。” *彼此救贖
26.9萬字8 7197 -
完結1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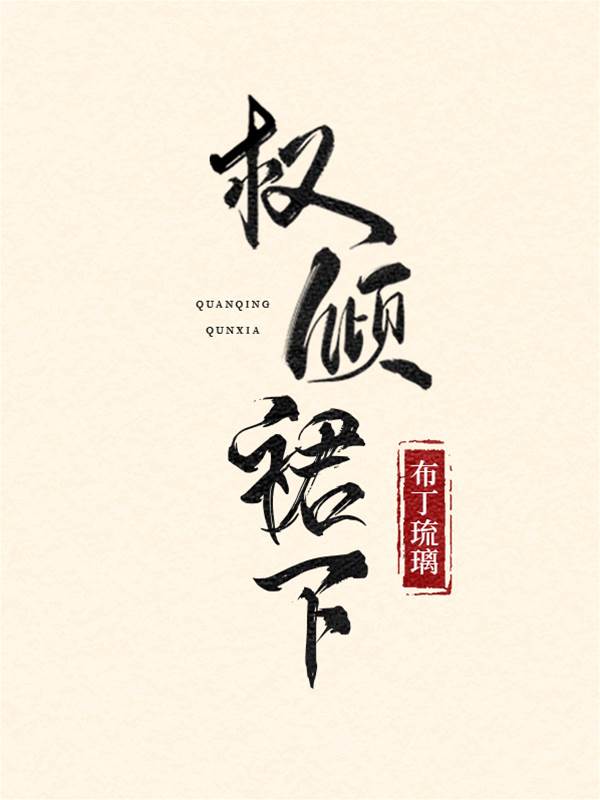
權傾裙下
太子死了,大玄朝絕了後。叛軍兵臨城下。為了穩住局勢,查清孿生兄長的死因,長風公主趙嫣不得不換上男裝,扮起了迎風咯血的東宮太子。入東宮的那夜,皇后萬般叮囑:“肅王身為本朝唯一一位異姓王,把控朝野多年、擁兵自重,其狼子野心,不可不防!”聽得趙嫣將馬甲捂了又捂,日日如履薄冰。直到某日,趙嫣遭人暗算。醒來後一片荒唐,而那位權傾天下的肅王殿下,正披髮散衣在側,俊美微挑的眼睛慵懶而又危險。完了!趙嫣腦子一片空白,轉身就跑。下一刻,衣帶被勾住。肅王嗤了聲,嗓音染上不悅:“這就跑,不好吧?”“小太子”墨髮披散,白著臉磕巴道:“我……我去閱奏摺。”“好啊。”男人不急不緩地勾著她的髮絲,低啞道,“殿下閱奏摺,臣閱殿下。” 世人皆道天生反骨、桀驁不馴的肅王殿下轉了性,不搞事不造反,卻迷上了輔佐太子。日日留宿東宮不說,還與太子同榻抵足而眠。誰料一朝事發,東宮太子竟然是女兒身,女扮男裝為禍朝綱。滿朝嘩然,眾人皆猜想肅王會抓住這個機會,推翻帝權取而代之。卻不料朝堂問審,一身玄黑大氅的肅王當著文武百官的面俯身垂首,伸臂搭住少女纖細的指尖。“別怕,朝前走。”他嗓音肅殺而又可靠,淡淡道,“人若妄議,臣便殺了那人;天若阻攔,臣便反了這天。”
52.5萬字8 21919 -
完結98 章

偏執寵愛
1 軍隊裡大家都知道,他們的陸隊長背上有一處誇張濃烈的紋身。 像一幅畫,用最濃重的色彩與最明媚的筆觸畫下一枝櫻桃藤蔓。 有援疆女醫生偷偷問他:「這處紋身是否是紀念一個人?」 陸舟神色寡淡,撚滅了煙:「沒有。」 我的愛沉重、自私、黑暗、絕望,而我愛你。 「我多想把你關在不見天日的房間,多想把你心臟上屬於別人的部分都一點一點挖出來,多想糾纏不清,多想一次次佔有你,想聽到你的哭喊,看到你的恐懼,看到你的屈服。 ——陸舟日記 2 沈亦歡長大後還記得16歲那年軍訓,毒辣的太陽,冰鎮的西瓜,和那個格外清純的男生。 人人都說陸舟高冷,疏離,自持禁欲,從來沒見到他對哪個女生笑過 後來大家都聽說那個全校有名的沈亦歡在追陸舟,可陸舟始終對她愛搭不理。 只有沈亦歡知道 那天晚自習學校斷電,大家歡呼著放學時,她被拉進一個黑僻的樓道。 陸舟抵著她,喘著氣,難以自控地吻她唇。
32.1萬字8 954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