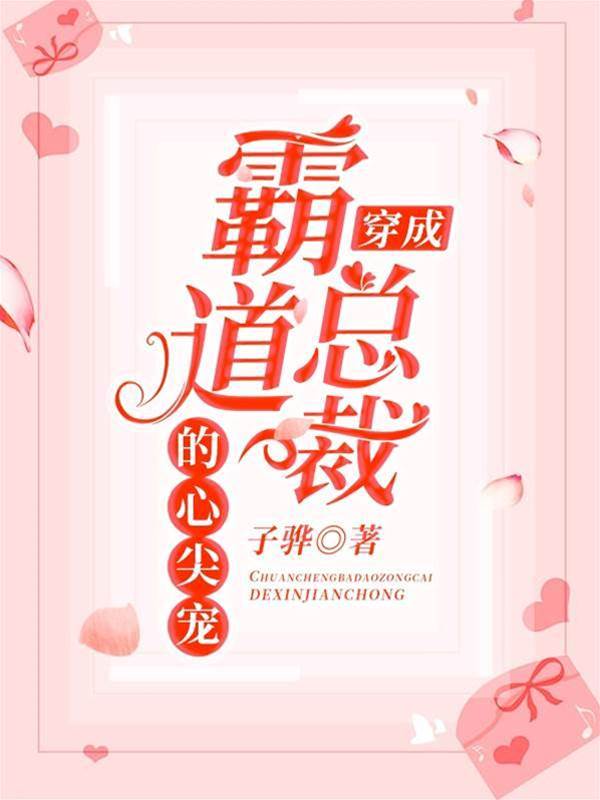《大唐明月》 第26章 天煞孤星 春江花月
房間裡的蠟燭早已經熄滅了。沒有月亮的時候,長安的夜晚是一片真正的漆黑,琉璃即使睜大了雙眼,也只能看見一個窗子的廓。遠遠的似乎有梆梆的打更聲傳來,一下,兩下,三下,應該是三更時分了,卻一點睡意都沒有。
其實琉璃並沒有失眠的習慣,尤其是到了安家之後,在這張舒適的廂式雕花牀上,的睡眠一直很好,只是今天白天聽到的那三個字,實在有些太過震撼,而史掌櫃後來說的話,又太過離奇,那背後似乎有些什麼東西,讓想不明白。
按照史掌櫃的說法,裴行儉這個名字如今在大唐的員和世家中幾乎是無人不曉,他都曾在與客人的管家們閒聊時聽到過兩三次。但究其原因,既不是他的書法,也不是他的智謀,而是四個莫名其妙的字:“天煞孤星”。
至於這四個字的由來,前面半截琉璃是大致知道的:裴行儉出裴嫡支,父親是聲名卓著的一代名臣,兄長是萬人莫敵的一代名將,裴家因世代鎮守,自然就投了當時在稱帝的王世充麾下。裴氏父子在**深固,威又高,頗王世充猜忌排,便謀投奔故李淵,不料慘遭出賣。王世充一怒之下屠了裴氏三族,而裴行儉就是這個大家族裡唯一倖存的腹子。
至於故事的後半截,還是第一次聽說,裴行儉十五歲喪母,十八歲從大唐頭號貴族學院弘文館舉明經出仕,當年便娶了兵部陸侍郎的兒,結果第二年長子夭折,過了兩年,陸氏又因難產去世,一兩命。自此之後,他便被認定是大唐頭號天煞孤星——全家,乃至全族都被他剋死了,難道還有比他命更的人麼?
想到這種荒誕卻廣爲流傳的說法,想起那張總是溫和而略帶疏離的臉,琉璃只覺得既困又不平:裴氏家族的事是世中的悲劇,怎麼能怪到一個還沒有出世的孩子上?至於人難產,孩子夭折,在這個時代是何等司空見慣的事,又怎麼了他是天煞孤星的鐵證?如今他並不是什麼大人,這個名聲怎麼會傳得如此路人皆知?單從史掌櫃那句“沒想到他竟是這樣一副和善的模樣”就可以想見他的名聲被傳到了何種地步!此外,在這個講究出的時代,他八九年前就已經以那樣正苗紅的方式出仕,爲什麼直到如今依然是個九品的員?
無數問題一個接一個的在琉璃腦海裡翻騰,在朦朧睡去之前,突然想起似乎在哪裡看到過一筆,裴行儉是有妻有子的,有一個兒子好像後來還當上了宰相。他並不是真的天煞孤星,而這世上原有一種人,是經霜雪而越加傲岸……舒了口氣,放心的睡了過去。
第二日一到畫室,琉璃便立刻找出了裴行儉上次留下的幾張字,左右端詳了半日,挑了兩張,讓小檀拿到相字畫店裡去簡單裝裱一番——裴行儉遲早會建功立業,他的字到時大概也能值點錢吧?就算不賣,留著做傳家寶也不錯。到老的時候,自己可以得意的跟孫子說,“你當年給皇陛下做過服,給高宗陛下畫過屏風,還讓裴大將軍寫過字……”這樣的人生,也很不錯啊!
還沒等琉璃YY完,門口響起了一陣腳步聲,門簾挑,出了武夫人笑盈盈的臉,進門便道,“唉,總算是有合用的屏風了!我這幾天可是一頓好找,最後還是母親那裡找到了一架金楠木的屏,真真是再難得不過的,足有五尺多高,邊框底座一木貫通的不說,雕工也極細,四面都是雕的蓮花捲草紋,我把尺寸都量好了,你來看看!”說著就從袖子裡拿出了一張紙箋。
琉璃看了一眼,上面記著是三尺九寸高,兩尺三寸五分寬,屏這樣算是尋常尺寸的。只聽武夫人問道,“若是要畫,幾日能得?”
琉璃想了想,覺得還是說得保守一些的好,“有個十幾天總是夠了。”
武夫人笑道,“那不是佛誕日之後就好?時間倒是富富有餘。你準備畫些什麼,又題些什麼字樣?”
琉璃心中早已有了腹稿:在這幅屏風裡,畫其實只是配角,重要的是詩,以及寫詩的那筆字。而想來想去,有印象的長詩也只有一首《春江花月夜》。上一世裡,臨摹過一副同題的水墨畫,也一筆一畫的臨摹了配畫的這首詩。琉璃雖然對詩歌不大冒,但那首長詩配上畫面的意境給留下的印象實在太爲深刻,以至於現在還能記下來十幾句,就算不到原詩的一半,想來也夠用了。如今的打算就是把這幅畫和這首詩都照搬過來——《春江花月夜》此時應當還未問世,約記得這首詩的來歷據說是有幾分不可靠的,倒是正好。
琉璃笑著把自己的想法大略說了一下,武夫人連連點頭,“春江花月夜,這名字就好,你說的那詩聽上去也好,原來的屏風裡面也是一幅畫,是閻立德畫的什麼《行獵圖》,十分無趣,我回去便拆了它!”
閻立德?初唐畫壇第一名家閻立本的哥哥……武夫人居然要拆了他的畫換上自己的,琉璃只覺得一滴冷汗落額角,力頓時大增。誰知武夫人看著,又笑了一笑,“倒是忘記說了,這幾日或許會有人來點名讓你畫花樣,你若爲難,只要把魏國夫人柳氏之事如實說了便好。”
琉璃的冷汗頓時便嚇幹了,怔怔的看著武夫人,這是什麼意思?
武夫人奇道,“你發什麼怔?想來問的人一多,那柳氏自然不好再難爲你。”
琉璃垂下眼簾,苦笑道,“此事不算什麼,怎好勞煩夫人掛心?琉璃能如今這般給夫人畫屏風就好,畫不畫花樣又有甚打?”這位武夫人也不知是真天真還是假天真,以柳夫人如今的權勢,自有一千種法子來收拾自己。若是讓以爲自己到訴苦,壞了的名聲,不定會招來怎樣的災禍!
武夫人搖頭笑道,“你總是這般謹慎!那柳氏最是橫蠻,人所皆知,你這樣的手藝,怎麼能就此埋沒了?我母親昨日請幾位夫人來家中做客時,特意讓們看了你做的那夾纈披帛,又提了提你,人人都說想讓你幫們也做兩條呢!我母親說,正要讓們都知道柳氏的所爲。”
琉璃低頭盯著自己的袖子,就像上面突然多出了一個。現在明白了,眼前這武夫人是真的傻,這事還能直接告訴自己?難道看不出來,這是母親揚老太在給柳夫人使絆子?而琉璃就是負重任的……那塊西瓜皮,就算摔不著柳夫人也能噁心一下。這些貴婦自然樂得看熱鬧,只是,有人想過西瓜皮的下場沒有?在心裡嘆了口氣,擡頭笑道,“楊老夫人真是熱心腸,琉璃多謝了。只是要畫這屏的畫卻極要靜心,明日起,琉璃就會在家閉門作畫,便是沒有魏國夫人的事,那些夫人也只怕要過些日子纔有閒能接待。”
武夫人點頭道,“這倒也是。”並不太明白母親的那些彎彎心思,在心裡,自然這屏風纔是第一等要之事,聽琉璃說得如此鄭重,倒多了幾分歡喜。
琉璃忙又問,“依夫人所見,這畫是上的好,還是水墨的好?”
武夫人果然便拋開了那些思緒,皺著眉頭思索了半日才道,“我是喜歡上的畫,記得見過一幅青綠的山水,甚是好看,只是這屏風上若要配上詩賦,只怕還是水墨的更合適些?”
琉璃心裡鬆了口氣,只順著的意思又說了些屏風的構圖、風格,又厚著臉皮吹了一通這屏風畫會如何清雅絕倫——的畫也就罷了,但裴行儉的書法,《春江花月夜》的名句,難道是鬧著玩的?武夫人走時果然一臉夢幻,一個字也沒再提起柳夫人的事。
琉璃看著的背影,無聲的搖了搖頭,超齡這種人,原來哪個時空都有會!轉回到屋裡,小檀在一邊笑著問道,“大娘,今日那兩張字是誰寫的?今日書畫店的米掌櫃讚歎了半日呢!”
琉璃奇道,“你不知道麼?自然是那位裴九郎的。”
小檀滿臉都是訝然,“是那位天……”看見琉璃微沉的臉,忙捂住,把後面三個字嚥進了里。
琉璃嘆了口氣,昨天小檀聽說了裴行儉的事,就嘖嘖稱奇的把“天煞孤星”四個字掛在了邊,自己忍不住拉下臉來說了一句,現在倒是不說了,心裡顯然卻還是這樣想的。只是看著小檀捂著,眼珠骨碌碌轉的樣子,琉璃撐不住還是笑了起來,“罷了罷了,我不是怪你,你須知道,武夫人這屏風還指這位來幫著寫呢,待我畫好之後,說不定還要你去請人,若把這幾個字說溜了口,那可如何是好?”
小檀放下手,眼睛笑得彎彎的,“婢子再笨,當面怎會說出來?”
琉璃笑道,“是是是!小檀你伶牙俐齒,名震西市,如何會說錯話?”
兩人說笑了片刻,琉璃便開始磨墨,想把記憶裡的那幅《春江花月夜》勾出個大樣來,才了幾筆,史掌櫃卻匆匆的走了進來,皺眉道,“大娘,外面有位鍾娘子,指名道姓要見你,看那架勢,彷彿是家夫人。”
.多謝親的書友612134327投的PK票。
猜你喜歡
-
完結666 章

報告王爺,王妃出逃1001次
一朝穿越,要成為太子妃的葉芷蕓被大越的戰神當場搶親!傳聞這位戰神性情殘暴,不近女色!性情殘暴?不近女色?“王爺,王妃把您的軍符扔湖里了!”王爺頭也不抬:“派人多做幾個,讓王妃扔著玩。”“王爺,王妃要燒了太子府!”王爺興致盎然:“去幫王妃加把火。”“王爺!不好了,王妃要跟南清九王爺踏青!”王爺神色大變:“快備車,本王要同王妃一起迎接來使!”
96萬字8 251804 -
完結37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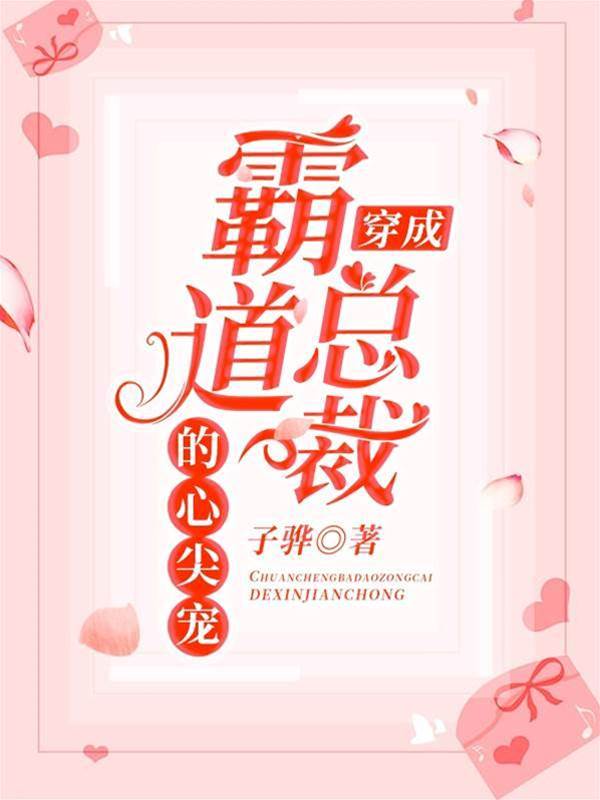
穿成霸道總裁的心尖寵
金尊玉貴的小公主一朝醒來發現自己穿越了? 身旁竟然躺著一個粗獷的野漢子?怎會被人捉奸在床? 丈夫英俊瀟灑,他怎會看得上這種胡子拉碴的臭男人? “老公,聽我解釋。” “離婚。” 程珍兒撲進男人的懷抱里,緊緊地環住他的腰,“老公,你這麼優秀,人家怎會看得上別人呢?” “老公,你的心跳得好快啊!” 男人一臉陰鷙,“離婚。” 此后,厲家那個懦弱成性、膽膽怯怯的少夫人不見了蹤影,變成了時而賣萌撒嬌時而任性善良的程珍兒。 冷若冰霜的霸道總裁好像變了一個人,不分場合的對她又摟又抱。 “老公,注意場合。” “不要!” 厲騰瀾送上深情一吻…
34.6萬字8 23507 -
完結2757 章

我家王妃很任性
鬼醫毒九一朝醒來,成了深崖底下被拋尸體的廢物,“哦?廢物?”她冷笑,丹爐開,金針出,服百藥,死人都能起死回生,這破病就不信治不了了。然而低頭一看,還是廢物。“……”…
499.8萬字8 40593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