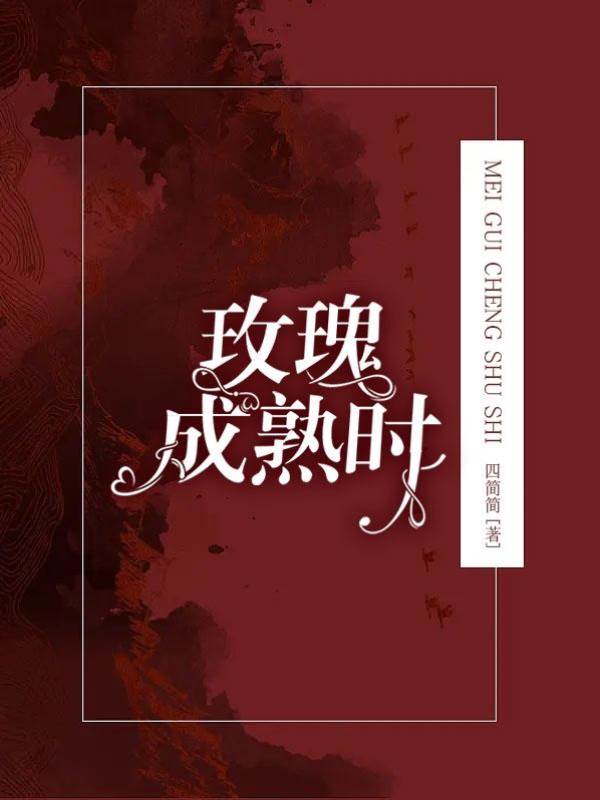《予我千秋》 第19章 壹拾玖
似笑非笑的神,使得的話聽上去半真半假。
戚炳靖臉不變地“嗯”了一聲,看不出是信了還是沒信,然后順著的話說下去:“做了王妃,再和我生幾個孩子。”
“幾個?”卓炎仍然將笑不笑的。
“三個也就夠了。”
戚炳靖倒還真的立刻給了一個回答,答前不曾思考一瞬,更像是隨著眼下的心而隨意調侃的玩笑話。
大抵是先前太耗力,卓炎此時不再多言,只是安靜地將他的目接住,挑了挑角,然后閉上眼,枕在他的肩窩睡了過去。
……
卓炎離開后,沈毓章沉下臉,鎖住眉頭,靜坐了很久都不發一言。
他的這副模樣掉英嘉央眼中,如彎刺一般勾著久遠卻仍舊悉的記憶。輕易地回想起上一次他如此怒不發的樣子。
那是景和九年,當時大平在北境接連打了幾場大勝仗,對于接下去該以何等策略對付大晉,朝中以裴穆清為首的主戰派與以王為首的主和派吵個不休,朝堂連續數日不得安寧。沈毓章的父親恰恰在廷議爭論最激烈的時候上表諫奏,力諍當議和、劃地、休戰,而由他父親代表沈氏所呈的這一封札子,對皇帝自然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皇帝最終下詔,令本乘勝向北進軍的大平北境軍暫止攻勢。詔令下達的當日,沈毓章自講武堂出來后沒有回沈府,而是來宮中請見一面。便陪著他,任他一言不發、臉黑沉、眉頭鎖地坐了整整半日,才聽他說了一句:我從軍。
須知沈氏文臣出,三百多年來鮮有人踐行伍之列。縱是他自時起便習兵略于講武堂,亦不過是循沈氏一貫培育子弟的舊例罷了,家中又有誰會真的想讓他上戰場。他口中的這四個字,是對父親政議的最直接的反抗,更是他決計疏遠親族的最早開端。
當時沒人想得到,沈毓章會在兩年后一舉登第武狀元、拜將出邊;更沒人想得到,大晉在用這兩年時間休養生息、厲兵秣馬后,會以洶洶之勢卷土重來,再犯大平北境。
而他那時的神,與眼下所目睹的,幾乎一模一樣。
不過那時的,尚可作為他忍重怒之下的一道藉,而今日的,對他而言又能是什麼?
在靜坐許久之后,沈毓章開口說話了。
他說得不快,因此更顯得語氣極冷:“你何必要來這一遭?”
這話是沖著英嘉央問的,但他看也不看一眼。
在短暫地停頓之后,他的語氣逐句加重:
“金峽關是個什麼態勢,你在京中難道一丁點不知道?兵部無能人可用了,求你來你就來?
“你既無意與我再敘舊事,那麼來了又有何用?又與其他任何一個人來有何分別?你以為拿著朝廷的那點誠意,你就能勸伏得了卓炎?勸伏得了我?
“皇室如今是什麼樣,何須我再多言?皇帝無心問政已是多年,王自封王后久不就封地,其野心昭然若揭。倘若你不來這一遭,云麟軍便會推立英氏宗親中最無勢力的端侯之子,再委忠懇之臣輔政,肅清朝中宵小,以制衡王一系。端侯封地偏遠且小,又是宗室旁系,新帝五年翻不出什麼大浪,足夠讓朝廷有時間收拾北境局。
“如今你將自己送到這關,卓炎扣住你不放,皇帝做什麼,能比立你之子更快讓他答應?不過才五歲大的孩子,何必要被卷這等事中來?”
說出最后一句話時,他幾乎不住火氣。
他明白卓炎所提議的確實是眼下的“上上之計”,他無法反駁,也不能反駁;他心中絕不希事態朝著這個方向發展繼續,但他卻又必須同意這樣去做。
這怒意歸結底,是他深覺自己虧欠了。他不止虧欠了,還更虧欠了二人的孩子。但他卻將對自己的火氣沖發了出來。
這樣的遷怒,鮮在他上發生。然而他竟然控制不住。
英嘉央一直靜靜地看著他,待他把話都說干凈了,才向他走近數步。
前近距離的人影帶來了些微的迫,沈毓章皺著眉抬眼,眼底墨黑中著紅斑。
英嘉央看著他說:“你問我何必要來這一遭,那麼我來告訴你。
“我想親眼看一看,令你不顧的、當初為了它寧可將我二人十余年的分一夕割斷的北境,究竟是個什麼模樣。這個理由夠不夠?
“六年前因我之故你未能戰沙場。五年前我沒能救得了你的恩師裴將軍。而今你不惜賭上沈氏一族而投叛軍,我將自己送到這關,就是為了將自己與你綁在一起,令朝中無人能論你之死罪、能議發兵北上攻金峽關。我用我自己來賠你我之當初。這個理由夠不夠?
“兵部從來沒有因無能人可用而來求過我。從始至終都是我主要求,替朝廷來走這一遭的。”
沈毓章聽得口一窒。
他盯著,張了張口,卻說不出一字。心底深一霎而起的強烈沖,令他抬起胳膊,一把攥住了的手。
他將的手地攥在掌心中,就好像攥著他二人所有的當初。
一不地任他攥了半晌,才緩緩地將手從他掌中出。
“毓章。”英嘉央輕輕嘆道,終還是了他的名,“此番賠過之后,你我便再無當初了。”
沈毓章的手在前滯了滯,重新落回膝頭。
他沒說好,也沒有點頭。他用新一的沉默來面對的這句話。
英嘉央側,在他旁坐下。
給出足夠的時間讓二人重新恢復冷靜。直到屋外的日頭移近天空正中,屋的熱意將人蒸出一層薄汗后,才出聲:“你來輔政。”
“你來輔政,”又重復了一遍,然后說:“我便同意。”
同意的是什麼,不需要多解釋。
沈毓章將的話聽得很清楚,臉不變地繼續沉默著。
他沒有表出一的驚訝或猶疑,證明這個主張亦經他自己慮過。
英嘉央看他一眼,繼續說:“余下的二位,你與卓炎可自決策。但是你,必須列位三輔臣之一。否則我絕不答應。”
說:“皇室如今是什麼樣,的確無須你多言。我自及長,邊所有人都告訴過我,父皇在當年母妃過世之后就像是完全變了個人。我不知從前他是什麼樣,但我又豈能不知他這些年來是個什麼樣。國政、天下、民生,哪一件都不在他心里。皇叔虎視在側,積蓄多年而有今日之勢。而今之朝堂,半壁皆是他的僚屬,照此以往,用不了三五年,這大位便該易主了。一旦讓皇叔得了這大位,以他過往對大晉的主張,大平國祚崩塌足可矣。”
笑一笑,笑里頭帶了點自嘲謔意:“如今云麟軍起兵謀大事,你放任部署嘩變不管,我因被扣金峽關便同意你們所為,別說什麼被無奈,這若是忠,什麼是不忠?這若是孝,什麼又是不孝?”收起笑意,一字一句:“但倘是這不忠不孝,能夠換得我大平國祚延綿,你我亦算對得起祖宗了。”
沈毓章目頗復雜地看著。
然后他沉沉應道:“好。”
這一個好字,便是他對提出讓他輔政這一要求的回應。
英嘉央起伏了兩日的心緒亦在此刻被這一個好字輕輕平。垂下眼,又想到一事:“你信卓炎,信到了如此地步。”
這話里有深意,引得沈毓章不得不問:“何意?”
答說:“你連續六年不曾回京,自然不知道。自五年前卓疆經王舉薦、提兵離京出豫州之后,他與卓炎兩人便再未一同出現于眾人眼前過。就連景和十五年,卓疆因軍功封逐北侯的那一次,卓府對外亦稱卓炎抱病,沒有隨眾人一同出城親迎兄長回朝。這其中多古怪,朝臣們亦非傻子,五年來不是沒人懷疑過,但因礙于王之勢,從沒人敢將疑慮宣之于口罷了。”
沈毓章倏然抬頭。
的話令他豁然一醒。
那些之前他能想得通的以及想不通的,統統在這一刻,全部重新想得通了。
……
卓炎以亡兄之名重聚云麟軍舊部,舉兵至今,凡之命,江豫燃等人無不奉從。卓疆在世時,麾下第一勇將江豫燃的名聲是連沈毓章也有所耳聞的。那本不可能是一個只沖著卓炎是卓疆胞妹這一點,便能夠讓渡兵權給、對所有的籌略兵策俯首聽從的子。
而自卓炎關以來,沈毓章親眼目睹其在軍中統管軍務,駐營、布防、城事、造械、屯糧、繪圖……諸事樣樣通,絕不可能是一個連續五年深居王府、而今一朝從軍掛帥的人能辦得到的。
猜你喜歡
-
完結80 章

我終于失去了你
十歲那年,許諾撞見父親出軌,父母失敗的婚姻讓她變得像只刺猬,拒絕任何人親近。高考完的一天,她遇見了莫鋮,這個玩世不恭的少年對她一見傾心。莫鋮與許諾完全是兩個世界的人,一個熱情如火,一個患得患失,卻在不知不覺中,許諾慢慢動了心。不料,一次生日聚會上的酒後放縱,莫鋮讓許諾失去了所有,包括心中至愛的親人。剛烈的許諾選擇了一條讓所有人都無法回頭的路,她親手把莫鋮送進監獄。多年後,兩人在下雪的街頭相遇,忽然明白了,這世間有一種愛情就是:遠遠地看著我吧,就像你深愛卻再也觸摸不到的戀人。 一場來不及好好相愛的青春傷痛絕戀。十歲那年,許諾撞見父親出軌,父母失敗的婚姻讓她變得像只刺猬,拒絕任何人親近。高考完的一天,她遇見了莫鋮,這個玩世不恭的少年對許諾一見傾心。莫鋮:你向我說后會無期,我卻想再見你一面。許諾:全忘了,我還這麼喜歡你,喜歡到跟你私奔。洛裊裊:我永遠忘不了十七歲的夏天,我遇見一個叫趙亦樹的少年,他冷漠自私,也沒多帥得多驚天動地,可怎麼辦,我就是喜歡他,喜歡得不得了……趙亦樹:我不知道要去哪里,什麼時候去,我只知道,我想見她,見到她會很開心。
33.3萬字8 6890 -
完結320 章

總裁娶妻套路深
原本只想給家人治病錢,沒想到這個男人不認賬,除非重新簽訂契約,黎晴沒得選擇,只能乖乖簽字,事成之后……黎晴:我們的契約到期了,放我走。傅廷辰:老婆,結婚證上可沒有到期這一說。--情節虛構,請勿模仿
86.9萬字8 37855 -
完結476 章

偏要
楚意沒名沒分跟了晏北傾八年,為他生了兩個孩子。 病得快死的時候,問晏北傾,能不能為她做一次手術。 卻只得到一句,你配嗎? 而他轉頭,為白月光安排了床位。 這個男人的心是冷的,是硬的。 瀕死的痛苦,讓她徹底覺悟。 身無分文離開晏家,原以為要走投無路,結果—— 影帝帶她回家,豪門公子倒貼,還有富豪親爹找上門要她繼承千億家業。 再相見,晏北傾牽著兩個孩子,雙眼猩紅:楚意,求你,回來。 楚意笑笑,將當年那句話送回: 晏北傾,你不配。
66萬字8 58645 -
完結14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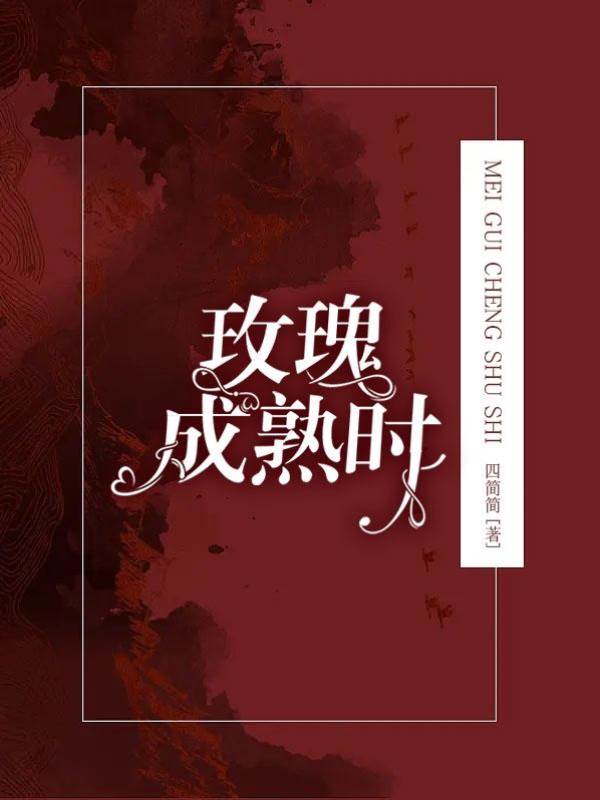
玫瑰成熟時
蘇落胭是京北出了名的美人,祖籍南江,一顰一笑,眼波流轉間有著江南女子的溫婉與嫵媚。傅家是京北世家,無人不知傅城深是傅家下一任家主,行事狠辣,不擇手段,還不近女色,所有人都好奇會被什麼樣的女人拿下。蘇落胭出國留學多年,狐朋狗友在酒吧為她舉辦接風宴,有不長眼的端著酒杯上前。“不喝就是不給我麵子?我一句話就能讓你消失在京北。”酒吧中有人認了出來,“那個是蘇落胭呀。”有人說道:“是那個被傅城深捧在手心裏小公主,蘇落胭。”所有人都知道傅城深對蘇落胭,比自己的親妹妹還寵,從未覺得兩個人能走到一起。傅老爺子拿著京北的青年才俊的照片給蘇落胭介紹,“胭胭,你看一下有哪些合適的,我讓他們到家裏麵來跟你吃飯。”殊不知上樓後,蘇落胭被人摁在門口,挑著她的下巴,“準備跟哪家的青年才俊吃飯呢?”蘇落胭剛想解釋,就被吻住了。雙潔雙初戀,年齡差6歲
23.5萬字8 17103 -
完結166 章

頂不住了,傅總天天按住我不放
[頂級豪門 男主冷傲會撩 女主嬌軟美人 後續男主強勢寵 雙潔]時憶最後悔的事情,就是招惹渣男未婚妻的小叔子。本來吃完就散夥,誰知請神容易送神難。一場意外,兩相糾纏。“傅先生,這事不能怪我。”傅霆洲步步緊逼,“ 所以你必須,我想你就得願。”傳聞中桀驁不馴的傅霆洲步步為營想偷心,其實最先入心的是他!
61.1萬字8.18 4029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