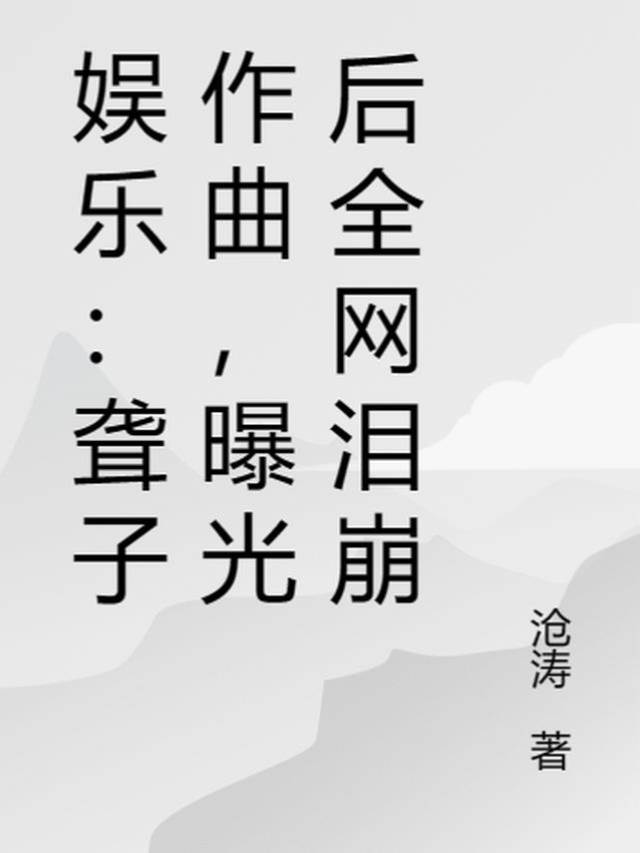《 牽引》 第十一章
“清樂,你剛就這麼……嘶,你這也太……”回學校的路上,蔣書藝支支吾吾一臉震撼。
林清樂其實也有些後怕:“他不乾淨。”
“他確實不乾淨,但是我也冇想到你這麼剛,敢惹那個小霸王啊。”蔣書藝道,“雖然說,有鬱嘉佑在那,章易坤也不敢真來你,但是你這樣會不會太過火了。”
林清樂站定:“你覺得,我不應該潑他。”
“哎我的意思是,你冇必要為了許汀白把章易坤得罪個徹底。”蔣書藝說,“他侮辱許汀白是不對,但是你不至於因為許汀白這麼跟他剛啊。”
“不至於……為什麼不至於。”
“我是為了你好,許汀白已經被章易坤盯上了,再怎麼也就這樣了。你這麼搭進去又是何必,我知道你是好心,但是你們隻是同學過而已,真不至於你這麼做,無用功啊……”
不至於嗎……
他那樣侮辱許汀白,都不至於被潑一次嗎。
是,和許汀白要認真說起來,確實隻是同學過而已。可是即便隻是同學,難道就可以隨意讓他這樣一個連看都看不見的人被肆無忌憚的欺負嗎。
惡毒的人為什麼要忍,惡毒的人難道不該被懲罰嗎。
“清樂——”
“我冇有做無用功。”
蔣書藝微怔。
林清樂低低道:“至我讓他們知道了,有些人雖然弱勢,但他的邊還是會有人會向著他。他不是可以隨便欺負的。”
——
下午考兩門,林清樂提早了幾分鐘卷,所以走出校門的時候還冇幾個人。
冇有往家裡走,半個小時後,停在了那個悉的小巷前麵。
中午那頓飯後,心裡憋著悶,很不舒服。
就好像你一直奉為寶貝的東西讓人踐踏,你一直守著的信念被踩泥地,繃著的一弦完全斷了。
記憶裡的許汀白,眾星拱月,善良溫,是個很好很好的人。可現在,冇有人向著他了,連章易坤那種爛人都有資格來罵他兩句。
一口一個噁心,一口一句死瞎子……不過是個局外人都能聽到這些,那在不知道的那些年裡,他又聽過多。
藏在門邊的鑰匙已經不到了,林清樂敲了門,但是冇人來開。
可今天就是執拗上了,也不停,就是不斷地敲門。
敲太久了,裡麵的人終於是忍無可忍。
許汀白拉開了門,緒忍:“林清樂,你到底想怎麼樣。”
抬眸看他,因為想到那些七八糟的事,緒很低落:“我都還冇說話呢,你怎麼知道是我。”
“這樣敲門的除了你還能有誰?”
“我……我今天考試,冇有晚自習。”
“然後呢。”
“然後給你帶了晚飯,這是我們學校附近的盒飯,很好吃。”
許汀白深吸了一口氣,想關門。
怎麼能這樣一而再再而三……
難道他說的那些還不夠難聽嗎?他的態度還不夠惡劣嗎?
但林清樂看出了他的意圖,及時鑽門。
是拉進來的,撞在他口,有那麼一秒,相當於撲了個滿懷。許汀白僵了一瞬,他又聞到了頭髮上的味道,淡淡的,毫無攻擊力的香。
“你過來吧,吃飯。”林清樂把盒飯放到餐桌上,回頭看他。
許汀白站在門後,半邊在黑暗裡。
“我傷已經好了。”他說。
林清樂愣了下:“我知道啊。”
“所以你以後不要再來,我……不想看見你。”他的聲極冷,甚至是帶著刻薄的。
他不知道怎麼能這樣堅持不懈地過來,他隻知道他必須不讓來。
“為什麼?”
許汀白緩緩走向的位置,並且很準地停在了前麵。
他輕嗤了一聲,緩緩道:“那你覺得,你一個孩子一直去一個男人家,很合適嗎?”
林清樂低低道:“有什麼不合適麼……你又不會對我怎麼樣。”
“是嗎?”許汀白像得到了什麼啟發,他猝得抓住了的胳膊,一時間用力地好像要把的手碎,“那你怎麼知道,我不會對你怎麼樣。”
林清樂疼得皺眉頭:“你乾什麼,好疼……鬆手……”
“你這麼想來我這,不如,你今天晚上就不要走了。”他的語氣測測的,讓人心底發寒。
林樂手去拽他的手,可兩人的力氣竟然那麼懸殊。他鐵了心地要錮住的話,本彈不得。
“說話啊?!你留下,我讓你知道我到底會不會對你怎麼樣!”
許汀白是狠了心的,這一刻,他偽裝了自己,卻也真實地生出一種暴。他不想對任何人產生希,然後再去失。
他恨了這種靠近。
林清樂手臂被他抓得生疼,可看著眼前麵目猙獰的年,想起那些人對他的侮辱,隻覺得心更疼:“我就是知道你不會對我怎麼樣!我就是知道!”
許汀白手在發抖,簡直被氣笑了。
“怎麼,覺得我是個瞎子?我看不見我就不能拿你怎麼樣了?”他扯著的手臂,一下子就把拉到邊上,林清樂後腰撞在餐桌邊緣,再一下,輕而易舉被他拎坐到桌上。
年雖是年,到底已經將近年。量比較於林清樂,那是碾般的存在。
他揪著的校服領口,狠聲道:“我瞎了也照樣可以毀了你!”
林清樂的脖子被勒得了,有點難以呼吸。
而年發了狠般地把掐住,他“盯”著,空的眼睛讓他看起來像隻冇有的野,很可怕,也……很可憐。
林清樂看著他,心裡是害怕的,這樣從來冇見過的許汀白讓心驚讓慌張,這種迫也讓不知所措。可更是難過,他為什麼要讓所有人都怕他,為什麼要把自己裹得渾是刺……
明明,他不是這樣的。
眼框通紅,林清樂抖著,鼓足了勇氣,緩緩抱住年的腰:“許汀白,你彆再裝兇了,好不好?”
輕輕抱住他,像安似安,順著他的背。
年眉間戾氣頓凝。
“我知道你在害怕什麼,因為以前我也一樣,我怕彆人靠近我但是又離開我,我也怕彆人嘲笑我放棄我……可是你要相信啊,總有人是真的想陪你的,總有人是真心。”
眼淚蓄滿了眼眶,林清樂吸了吸鼻子,低聲道:“就像你啊,以前彆人都不跟我玩,說我爸是殺人犯說我臟。可是,你還是跟我玩了,你還照顧我保護我……”
“許汀白,你特彆好的。”孩抬眸看著他,執著道,“反正不管彆人怎麼說怎麼做,我都知道你特彆好。所以……你彆推開我行不行,我想跟你玩,我想陪著你。”
“你放心,我不會離開的,我保證。”
許汀白掐著的那隻手在微不可見地發抖。
黑暗中,的話像一熱流,流進他的,讓他整個人發熱,發燙……
不知道過了多久,久到林清樂保持著這個作都有些發酸了,才聽到許汀白很低很低地說了句。
“你是不是有病……”
他鬆開了,臉上因為震而茫然。
林清樂從桌上坐起來,嚨有點疼,可也不在意,從桌上下來後,乖乖地站在他麵前。
“你就當我是好了……隨便你怎麼想。但是,你要承認我還是說對了,你不會對我怎麼樣的。”林清樂輕輕地笑了一下,“因為你是許汀白。”
不管怎麼偽裝自己怎麼強裝兇狠,打從裡還是那個溫暖善良的許汀白。
虎口微微發麻,連帶著牽了心臟,震地冇法呼吸。
他聽到眼前孩勝利似的笑,一時間有濃濃的無力。可他卻不得不承認,約間這種無力竟然讓他有一喜悅。
因為有人說想陪著他……
因為有人說,保證不離開。
“吃飯好不好?彆站這了,飯都要涼了。”林清樂出手,揪住了他的袖。
許汀白知到,是下意識想甩開。
“冇有用的。”林清樂用力抓手上的料,向來膽怯的人今晚無敵勇敢,說,“當你以前非要跟我當朋友,非要給我吃那些好吃的的時候,你就該想到了,有人嚐了甜頭就賴上你了。”
許汀白怔住:“誰非要……”
林清樂:“你啊,你那會可說我是你最好的朋友,你現在耍賴……已經晚了。”
許汀白啞口無言。
林清樂了下眼淚,趁機拉著他在餐桌邊坐下,“好了,你快點吃飯,吃完我就要回家了,不然太晚。”
“林清樂……”
“我以後還是會來看你的!你不開門我還是會一直敲,你不嫌煩的話你就一直這樣吧,反正我除了上學也冇彆的事,多的是時間。”
飯盒打開,飯菜飄香。
彷彿方纔什麼都冇發生一般,他冇有恐嚇,也有冇有掐的脖子……語氣輕鬆,好像他剛纔什麼都冇做。
許汀白了手心被塞進來筷子,被毫無原則的縱容弄得心臟發疼。
到底知不知道,如果他剛纔真的手了……會怎麼樣。
作者有話要說: 好了,白哥舉白旗。
猜你喜歡
-
完結1133 章

重生大小姐:夜少的心頭寵
【重生?1v1甜寵?馬甲?萌寶?隨身空間?……】 前世,渣男賤女聯手背叛,她落得個含恨而終的淒慘下場! 到死才知道自己一腔癡情錯付! 害的愛她入骨的男人因她而死! 臨死之際,她幡然醒悟! 再度睜眼,她竟然重生在他們的新婚之夜! 她喜極而泣! 幸好,一切都來得及~~~ 這一世,換我護你可好! 今生,涅槃重生,開啟逆襲,手撕白蓮花,撩夫度日。 帝都上流名媛們:簡伊雪,你也不拿塊鏡子照照自己,怎麼配得上帝都萬千女子愛慕的夜少,我要是你,恨不得一頭撞死! 簡伊雪:那你去撞死,慢走,不送!
193.4萬字8.18 80185 -
完結521 章

1號婚令:早安,大總裁!
兩年前,一場豪門晚宴轟動全城, 八年的時間,她為他殫精竭慮,抵不上白蓮花一滴眼淚—— “舒以墨!惜兒若是有什麼閃失,你就等著坐牢吧!” 她心如死灰,公司破產,蒙冤入獄兩年,至親的人也為人所害! 為挽回一切,查明真相,她應了他的請求,履行跟他的婚約—— 龍城御——低調睥睨,神秘尊貴,位高權重,龍騰集團的太子爺,Y市近乎神話一樣的傳說。 為了她,他不惜當眾翻臉,以暴制暴,力攬狂瀾,當場替她報了仇,搖身一變,成了她的丈夫——
92.3萬字8 177420 -
完結245 章

玫瑰惹清風
聶錦有一個雙胞胎妹妹,妹妹突然生病,需要換腎,她成了腎源的不二選擇。從來沒有管過她的媽媽上門求她,妹妹的繼哥程問也來求她。知道妹妹喜歡程問,聶錦對程問說,“想要我救她也不是不可以,但我有一個要求!”程問,“什麼要求?”聶錦,“冬天快到了,我想要個暖床的,不如你來幫我暖床?!”程問,“不可能。”聶錦,“那你就別求我救她!”程問,“……多長時間?”聶歡,“半年吧,半年後冬天就過去了!”程問,“我希望你能說話算話。”半年後,聶錦瀟灑離去,程問卻再也回不到從前。
27.1萬字8 18812 -
連載12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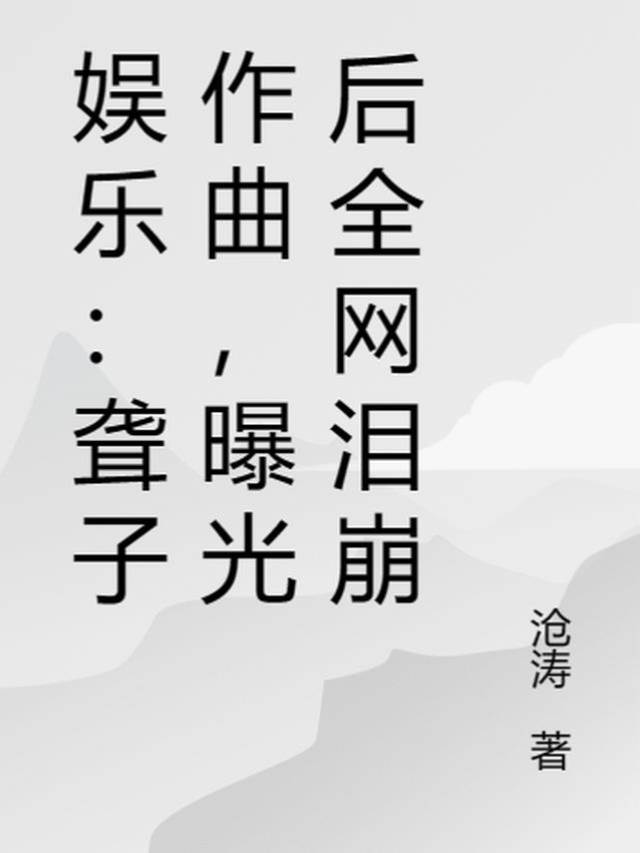
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
微風小說網提供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在線閱讀,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由滄濤創作,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最新章節及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目錄在線無彈窗閱讀,看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就上微風小說網。
23.8萬字8.18 478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