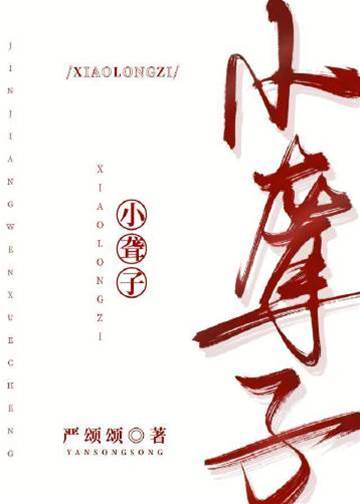《輕易放火》 第五十七章 新西蘭之旅(3)
下午文潤帶著小外甥去超市,易文澤就帶著去了母校。
佳禾念書的時候,總覺得大老校區很有覺,可是進了奧克蘭大學,卻覺得不像學校。所有的建筑都藏在綠茵花叢中,因為沒有所謂大門和圍墻,遠近走著的很多都不是學生,倒更像是植園。
走在易文澤邊,聽他講一些大學的事,很地嘆著:“算起來,我母校的世界排名,比你差了百位數,太挫敗了。”
他笑著看:“你怎麼知道?”
挑眉說:“我當初看你明星資料嘛,看你在哪里畢業后,特地查了下這個學校,”很是自滿地看了他一眼,繼續說,“我還知道你們學校附近,就是奧克蘭最大的國家公園,老實待,你當初有沒有在那里和別人約會過?”
本來是玩笑著問,他卻笑而不語。
哼,我就知道有……
佳禾裝作大方的說:“青春年,總會春心萌,放心,我既往不咎。”
易文澤依舊保持沉默,笑著看。
佳禾終于繃不住,盯著他說:“你不會景生,開始回憶了吧?”
“很憾,”他終于笑了,“當時我除了圖書館和各個階梯教室,基本就沒有去過別的地方。”佳禾哦了聲:“真憾。”心里早已滋滋地樂開了花。
兩個人走走停停,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著話。
縱然是再開放的學校,可還是讓找回了學生時代的覺,跟著他的腳步,很輕地拉住了他的手指,五指叉握著:“了。”
“好,回家,”他很簡單地說完,手了的腦袋,“你讓我開始后悔,當初在大學沒有。”佳禾把這話在腦子里繞了兩圈,才很滿意地點頭:“同學,晚了,你已經是有婦之夫了。”
樹很低,能過隙,看到遠的白鐘樓,很漂亮。
挽著他的胳膊,一步一步地走著,然后忽然有而發地說:“有時候我會想,大學時候要是好好讀書,不談,就會完完整整地上你,只你,那多好。可是有時候又會想,如果沒有之前,我就不會轉行做編劇,也就不會認識你……”
生活真是是辯證啊,不知怎麼了,竟然很是慨了一把。
他的笑很淺,聽著說完,才說:“同學,我可以認識你嗎?”
怔了下,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馬上松開他的手臂,退后了兩步,裝作抱著書的樣子,很是靦腆地看著他:“為什麼?”
易文澤目漸和了下來:“我想,你的未來應該和我有關。”
盛夏的熱浪,還有他的眼神,都灼著的心。
不知道是他演技太好,還是這個環境本就能讓人產生幻想。竟覺得易文澤真的就是這個學校的建筑系大帥哥,而自己只是一個普通的每天只想著如何不掛科的生。眼神飄著,努力想說出一句驚天地泣鬼神的對白,可是想了很久,也沒有什麼好的臺詞。
而易文澤也就只是這麼看著他,單手兜,很是隨意地站著。
“編劇,接下來怎麼演?”他微微笑著,終于又開了口“要不要cut?”
“不要,”努力挽回面子,“你不知道此時無聲勝有聲嗎?”
忽然想起和他唯一那兩場對戲,還是飾演淚眼婆娑的棄婦,本想找點兒覺,徹底被回憶打敗了。看著他,最后終于嘆了口氣:“對不起,我大學不想……”
好吧,咱也演一次拒絕人的人。
“是嗎?”他笑著看,走上來兩步,就這麼低下頭了下的。
很輕,也很純的一個吻。四周還有人走過,佳禾心怦怦地跳著,本就沒猜到他這一步的作,只下意識退后一步,頭重腳輕地看著他:“你跳集了?怎麼能剛搭訕就吻戲呢?況且我還拒絕你了。”
易文澤很是正經地看:“還沒演過登徒子,想試試覺。”
哦了聲,把玩著脖子里的小金豬,明明被調戲了,竟還笑的像中了大獎。
到晚上時,易文澤接了個電話。
佳禾看著他站在窗口,很溫地說著話,立刻心跳的有些不穩。這個時間這個電話,老佛爺要見兒媳婦了……見過易文澤一家的照片,不得不說他們兄妹兩個長得很像媽媽,尤其是那雙眼睛,都很溫和,視線專注的讓人很有安全。
可是,畢竟是見未來的婆婆。
有些小張的想起老媽的叮囑。一定要說話溫,不要穿著太隨便,要幫著做一些事顯示自己不是個懶人……腦子里過著這些話的時候,易文澤已經掛了電話,看開始翻著箱子里的服,拿出了一件七分袖的外,又去挑很長的子。
他看著對著鏡子比對,才笑著說:“你這麼穿,不熱嗎?”
很認真地看他:“保守一些,總好過穿的暴。”
易文澤也很認真看:“老婆,說實話,你平時已經很保守了。”
張了張,啞了。
這算是夸獎?還是抱怨?
最后為了第二天的見面,一夜翻來覆去沒睡著。易文澤看實在張,就陪著說話,懷里是小孩子,兩個人也不敢很大聲,就這樣在耳邊耳語著,到天蒙蒙亮了才算是睡了會兒。直接的結果就是,臉真的有些差。
車開進惠靈頓時,就開始看他,一眼又一眼的,終于把他得笑起來:“老婆,你讓我也開始張了。你知道你現在覺像什麼?”
“什麼?”佳禾張看他,“是不是臉很難看?”
“像白雪公主去見惡毒后母,”他盡量用話來形容,企圖讓放松,“你可以試著這麼想,你要見的不是后母,而是吻醒你的王子的母親。”
易文澤難得說話這麼酸,徹底讓笑出了聲,也輕松了些:“我應該把你這段話錄下來,賣給國的話,絕對是炸的效果。”
他只是笑了笑:“我不介意。”
佳禾看了他一眼,你不介意,我介意……
結果兩個人剛才進門,易文澤母親的三句話,就讓徹底不會說話了。
第一句:你們準備在新西蘭辦婚禮嗎?
第二句:定好日子了嗎?
第三句:需要我開始準備了嗎?
看著面前笑的完婆婆,森森然回頭看易文澤。怎麼覺是買了一堆昂貴裝備,膽戰心驚準備打*oss,到關卡時卻直接被告知:您已順利通關。
“怎麼?”易文澤母親也去看他,“這次回來不是結婚的嗎?”
易文澤笑著把熱茶遞給佳禾,示意鎮定,才對母親說:“您再說下去,就把我想要說的話,都說完了。”
易文澤母親驚異看他,再看佳禾,又去看他。
最后終于長嘆口氣:“太過分了,”繼續回頭看佳禾,“你們在一起這麼久了,他竟然還沒有求過婚?佳禾,你該好好思考下,不能這麼放任男人。”
佳禾窘然點頭。
這哪兒是婆婆,親媽啊這是……
兩個人很投機,媽媽竟像是只有個普通的兒子,從來對演藝圈沒有了解一樣。只是笑著不停問佳禾編劇的各種趣事,聽得興起,還會把遠陪父親說話的易文澤過來,讓他再說些有趣的事。
這樣的氣氛,佳禾很快就放松下來。
到了半夜,易文澤母親終于很神地拉著站起來:“我昨天一回來,就特地給你們布置了房間,你來看看喜歡不喜歡?”佳禾很是喜地看易文澤,然后就聽見他母親又耳語了一句,“今晚試試,讓他求婚。”
佳禾啞然,盛難卻下只好點點頭,徹底不知道說什麼了。
兩個人的房間在二樓,走廊最盡頭的那一間。
易文澤母親推開門時,徹底就被震撼了。
總被蕭余喬喬嘲笑有紅心,可現在才發現,真正有心的是邊這位漂亮的婆婆大人。易文澤和進了房,門就被他母親主關了上。
房間里有數百只蠟燭,沒有燈。
星星點點中,床上都是玫瑰花瓣,地上也都是,大片大片的讓人瞠目。
這樣俗的場景,卻是所有人的最。
可是現在站在他邊,卻只想笑,最后實在忍得不行,兩只手抱著他的胳膊,蹭來蹭去終于笑了出來。聲音是刻意低的,忍得胃都疼了。最后才抬起頭,看他也是一副很震驚很忍俊不的表:“如果我不知道你是易文澤,我肯定會認定你是娶不到老婆的大齡剩男……你媽實在太可了。”
他走過去,用開瓶打開紅酒,倒在杯子里,輕抿了一口:“這應該還有文潤的功勞。”
佳禾更是笑個不停,走過去,湊著他的杯子也喝了口:“好吧,我認輸了,我投降了。”
他笑著了下的臉:“你不是昨天一夜沒睡嗎,快睡吧。”
笑著指了下床:“老公,你真想睡在一堆花瓣上?”
于是兩個人費盡力氣,才把被子上和被子里所有的花瓣清理干凈。佳禾看著滿地的各花瓣,很是嘆了口氣:“這些明天整理起來更麻煩,果真浪漫是要付出代價的。”
飛機上十幾個小時的折磨,再加上這兩天都在伺候小孩子,兩個人早就累得不行。
此時難得有個舒服安靜的睡覺環境,也顧不上有多浪漫,很快就睡著了。
猜你喜歡
-
完結47 章

離婚成為富婆后
影視頂流顧宣烈,劍眉星目,矜貴高冷。 身為顧氏企業的大少,是粉絲們嘴里不努力就得回家繼承家業的“人間富貴花”。 他從不與人傳緋聞,對外宣稱不婚主義。 但心底埋藏一個不為人知的秘密—— 他想要的女人,是別人的老婆。 才剛離婚,季開開頂著亞姐的頭銜重回娛樂圈,上綜藝,演電視,錢多人美,一炮而紅。 娛記樂于報道她的豪車上,又載了哪個小鮮肉來博取新聞版面。 黑粉群嘲:不過是拿錢泡“真愛”,坐等富婆人財兩空。 后來,眼尖的粉絲發現,從季開開車上下來的是娛樂圈的頂流影帝顧宣烈! 認為她一定會后悔的前夫:“……” 嗯?不對!一定是哪里出了問題。 前夫緊急公關,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太太有些頑皮,過幾天就會回家!” 一天后,影帝曬出八億的藍鉆戒指和一張幼時的合影,[顧太,快來認領我!] 他想要的女人,這次一定得是他的。 **雙C卯足了力氣開屏吸引人的影帝VS我只喜歡你的臉真的不想再結婚的小富婆
13.3萬字8.33 7585 -
完結7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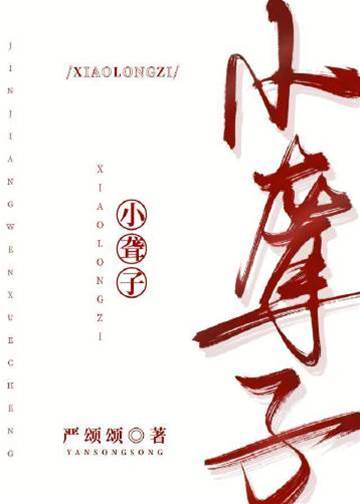
小聾子受決定擺爛任寵
憑一己之力把狗血虐文走成瑪麗蘇甜寵的霸總攻X聽不見就當沒發生活一天算一天小聾子受紀阮穿進一本古早狗血虐文里,成了和攻協議結婚被虐身虐心八百遍的小可憐受。他檢查了下自己——聽障,體弱多病,還無家可歸。很好,紀阮靠回病床,不舒服,躺會兒再說。一…
30萬字8.18 17628 -
完結207 章

不浪漫罪名
簡介: 周一總是很怕陸聿。他強勢霸道,還要夜夜與她縱歡。他貪戀她的柔軟,想要她的愛。世人都以為他在這段感情裏占據了絕對的主動權。可他說:“一一,我才是你卑微的囚徒。”~也許,你我都應該認下這從一開始就不浪漫罪名。
33.3萬字8.25 762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