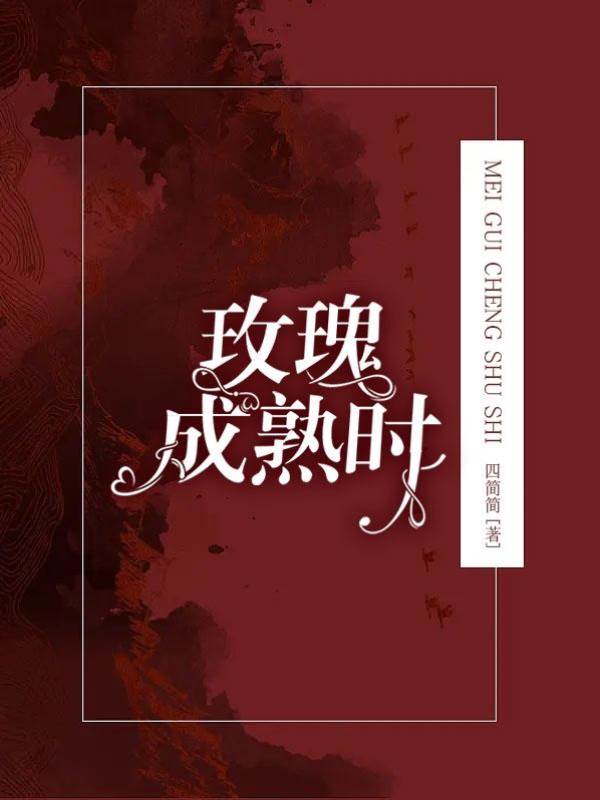《他站在時光深處》 第23章 他站在時光深處22
應如約咬了咬下, 在溫景然滿目似笑非笑里忽然醒悟此刻自己捂著后頸一副投降的姿態看上去有多蠢。
松開手, 一時不知道是該先和溫醫生打招呼還是先問問他怎麼會出現在這里。
畢竟從應如約已知的報里, 溫景然敬業負責到幾乎快住在醫院里了, 可現在的況卻是……隔三差五的,總是在一些匪夷所思的地方遇到他。
比如現在。
有水珠不偏不倚地落在的額頭上, 又沿著的鼻梁往下落, 水珠滾時那微微的意如同撓心一般, 讓應如約再也無法忽視。
抬手干額頭上的水珠,不那麼真誠地吐出兩個字:“好巧。”
溫景然不置可否。
他看上去心不錯, 溫淡的眉眼似凝著這山林間的水汽,有潤的明亮。此時,這雙眼睛里正清晰得倒映著如約的影,小小的, 卻格外鮮明。
他的手指從金龍脊上移開,指尖帶著幾分漉, 握住傘柄撐開傘, 替擋住多寶塔上仍不斷往下滴的水珠。
然后,那繃直的傘面就發出清脆的敲打聲,聲音沉悶,卻意外得好聽。
同時響起的,是他同樣低沉的聲音:“回來看看阿姨?”
“嗯。”如約點頭:“等上班后就不會有這麼充裕的時間可以往返在兩個城市之間了。”
傘面上水珠的敲打聲漸漸集。
不知何時又下起了雨,除了傘下的空間,其余的空地紛紛被雨水打。
剛剛如約在梵音寺門口見到的沙彌此時也一手著寬大的袖子遮雨,一手握著掃帚匆匆地往廊檐下走。
溫景然握著傘柄的手微抬:“走吧, 去避避雨。”
如約“喔”了聲,亦步亦趨地跟著他的腳步往大殿的廊檐下走去。
有一只橘的貓被驚擾,“喵”的一聲輕,從石柱下鉆出來,弓著子幾下就沿著走廊奔向了后院,不見了蹤影。
應如約眼睜睜看著橘的花貓從的邊飛躥過去,新奇地咦了聲:“寺廟里還養著貓嗎?”
“不是正經養著的。”溫景然握著傘骨合上傘,從多寶塔走過來沒幾步的距離,傘面上已經漉了一片,此刻正有雨水沿著傘骨往下滴著水,沒一小會,就在干燥的地面上匯聚了一灘。
他隨手把黑傘靠在了廊柱下,偏了子替擋風:“這里的貓來的隨,走得也很隨意。有貓的時候,這邊的僧人和客堂里住的客人都會投喂。”
如約會意,忍不住回頭張了眼那只貓消失的地方。
溫景然一直留意著的神,見狀,問道:“喜歡貓?”
喜歡茸茸的小他一直都知道,但范圍廣泛到在路上看到乖巧的貓狗都會多看幾眼,即使這麼多年,他也依舊不清楚喜歡的到底是貓,還是狗。
“還好。”如約對上他的目,有些不自然地撇開:“我喜歡別人家的。”
溫景然的角了,似乎是想笑。
應如約說完才覺得有些尷尬,了鼻子。
正好,旁邊的石碑上繪制著梵音寺的地圖,湊過去,認真的研究。
地圖上只標注著基本的方位,和殿名。
如約所在的方向不過是剛邁正門口,離后面的佛堂,客堂都還有一段距離。
徒步上的山,按照原計劃,這會要先去給菩薩上香,再去跟梵音寺的主持求幾個平安符,午飯就在寺里吃素齋。
如約在腦子里臨摹好整個路線圖,等抬起頭,目落在梵音寺目能所及的那些錯落的回廊,殿宇,香堂時……頓時頭大。
一旁站立的人,終于忍不住笑出聲。
那笑聲清越,又帶著男人特有的低沉,被雨聲修飾了鋒棱,就像在多寶塔下,他撐起傘替擋去滴落水珠時,那水珠落在傘面上的聲音,微有些沉悶的悅耳。
應如約轉頭怒視。
溫景然略收斂了幾分,自然地拿起傘:“走吧,我給你帶路。”
應如約很有骨氣地立在原地,一步不邁。
哪怕沿著這條回廊多走幾條冤枉路,遲早也能把整個梵音寺逛一遍,才不需要他帶路。
但這樣的堅持沒超過三秒。
已經邁上臺階穿過拱形門的人,停下來,轉頭看了一眼,好心提醒:“齋飯每日都有份額,要提前去告訴師傅。你再磨蹭,只能下山吃素面了。”
——
上了香,又給應老爺子,外婆,向欣,以及甄真真求了平安符后,正好到飯點。
從大殿出來,沿著一條上坡的小路,穿過了庭院。
庭院里種著一列不知多年的榕樹,榕樹的須茂,長些的已快垂落地面。幾株樹巍峨拔,幾乎遮天蔽日。
小徑是沒雕砌過的青路石,凹凸不平。
沿著明黃的矮墻一路往上走,等到空地時,遠是一排錯落有致的古建筑。說是古建筑,外面的紅漆和明黃的琉璃瓦又是簇新的。
云霧繞著立在屋檐最頂端的金鶴,整座客堂猶如生在云端,恍若世外之。
還未等如約跟著溫景然走到近前,有一個年輕的人從客堂的樓梯上下來,拿著一把明的雨傘,正松散了傘面撐開,可抬起眼的那刻,看著面前的兩個人,頓時愣住了。
這種驚訝不過短短幾秒,很快出笑來,快步迎上來。
應如約看第一眼的時候,覺得有些眼。
這個年輕人長得很好看,那種好看沒有攻擊,就像是江南深閨里撐傘而來的溫子。
一顰一笑,皆是化骨。
“景然。”隨安然走到近前,友善地對應如約微微頷首后,遞過去一個眼神。
溫景然會意,介紹道:“這位是小師妹,應如約。”
小師妹?
隨安然在記憶里搜尋了下,似乎是有些印象。
溫景然雖鮮回A市,但因溫景梵和經常會來往A市和S市之間,偶爾見面也會聽他提及些工作上或者生活上的事。
隨安然有印象的不是小師妹這個份,而是應如約這個人。
所知道的幾次溫景然回A市,幾乎都與應如約有關。
“隨安然。”出纖長的手,自我介紹道:“我是景然的嫂子,輩分是高一些,年紀比景然還小些。”
微笑,眼神里有明顯的曖昧之意。
可不知是氣質安靜的原因還是那溫如水的語氣,哪怕此刻眼里帶著幾分打量探究,應如約都覺得并不唐突。
出手,輕輕握住隨安然的:“你好。”
一路談到齋堂。
梵音寺今日香客不多,齋堂的窗戶臨山而開,格外幽靜。
遞了木牌,取了齋飯,三人對坐。
因是齋飯,不宜談,一頓飯吃得格外安靜。
午飯后,隨安然要隨溫景然回S市,反正順路又方便,就捎帶上了如約回家拿行李。
從梵音寺下山到老城區,走走停停竟也花了快一個小時。
老城區街道狹窄,自古鎮旅游業興旺后,機車在上橋進古鎮前便被攔下來,只容許非機車進出。
溫景然臨河停了車,一手還握著方向盤,轉頭正想問后座一到目的地就神了的應如約需不需要幫忙拿行李。
還沒張口,就見邊推開車門跟只小老鼠一樣哧溜一下就下了車,邊留下了一句“你們稍等,我去拿行李”,轉就跑了。
隨安然看得忍不住發笑,打趣道:“我看你這小師妹跟你的關系并沒有很好啊。”
溫景然抬頭瞥了一眼,沒作聲。
這種明眼人都能看得出來的事,這麼拿出來問他,不是明擺著他痛麼?
偏偏今日,隨安然像是看不出他不說話的緒一樣,又問道:“我聽說你在梵音寺求了姻緣簽?”
溫景然:“……”
“不是說暫時沒有結婚意向,也不急著找朋友?”隨安然輕笑,手肘支著敞開的車窗,側頭看著他:“承認有喜歡的人就這麼難?”
那略帶了幾分清冷的語氣,倒是和溫景梵像極了。
“不難。”溫景然出煙,正要點上,想起旁邊坐的人現在特殊,已經叼在邊的煙被他擰斷。
“我和之間的況不是你和我哥那樣簡單。”溫景然微微瞇眼,指尖把玩著那已經被擰斷的香煙,悶聲道:“太急進適得其反,我拿是一點辦法也沒有。”
難得能從溫家這位優秀的外科醫生里聽出無奈,隨安然新奇之余有些幸災樂禍。
抬手遮住忍不住上揚的角,輕咳了一聲清了清嗓:“那你打算怎麼辦?溫水煮著?”
溫景然瞥了一眼,含糊地拋出一句:“我心里有數。”
——
S市下了一整天的雨,這暮比往常來得要更深更沉。
中午吃的齋飯不夠墊肚子,饒是應如約這種全程睡過來的,醒來時也腸轆轆。
猜你喜歡
-
完結80 章

我終于失去了你
十歲那年,許諾撞見父親出軌,父母失敗的婚姻讓她變得像只刺猬,拒絕任何人親近。高考完的一天,她遇見了莫鋮,這個玩世不恭的少年對她一見傾心。莫鋮與許諾完全是兩個世界的人,一個熱情如火,一個患得患失,卻在不知不覺中,許諾慢慢動了心。不料,一次生日聚會上的酒後放縱,莫鋮讓許諾失去了所有,包括心中至愛的親人。剛烈的許諾選擇了一條讓所有人都無法回頭的路,她親手把莫鋮送進監獄。多年後,兩人在下雪的街頭相遇,忽然明白了,這世間有一種愛情就是:遠遠地看著我吧,就像你深愛卻再也觸摸不到的戀人。 一場來不及好好相愛的青春傷痛絕戀。十歲那年,許諾撞見父親出軌,父母失敗的婚姻讓她變得像只刺猬,拒絕任何人親近。高考完的一天,她遇見了莫鋮,這個玩世不恭的少年對許諾一見傾心。莫鋮:你向我說后會無期,我卻想再見你一面。許諾:全忘了,我還這麼喜歡你,喜歡到跟你私奔。洛裊裊:我永遠忘不了十七歲的夏天,我遇見一個叫趙亦樹的少年,他冷漠自私,也沒多帥得多驚天動地,可怎麼辦,我就是喜歡他,喜歡得不得了……趙亦樹:我不知道要去哪里,什麼時候去,我只知道,我想見她,見到她會很開心。
33.3萬字8 6890 -
完結320 章

總裁娶妻套路深
原本只想給家人治病錢,沒想到這個男人不認賬,除非重新簽訂契約,黎晴沒得選擇,只能乖乖簽字,事成之后……黎晴:我們的契約到期了,放我走。傅廷辰:老婆,結婚證上可沒有到期這一說。--情節虛構,請勿模仿
86.9萬字8 37855 -
完結476 章

偏要
楚意沒名沒分跟了晏北傾八年,為他生了兩個孩子。 病得快死的時候,問晏北傾,能不能為她做一次手術。 卻只得到一句,你配嗎? 而他轉頭,為白月光安排了床位。 這個男人的心是冷的,是硬的。 瀕死的痛苦,讓她徹底覺悟。 身無分文離開晏家,原以為要走投無路,結果—— 影帝帶她回家,豪門公子倒貼,還有富豪親爹找上門要她繼承千億家業。 再相見,晏北傾牽著兩個孩子,雙眼猩紅:楚意,求你,回來。 楚意笑笑,將當年那句話送回: 晏北傾,你不配。
66萬字8 58645 -
完結14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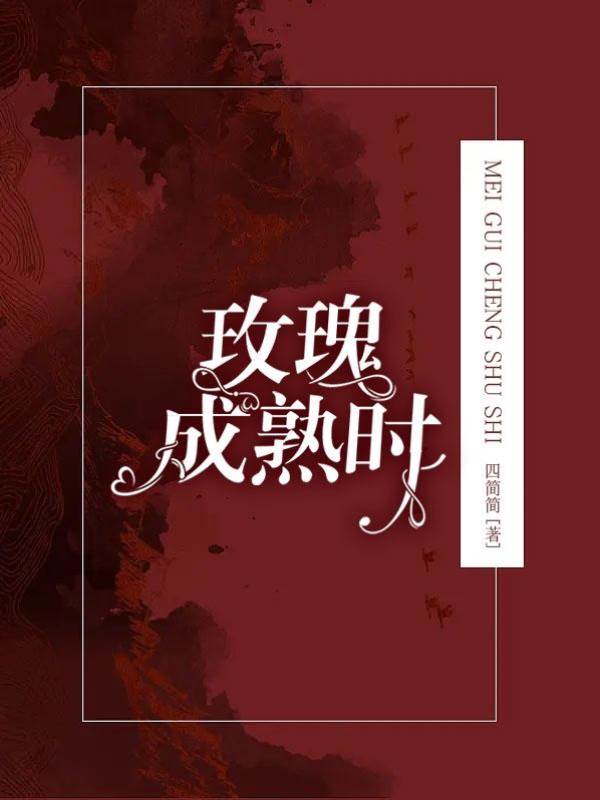
玫瑰成熟時
蘇落胭是京北出了名的美人,祖籍南江,一顰一笑,眼波流轉間有著江南女子的溫婉與嫵媚。傅家是京北世家,無人不知傅城深是傅家下一任家主,行事狠辣,不擇手段,還不近女色,所有人都好奇會被什麼樣的女人拿下。蘇落胭出國留學多年,狐朋狗友在酒吧為她舉辦接風宴,有不長眼的端著酒杯上前。“不喝就是不給我麵子?我一句話就能讓你消失在京北。”酒吧中有人認了出來,“那個是蘇落胭呀。”有人說道:“是那個被傅城深捧在手心裏小公主,蘇落胭。”所有人都知道傅城深對蘇落胭,比自己的親妹妹還寵,從未覺得兩個人能走到一起。傅老爺子拿著京北的青年才俊的照片給蘇落胭介紹,“胭胭,你看一下有哪些合適的,我讓他們到家裏麵來跟你吃飯。”殊不知上樓後,蘇落胭被人摁在門口,挑著她的下巴,“準備跟哪家的青年才俊吃飯呢?”蘇落胭剛想解釋,就被吻住了。雙潔雙初戀,年齡差6歲
23.5萬字8 17121 -
完結166 章

頂不住了,傅總天天按住我不放
[頂級豪門 男主冷傲會撩 女主嬌軟美人 後續男主強勢寵 雙潔]時憶最後悔的事情,就是招惹渣男未婚妻的小叔子。本來吃完就散夥,誰知請神容易送神難。一場意外,兩相糾纏。“傅先生,這事不能怪我。”傅霆洲步步緊逼,“ 所以你必須,我想你就得願。”傳聞中桀驁不馴的傅霆洲步步為營想偷心,其實最先入心的是他!
61.1萬字8.18 4029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