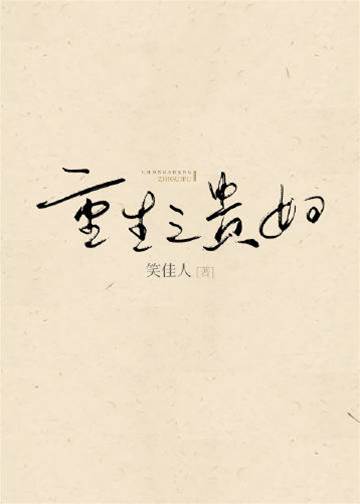《被廢后成了鄰國皇帝的獨寵》 第82章 動心 他太像是爭風吃醋了
“我中傷他?”
宋寒時像是聽到了什麼好笑的話, “我中傷蕭嶼?”
他一下子就握了拳頭,“他有什麼值得我好中傷的,我說的每一句話都是實話, 你如今連我都不信,便要去信那個險小人?”
“他不是你說的險小人!”夏倚照打斷他, 眼神已經有些不耐, “不要自己是什麼樣, 就把別人想什麼樣……”
“夏倚照!”宋寒時終于忍無可忍, “你為何這般維護他?你本就不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人!”
“我不知道,你便清楚了嗎?”夏倚照直接反問他,看著他時眼里沒有任何溫度, 早就沒有了從前看著他時那全心縱容崇拜的樣子,只剩下冰冷和失。
“你也不了解他,又為何憑空斷言他是險小人?起碼在我與他相的過程中, 從未見過他有像你說的那般不堪!”
親眼所見, 自然信任蕭嶼的為人。
倒是宋寒時上有無數讓無法接的暗之。
他給的傷害和創傷,全都是親經歷, 而蕭嶼卻從未在陷囹圄時迫于。
他也許像宋寒時說的那樣,很多年前便過心思, 可他從未讓夏倚照察覺,說明他不曾有過足的想法。
又如何能依照宋寒時口中說的那些只言片語對他進行審判?
即便是從前全心著宋寒時的時候,也定然不會隨意相信他說的這些話,更何況如今他們之間已經沒有任何關系。
宋寒時在這里的信譽度也早就清零。
聽著清凌凌的話語, 宋寒時握的拳頭松懈片刻, 像是已經放棄,可頃刻間又忽而攥,“他不是什麼好人……”
說完這句話之后, 他的眼尾忽然泛起一抹紅,像是終于意識到自己依靠這種手段來對付蕭嶼,屬實下作。
他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變這副模樣,自嘲地笑了一聲,聲音也低了許多,變得有些委屈,“別跟他在一起……”
他忽然出手,牽住了夏倚照的袖,輕輕往外扯了一下,“別跟他在一起,好不好?”
他的聲音很低,聽上去似乎帶著一祈求。
夏倚照著他,眉頭地蹙起,“你這是又換了一種方式?改用示弱想要達你的目的?”
宋寒時頭一哽,“阿照……”
他如今無論做什麼,在夏倚照眼中都是別有目的。
他早就消耗了的信任,這是他自作自。
他沉默下來,過了一會兒才沙啞著聲音嘆笑了一聲,“我知道你憎惡我……可我心中真的從未有過旁人。”
他抬起眼眸,定定地著面前的人,像是忽然想通了什麼,直直道:“我知道你在意什麼,也知道你從來不是會回頭看的人,可我只想告訴你,從一開始到現在,我都不曾背棄對你的承諾,一生一世一雙人,也是我所想的,對于春兒……我從來就沒有旁的,對只是利用……”
這些事夏倚照已經知道,但聽到他這般堂而皇之地說出口,卻只覺得反。
忽然就甩開他的手,“你不必在這里與我強調一次,我知道你從前的所作所為興許有自己的難言之,可當你選擇用這樣的手段去謀求功之時,你我之間便已經有了一條深深的壑。”
夏倚照聲音微涼,“你也明知我不會贊同,可還是那般做了,說明你早就已經做好了要與我陌路的準備,既然已經做好準備,此時此刻又何必在我面前裝出一副深的模樣?”
從前無論是何樣的境地,宋寒時心中都始終殘存著一希。
可夏倚照方才這句話,卻是真真切切地扎在了他心上。
裝?
他從來沒想過,會用這樣的詞匯形容自己與的……
眼尾那一點紅逐漸彌漫,帶著一瘋狂,占據了他的眼眸,原本帶著一清醒的思緒如今也變得不理智起來。
“我在你眼里,就只剩下裝出來的模樣?”他用力地攥著夏倚照的手腕,顧不得什麼。
如今夜彌漫,他只用力地攥住,讓看著自己的眼睛。
看到的眼中就只有自己的倒影,自欺欺人一般自我安,仿佛的心里也只有他一個人。
夜四合。
夏倚照知道如果不跟他說個清楚明白,此后還會有再多這樣不必要的糾纏。
于是定定地看著他的眼睛,“難不你還真以為自己對我依舊深重?”
聽到完全否認他們過去的,宋寒時忽而就有些激,“那十年對你來說什麼都不算嗎?阿回對你來說也什麼都不算嗎?”
夏倚照沒有說話,角繃,過了一會才開口道:“如果真的什麼都不算的話,就不會有那十年……那十年你與春兒在一,即便你說的是利用,可你們真的在一起時,陪伴在你邊的那麼多個日日夜夜都不是假的,但凡你有一刻鐘的偏離,對于我而言,那便是永遠無法消糜的針刺。”
“無論如何我們之間都回不到過去,為何不直接放手?”
如同完好無損的貝殼里闖進一粒讓人難的沙礫,不會像那珍珠貝一樣用去磨合,在時的釀造之下磨練出一顆圓潤的珍珠來。
沒有那麼多的奉獻神。
只為自己的理想生活付出,倘若知道那十年摻雜著那麼多的雜質,絕不可能堅守時。
若是在那十年里,宋寒時并未瞞著,并未瞞替的事實,絕不可能在這邊堅守十年。
宋寒時心里明明很清楚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卻從來不在書信之中提起過春兒的事,便是怕知道之后會與他反目仇。
他分明都知道什麼都知道,可還是抱著那一僥幸,又或者是從來不覺得夏倚照會離開他,便覺得就算不告訴也無所謂,他總有一天能夠將兩個人都糊弄過去。
他在利用春兒,又何嘗不是在利用夏倚照?
這些話宋寒時聽夠了,也聽倦了,眼中火閃爍,“倘若我就是不放手呢?”
他如此冥頑不靈,夏倚照便覺得沒什麼好跟他說的,后退一步,突然揮劍在他面前,“那我便只能夠斬斷一切。”
劍刃地锃”音在空氣中劃出一道痕跡,那蜂鳴聲讓宋寒時腦子里一片空白,幾乎是有些茫然地看著面前的人——
這一切就好像鏡花水月一樣不真實,他們也曾經在夜月下并肩漫步,說著綿綿話,互訴衷腸。
可如今時一轉,在自己面前如同敵人一般,要與他劃清所有的關系。
縱然他們已經離心許久,可他還是無法接這樣的事實。
那忍泛紅的眸無一不在昭示他的緒,可卻沒有辦法夏倚照半分。
哪怕是半半毫的都不再有,只是清清冷冷地著他,“放手吧,這樣對你我都好。”
這話不知道說了多遍,可還是不厭其煩地一遍遍重復。
宋寒時知道是認真的,頹然松開手,頭有些哽咽,那想說的話最終還是難以啟齒。
他如今還剩下一點尊嚴,也只剩下這麼一的尊嚴。
看著夏倚照毫不猶豫遠去的背影,他握拳頭,整個形都匿于黑暗之中。
無時無刻不在后悔,但并沒有什麼作用。
……
夏倚照回到營帳之中時,蕭嶼似乎已經休整好,看到進來,抬頭了一眼。
“過來。”他喚。
夏倚照頓了一下腳步,奇怪地看了他一眼,見他好像并沒有什麼異樣,這才走到他面前,“皇上,怎麼了?”
話還沒有說完,蕭嶼便扯著的手腕,將往前一拽。
男人的力氣恢復得很快,夏倚照一個趔趄,兩個人的鼻尖就快要湊到一塊。
蕭嶼的眼神看著,墨的深眸暗涌,過了一會兒才沙啞著聲音問,“方才去見誰了?”
夏倚照聞言睜大眼睛,倒吸一口冷氣,推著他的肩膀便起,“你派人跟蹤我?”
就連皇上都未曾稱呼,眼睛里面染著一層薄怒。
這一點踩到了的底線。
男人的角繃直,過了一會兒才說:“不是,方才我出去找你,看到你和他雙雙進了林之中……”
“什麼林!不過也就是一僻靜地方而已,你說的好像我們兩個做了什麼事一般……”夏倚照覺得他用詞刁鉆,下意識地糾正他。
看著他蒼白的臉,心又了一瞬。
畢竟也是為了自己才傷,的聲音和下來,“只是去跟他說清楚一些事。”
蕭嶼聞言也不再糾纏,點了點頭,臉上卻沒什麼表,“跟我解釋做什麼?我又不重要。”
夏倚照一陣沉默。
之后有些打量地看著他,“皇上萬金之軀,自然是重要的。”
猜你喜歡
-
完結181 章
鳳隱天下
洞房夜,新婚夫君一杯合巹毒酒將她放倒,一封休書讓她成為棄婦!為了保住那個才色雙絕的女子,她被拋棄被利用!可馳騁沙場多年的銀麵修羅,卻不是個任人擺布的柔弱女子。麵對一場場迫害,她劫刑場、隱身份、謀戰場、巧入宮,踩著刀尖在各種勢力間周旋。飄搖江山,亂世棋局,且看她在這一盤亂局中,如何紅顏一怒,權傾天下!
17.9萬字8 43459 -
完結418 章
鳳逆九天:一品毒妃傾天下
她是將軍府的嫡女,一無是處,臭名昭著,還囂張跋扈。被陷害落水後人人拍手稱快,在淹死之際,卻巧遇現代毒醫魂穿而來的她。僥倖不死後是驚艷的蛻變!什麼渣姨娘、渣庶妹、渣未婚夫,誰敢動她半分?她必三倍奉還。仇家惹上門想玩暗殺?一根繡花針讓對方有臉出世,沒臉活!鄰國最惡名昭著的鬼麵太子,傳聞他其醜無比,暴虐無能,終日以麵具示人,然他卻護她周全,授她功法,想方設法與她接近。她忍無可忍要他滾蛋,他卻撇撇唇,道:“不如你我二人雙臭合璧,你看如何?”【情節虛構,請勿模仿】
109.7萬字8 73405 -
完結2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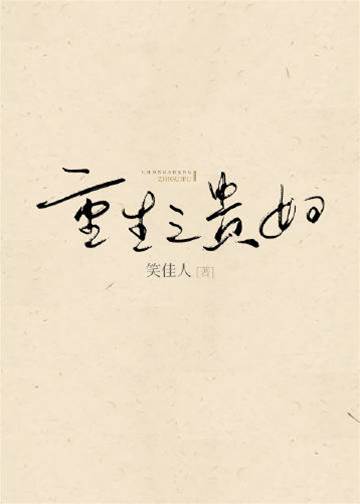
重生之貴婦
人人都夸殷蕙是貴婦命,殷蕙也的確嫁進燕王府,成了一位皇孫媳。只是她的夫君早出晚歸,很少會與她說句貼心話。殷蕙使出渾身解數想焐熱他的心,最后他帶回一個寡婦表妹,想照顧人家。殷蕙:沒門!夫君:先睡吧,明早再說。…
66.6萬字8.71 18750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