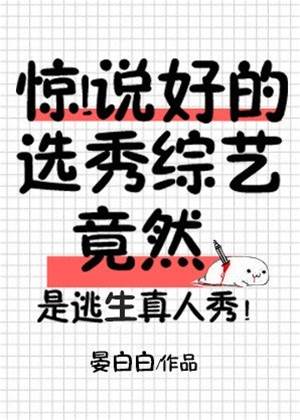《同居契約》 第70章 囚系 (1)
“不就是傷了指關節嗎?一點都不痛,”莊凌霄冷笑一聲,在聶長生的訝異憤怒的目里,左手突然扯下鞏固在右手指間里的鋁板,“當啷”的落地聲中,四個鋁板全部被莊凌霄丟在腳下,連同紗布也一同解了下來,原本已經止了的手被這麼魯的對待,新的洶涌出來,很快打了整只手。
“你瘋了!會弄二次折傷的!”聶長生驚呼著,里說不出心底復雜的。這個人,刻意的把傷勢弄得那麼可怖,刻意的讓自己心疼,是想留住自己的目多一點吧……
果然,莊凌霄冷聲笑道:“這些痛跟我出差回來發現你消失了的痛相比,本不算什麼!”他似乎不愿再回憶那段被黑夜籠罩下不管從哪個方向走,堅的墻就堵在黑暗的每一個角度,讓他無從下手,無力下手,只能四噴鼻的憤怒無助的日子,“你是不是以為我的這里不會痛,不會傷,任由你欺瞞哄騙?是不是!”他用淋淋的右手抵在自己的心口,鮮紅的在他白襯衫上印了一個又一個漉漉的印,擴大向聶長生質問的籌碼。
聶長生啞口無言,垂下眉睫,看著莊凌霄手里流淌的鮮,看著那一枚一枚印在襯衫上紅的手印,他的口一陣翻騰,那片紅刺傷了他的眼瞳。聶長生闔上了眼睛,一行淚水眼眶里滾落了下來,打了的睫,下了他的臉頰。
“你有沒有后悔離開我,有沒有!”莊凌霄憤怒的聲音砸在他的耳旁,敲打著他的心,“哪怕只有一秒鐘,后悔離開我,師哥?”凌厲聲里,竟然夾雜了一哽咽。
聶長生睜開眼,雙手慢慢的出,上了莊凌霄那只痕累累的右手,他嘆息著,輕輕的把瓣在這只繼續淌著的指腹上,將悔過的吻印在每折傷了的指關節上,低低的承認道:“有,有過。”
“呵!”莊凌霄發出一聲冷笑,吊起半眉,目肆無忌憚地盯著這個贖罪的男人,帶的手指上這張時常出現在夢中的臉,里卻說著殘酷至極的話,他說,“太遲了,你的悔恨來得太遲了!我要用我的方式,讓你知道不是所有的悔恨都可以被諒解的!”手用力一推,將聶長生推到在躺椅上。
“你要怎樣恨我都可以,現在,先讓我給你包扎傷口吧。”聶長生掙扎著,試圖坐起來將莊凌霄淋淋的手理好。
然而這一次的莊凌霄再次把語言流的渠道掐斷,用流的渠道取而代之了。
流的花樣較之從前變多了,聶長生浮浮沉沉在莊凌霄制造出來的甜與痛苦里,載浮載沉在孽海的旋渦中,在死仙的流中昏了幾次,每次醒來,都以為酷刑終于結束了,卻不知道新的一折磨才剛剛開始。
等到聶長生從昏迷中蘇醒過來時,眼前是一片橘的昏黃。
側躺的姿勢已經很久沒有過了,一個人睡的話,他還是習慣仰躺。
此刻正側躺著的聶長生,只需一睜眼,就看到了睡在旁邊的莊凌霄。
睡著了的莊凌霄了很多銳氣和凌厲,眼睛合著,沒了霸道的視線,閉的更不可能得理不饒人,他就這麼安安分分的躺在自己的邊,呼吸悠長,睡得正沉。
如果不是渾的酸痛席卷到四肢百骸,聶長生幾乎以為這只是一場帶了的夢境。
軍事飛機上與莊凌霄糾纏在一起的一幕幕像電影中的慢鏡頭似的,一幀一幀的從腦海里浮現出來了。
抵死的纏綿,不休的jiao媾,瘋狂的速度,yin的姿勢……每一幕都足以令聶長生渾發熱,栗不止。
所以現在的才迎接了難以言喻的痛,聶長生皺著眉,尤其是那一,太久沒有被拜訪,卻被莊凌霄惡意地瘋狂對待,不痛才怪呢。
聶長生抬起一手,掀開了被子,一陣微弱的窸窸窣窣聲音霍然響起。
他愕然地看著自己的手腕上,不知什麼時候多了一條細細的鏈子,鏈子的另一頭系在樁頭的木樁里,上頭還掛了一個電子鎖。昏暗的室,聶長生也看不清鏈子的質地,只覺得冰冰涼涼的扣在自己的手腕上,或許是睡覺的時候硌著,手腕上現出了一條淺淺的鏈條紅印。
原本掀被子牽扯到了上的疼痛令聶長生非常不舒服,現在發現自己的手腕上多了一條不應存在的鏈條,聶長生皺起了眉,不悅的心更是一落千丈。
他的枕邊人雖然睡得沉,卻是一個淺眠的人,稍有一點點的風吹草,就能醒過來。
莊凌霄睜開眼睛時,看到的正是拉扯著鏈條的聶長生氣餒的臉容。
“你醒了。”莊凌霄的聲音還帶著濃濃的倦意,他跟從前那樣,沒有聶長生睡在邊,他就失眠,當然,他也沒有吃藥看醫生,反正都沒用,所以聶長生離開了多久,他就失眠了多久,這還是半年來,他第一次睡得那麼香甜的呢。
只有躺著聶長生的邊,摟著他不怎麼高的溫,嗅著他的氣味,才能徹底的消除他心的惴惴與焦灼,沒有這個人的日子,他仿佛失去了人生的目標。
藍迤邐曾經想用的溫去化他對聶長生的執念,可惜不管做了什麼,做了多,莊凌霄都無法將放在聶長生的位置上。
不是聶長生,就不行!誰也不能站在他的邊,睡在他的側!
“嗯。”聶長生悶悶的回了一句,繼續拉扯那條細細的鏈子,故意弄出讓枕邊人難以睡的聲音。
“你扯它干嘛?”莊凌霄摟著他,讓他的頭在自己的口,他只要一手,就能把他環在懷中,滿滿當當的,他就哪兒也去不了了。
“我要起床。”聶長生垂著眼簾說,他的聲音喑啞得像一把失去助弦的古琴,彈奏不出悅耳的聲音,可落在莊凌霄的耳朵,這沙啞的音線無疑就是對他驚人的持久力的贊賞。
哪個男人不喜歡別人對自己這種能力的稱贊呢?
“這麼早起床做什麼,再睡一會。”莊凌霄邊扯出一笑意,用包扎了繃帶的右手上了聶長生拉扯的手,聶長生果然停下了作。
“我了。”聶長生挲著繃帶,低聲道。
那場可怖的運消耗了聶長生太多的力與水分,流了這麼多的汗,嗓子喊到幾乎冒煙,現在的他迫切需要一杯水緩解嚨里的焦。
“你等等。”莊凌霄低笑著掀被起床,在聶長生的邊蜻蜓點水似的吻了一下,才踩著歡快的腳步離開了臥室。
聶長生抿了抿,舌尖嘗到了留在上專屬莊凌霄的氣味,他翕了翕眼睛,抬起了頭,才有心打量四周,這是一個非常陌生的臥室,約莫二十來平的空間,不算很大,床卻大得有點離譜,幾乎占據了房間一半的空間,寫字桌擺在書柜的旁邊,這里大概是臨時的住,男人又都不化妝,所以桌面上沒放什麼東西,聶長生比了一下鏈子的長度,書柜前還算是他可以活的范圍,房間沒有鋪地毯,不過中央掛燈卻很奢華大氣,很有時尚的氣息,墻壁上亮著昏暗的燈是荷花形狀的,致漂亮,橘的線像一塊朦朧的薄紗將眼前的一切都鍍上一層朦朧的澤,整個臥室的格調顯得溫馨而和,讓人很舒服。
如果手腕上沒有那跟細細的鏈條鎖住的話,聶長生并不討厭這間臥室。
莊凌霄很快就返了回來,他手里握著一瓶礦泉水,那是一瓶聶長生從未見過的瓶子,昏暗中上面印的字雖然不怎麼清洗,但卻不是中文和英文,聶長生知道莊凌霄對飲食很挑剔,不太可能喝雜牌的礦泉水,看來,這是一個他相當陌生的地方,或許連語言都不通的地方。
語言不通,他想去哪里,都沒有人可以幫助。
果然是一個適合囚人的地方。
莊凌霄擰開了礦泉水瓶蓋,然而微微仰起頭,喝了一口礦泉水。
聶長生看著他,直到莊凌霄俯過了子,含著礦泉水的在他的瓣前,他才知道,男人是想用口度水給他解。
雖然什麼都已經做過了,可用這種方式解,聶長生還是覺得有點難為。
“我自己喝……唔!”聶長生一張口,瓣便失守,落了莊凌霄的肆的上,纏追逐的舌里,一大半的水溢出了兩人的角,到了彼此的襟上,還有一些灑在被子上,偏偏兩人一點都沒有覺察,繼續在吻中吸取著水分。
一瓶中等型號的礦泉水見底后,聶長生才算解了,然而一床的被子卻了一大片,不能再蓋了,莊凌霄心很好地換上了另外一床新被子,摟著聶長生睡回籠覺。
猜你喜歡
-
完結213 章
走紅后豪門大佬成了我粉頭
江放因體質弱從小被家人送去寺廟當和尚,後來被老和尚趕回家,碰巧練習生出道的弟弟正準備參加一檔綜藝,需要邀請一位親人參加。 看在錢的面子上江放答應參加,誰知弟弟自帶黑熱搜體質,兄弟倆參加綜藝的消息剛在網上傳開。 黑子:怎麼什麼低學歷的人都能上綜藝,碰瓷王江齊這次嫌一人不夠,打算帶著他哥組個碰瓷組合嗎? 江?人送外號高冷校草學神?放:? ? ? ? 你們怕是不知道什麼叫碰瓷,傷殘那種。 節目開拍後 “臥槽,怎麼沒人說江齊的哥哥長這樣,這顏值我能舔壞無數隻手機!” “是我眼花了?為什麼我會在一檔綜藝上看到我們學校的校草。” “說江放低學歷的人認真的嗎,燕大學神了解一下?” # 只想撈一筆項目啟動資金沒想過混娛樂圈的江放爆火後,收穫了土豪粉一枚和後台黑粉連發的99條恐嚇私信。 土豪程肆:等他再發一條。 江放:? 土豪程肆:湊個整送他上路。 江放:順便撒點紙錢,走得安詳一點 。 # 程肆的妹妹為某明星花百萬砸銷量驚動了程家,程父程母擔心女兒被騙,讓程肆幫忙照看。 程肆在監督的過程中,學會了簽到打榜,學會了給愛豆應援,學會了花錢砸銷量,還學會了監守自盜。 妹妹:說好監督我的呢,你怎麼就成了我愛豆的粉頭? 表面高冷學神實則壞心眼受X表面霸道總裁實則老幹部攻
48.7萬字8.18 10825 -
完結27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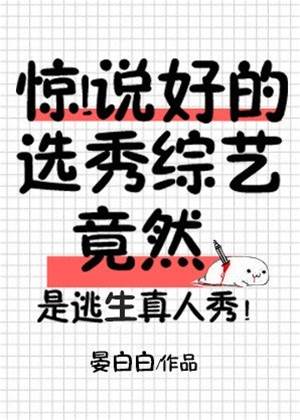
驚!說好的選秀綜藝竟然
某娛樂公司練習生巫瑾,長了一張絕世美人臉,就算坐著不動都能C位出道。 在報名某選秀綜藝後,閃亮的星途正在向他招手—— 巫瑾:等等,這節目怎麼跟說好的不一樣?不是蹦蹦跳跳唱唱歌嗎?為什麼要送我去荒郊野外…… 節目PD:百年難得一遇的顏值型選手啊,節目組的收視率就靠你拯救了! 巫瑾:……我好像走錯節目了。等等,這不是偶像選秀,這是搏殺逃生真人秀啊啊啊! 十個月後,被扔進節目組的小可愛—— 變成了人間兇器。 副本升級流,輕微娛樂圈,秒天秒地攻 X 小可愛進化秒天秒地受,主受。
89.5萬字8 857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