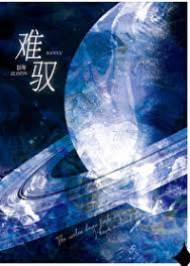《晚風漪》 第36章
賀銘推開飯店包廂門,把檢察院和律所幾個男人醉醺醺的吆喝聲鎖在門后。幾個剛畢業的實習生說說笑笑結伴從洗手間回來, 看到他后立刻斂了笑鬧, 畢恭畢敬站定。
“賀律好。”
賀銘舉著手機,點點頭往外走, 聲音有些嚴肅:“……是一件讓我覺得很詭異的事,我猜或許和當年的離開有關系。”
果不其然, 他話音方落, 國際長途的那邊淡淡呼吸聲停滯了幾秒鐘。大概是為了照顧老朋友的緒,一向嚴苛的賀律故作輕松地聳聳肩,緩和一下氣氛:“一時半會兒可能說不清楚, 這國際長途的費用你可得報銷。”
“今天中午我們律所和幾位檢察一起聚餐, 大家都喝醉了……”
飯桌上照例開始拼酒,幾旬酒后,律師們結伴離席, 只留下一群醉醺醺的大老爺們兒。
一群酒足飯飽的男人, 討論最熱烈的難免就是那幾個話題——票子和妹子。
賀銘一會兒得開車,所以滴酒未沾, 也懶地參與,便坐在一邊有一搭沒一搭地聽著。
幾下來,話題已經從某個大腰細的明星轉移到了邊的人, 一個律師大著舌頭說:“……欸你們發現沒, 東城區警局前幾天新來的那個警,長得賊……賊拉好看。”
一群人中除了賀銘之外,最年輕的李檢察喝得滿臉通紅, 聞言愁眉苦臉地回憶:“哪個啊?”
“就……就小孟啊,上次那個室搶劫案可不就是去抓的人嗎,那手那大長,絕對是北京城警局一枝花。”
另一個檢察也跟著附和:“對對對,小孟真漂亮,我現實生活見過的妹子里,屬最好看。”
喝醉的男人最攀比,李檢“嗤”了一聲,不屑道:“小孟好看是好看,不過還是比不上我見過的。應該是五年前吧,那時候我大學剛畢業,還是個小警察,沒有進檢察院。我工作的第一天見到一個報案人,嘖,那張臉,演電影都綽綽有余。”
“切,就屬你特麼吹牛,要這麼說,我上次去辦案還見著仙下凡了呢,編唄!”
李檢皺著眉頭辯解:“真的!那姑娘當時也就二十出頭吧,長得實在是太讓人驚艷了,那眉眼,那鼻子,比現在很多明星都漂亮。可惜我當時被那個案子整懵了,等人走了很久才想起來忘了要聯系方式,后來懊惱了好多天。”
周圍幾個男人眼神都沒什麼變化,顯然是不相信。
李檢急了,為了證明表示自己沒在說謊,于是回憶了很多細節:“那天正好是我第一天工作,是五年前的六月十七號。是在傍晚的時候來的,穿著打扮非常致。姑娘手腕上戴了一串銀的手鏈,底部墜著一朵火紅的玫瑰,反正一看就是有錢人家的小孩兒。”
聽到這里,一旁懶懶散散的賀律師忽然皺起了眉頭。
玫瑰手鏈……在他的記憶中有過這樣一條手鏈。
賀銘記得,大概是大三或者大四那年,紀悠之有一次說過,江澤予在外面兼職了幾個月,給謝昳買了條很貴的手鏈。
那條手鏈設計得確實好看,謝昳幾乎天天都戴在手上——鉑金底鏈,墜子是一朵雕刻得相當致的紅玫瑰。舟舟還因此發過空間,酸怎麼沒有人給送這麼好看的禮。
而且,五年前二十出頭、打扮致、長相漂亮、家境優渥的孩子,也全都能對上。
賀銘心里覺得或許不是巧合,于是不聲遞了個話頭:“然后呢?”
李檢聽到有人捧場,來了傾訴,眉飛舞道:“……但報案的容相當古怪,說有人綁架,企圖對實施/侵犯,可案發時間距離報案姑娘當天,竟然長達七年,是在念初三的時候。”
“初三欸,還是個未年!我當時一邊覺得憤怒,一邊又覺得詭異,一樁七年前的侵案,為什麼要時隔這麼多年才來報案?如果案不嚴重,都已經超過公訴時效了。”
“當時那姑娘臉很差,看著死氣沉沉的,可神卻極為冷靜。和很多歇斯底里的報案人不同,的敘述非常平緩,說起施暴人當年對犯罪的全部過程時,從頭到尾表都沒有變過,簡直像是在說一件無關痛的小事。”
賀銘心下一凜,抓住了重點問道:“也就是說十二年前,在念初三的時候被人綁架、侵未遂?有沒有的時間點和案發地點?”
李檢回憶了一會兒,說到:“……有,因為這是我畢業進警局接到的第一個案子,印象非常深刻。姑娘陳述中說,案發時間是在初三畢業的暑假,地點……我想一想,對,是在北京城東那一帶一個當時剛剛被推平、等待開發的廢棄工廠。說施暴人曾經約過出去玩,沒有同意,結果在補習班門口被施暴人帶人綁架到了那個廢棄工廠。那人企圖對實施/侵犯,好在冷靜地等到他有所松懈后,掙開逃跑了。”
賀銘的眉頭皺得更加厲害,一只手梭著棉質桌布,低聲問道:“你可知道施暴者……是誰?”
李檢這次猶豫了許久才出聲:“綁架、侵未年人是重罪,一般追訴時效超過十年。我準備給立案,但卻不說自己的名字,只說了施暴者的名字。”
話至此,他稽地四張了一下,低聲音神神道:“說……施暴者,是周子駿。賀律,你們賀家和周家應該很悉,周子駿你知道吧?就是北京城周家周奕的獨生子!之前在說案發過程的時候特別平靜,臉上的神古井無波,可在說到施暴人姓名的時候,整個人卻開始劇烈抖起來,眼底的憤怒和恨意猛烈到隔著張桌子都令我頭皮發麻。我還記得紅著一雙眼睛,一字一頓地告訴我,像是把全部的希在我的上:‘他周子駿,北京城周家的周子駿,警察哥哥,您能不能幫幫我,幫我抓住他,好不好?’”
飯桌上,幾個律師和檢察們聽慣了各離奇的案件,對于一個侵未遂的案子實在提不起興趣,大多醉醺醺地聊起別的來、也有的睡死了過去,只有賀銘還聽得專心致志。
但凡有一個聽眾,李檢也得講完故事:“你猜怎麼著?接下來就是最古怪的事,我仔仔細細寫完筆錄,告誡那姑娘,想要立案必須要有害者的姓名。姑娘猶豫了一會兒,方要開口,警察局門口忽然進來好幾個人。為首那個是的父親,個子很高、非常氣派。他面不虞地走過來,從桌上拿走了那份筆錄,然后吩咐后的幾個人生生拉走了那姑娘。”
“那天傍晚的況非常混,警局里沒有其他報案人,值班的警察也沒有幾個。我正想呵斥他們在警局鬧事,結果警察局局長親自過來,哈著腰跟那人打了招呼,接著便過來警告我不要多管閑事。”
“偌大的警局里,姑娘當時就崩潰了,拼命掙著跑過來,再也沒有了方才面的模樣。眼底紅、滿臉是淚地跑到我邊,一雙眼睛倔強又痛苦:‘請您幫忙立案,我謝……’,可話沒說完,卻被父親狠狠地扇了一掌。我后來猜測,他們家里應該也是做生意的,大概是懼怕周家的權勢吧。”
李檢說著有些唏噓,皺著眉頭醉意凜然,“……我當時也是一下懵了,竟然就眼睜睜地任由被家里人拉走。那姑娘臨走前眼里的絕和痛苦,我到現在偶爾做夢還能想起來……所以那樁案子后來也沒有記錄,除了我,并沒有任何人知道。好在善惡終有報,就在來報案的半年之后,周子駿被人匿名舉報,現在還沒從牢里出來呢,真是活該。”
國際長途那頭,細微的電流聲作響,賀銘說到這里,提出了自己認為這件事里最詭異、最不符合邏輯的地方。
“……我覺得那個報案人十有□□就是謝昳,但奇怪的是,明明案發時間是十二年前,也就是念初三的時候,可為什麼要等到大四畢業才去報案?”
“而且據時間節點來看,謝昳五年前的六月十七號去警局報案,被謝川攔下后,七月三號就飛去國。由此可見,這件事或許和當年的離開有著直接的聯系。”
“再者,謝昳離開半年后,周子駿被人匿名舉報,周家這麼多年都找不出背后的人。”
出于律師的謹慎,賀銘只陳列了一些有關事實,并沒有說出自己的推測:“或許謝昳當年的離開,有我們不知道的,我聽舟舟說過,當年真的對你很上心,應該不可能無緣無故一走了之。”
猜你喜歡
-
完結91 章

樑少的寶貝萌妻
【暖寵】他,宸凱集團總裁,內斂、高冷、身份尊貴,俊美無儔,年近三十二卻連個女人的手都沒牽過。代曼,上高中那年,她寄住在爸爸好友的兒子家中,因爲輩分關係,她稱呼樑駿馳一聲,“樑叔”。四年前和他的一次意外,讓她倉皇逃出國。四年後,他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而她歸國後成了正值花樣年華。樑駿馳是她想拒絕卻拒絕不
14萬字5 38722 -
完結517 章

婚不設防:帝少心尖寵
日久生情,她懷了他的孩子,原以為他會給她一個家,卻冇想到那個女人出現後,一切都變了。靳墨琛,如果你愛的人隻是她,就最好彆再碰我!
92.1萬字8 67357 -
完結2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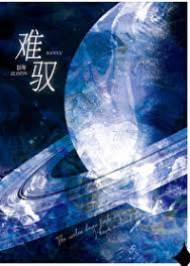
難馭
檀灼家破產了,一夜之間,明豔張揚、衆星捧月的大小姐從神壇跌落。 曾經被她拒絕過的公子哥們貪圖她的美貌,各種手段層出不窮。 檀灼不勝其煩,決定給自己找個靠山。 她想起了朝徊渡。 這位是名門世家都公認的尊貴顯赫,傳聞他至今未婚,拒人千里之外,是因爲眼光高到離譜。 遊輪舞會昏暗的甲板上,檀灼攔住了他,不小心望進男人那雙冰冷勾人的琥珀色眼瞳。 帥成這樣,難怪眼光高—— 素來對自己容貌格外自信的大小姐難得磕絆了一下:“你缺老婆嘛?膚白貌美…嗯,還溫柔貼心那種?” 大家發現,檀灼完全沒有他們想象中那樣破產後爲生活所困的窘迫,依舊光彩照人,美得璀璨奪目,還開了家古董店。 圈內議論紛紛。 直到有人看到朝徊渡的專屬座駕頻頻出現在古董店外。 某知名人物期刊訪談。 記者:“聽聞您最近常去古董店,是有淘到什麼新寶貝?” 年輕男人身上浸着生人勿近的氣場,淡漠的面容含笑:“接寶貝下班回家。” 起初,朝徊渡娶檀灼回來,當是養了株名貴又脆弱的嬌花,精心養着,偶爾賞玩—— 後來養着養着,卻養成了一株霸道的食人花。 檀灼想起自薦‘簡歷’,略感心虛地往男人腿上一坐,“叮咚,您的貼心‘小嬌妻’上線。”
34.9萬字8.18 1069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