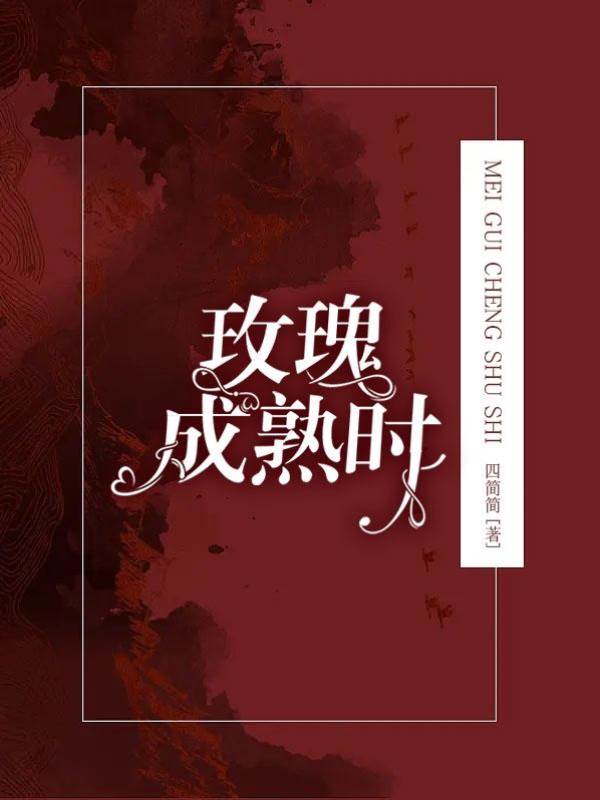《請你留在我身邊》 第44章 爬樹追媳婦兒
迎晨子, 不像時候,雖馨香,但青猶存。如今是真真兒的人了。不算骨,但條子順, 勝在高挑勻稱,有的部位, 都是男人喜歡的地兒。
厲坤頭埋在里面, 有點兒失控。
迎晨起先還能忍,忍無可忍了, 一聲嚶嚀口,厲坤這才滿意抬起頭,一臉壞笑。
“你老是喜歡在這種地兒弄, 煩不煩啊。”迎晨不滿。
“你煩了?”厲坤角,“我看你舒服啊。”
迎晨抬腳就朝他肩頭去, 這個姿勢恰好自曝其短,厲坤盯著,眼睛都紅了。一禮拜不見,他不住, 把人扛起就出了浴室。
兩小時后,被子大半邊掉在地上,床單也到是被揪旋渦的形狀。迎晨趴在床上, 厲坤趴在上。
兩個人,著氣兒,心跳隔著骨骼嘭嘭狂蹦。
厲坤側著頭, 被汗水潤的頭發兒,一縷一縷地夾去耳后,直到這張干凈清秀的臉蛋全了出來。
“小晨。”厲坤低低。
“嗯。”迎晨眼睫都睜不開,敷衍地應了聲兒。
厲坤的臉,“難?”
“嗯。”
“那我再讓你舒服一下?”
迎晨翻了個,不理。
今晚好像有點不一樣,厲坤能覺到。
迎晨瞇了一小會兒,恢復了神,裹了件日式和服式樣的睡下床洗漱。
厲坤來了癮,什麼都沒穿,坐去飄窗上點了煙。
迎晨在浴室問:“客廳里的那些鞋墊都是你買的?你買它們做什麼?”
“來的路上,瞧見一老在天橋上賣這些。”
農歷新春將至,天寒地凍,夜晚十一點還下起了雪子。厲坤今天是打車來的,想著迎晨也沒回,一個人無趣,干脆提前下車散散步。
這位老七十多歲,一頭花白頭發,瘦得都沒形兒了,就這麼坐在一張小馬扎上,抱著子等候生意。怕城管抓,所以只用油面塑料袋鋪地上,城管來了,就能迅速收起逃跑。
厲坤經過,本是隨意一瞥,但后頭又倒退回來。
實在于心不忍,便把鞋墊全買了。
“不貴,總共才一百二十塊錢。”厲坤往窗戶外吐煙,星火明暗微閃,夾在他指間。“老人家掙個錢不容易,這都是手工做的,一雙就賣五塊。”
迎晨笑他:“善良男孩啊你。”
厲坤彈了彈煙灰,也笑:“當時我在想,如果換做你,一定也會這樣做。”
“你別把我想太好啊,”迎晨洗漱完出來,神神的,“我可小氣摳門守財奴了。”
厲坤掐了煙,又往外呵了呵氣,才對招了招手,“到我這來。”
迎晨順從,一肚子的壞水兒,爬到他大坐著。
厲坤著的臉,眼底含了。迎晨歪著腦袋,勾著眼兒對他笑。
人之間的曖昧,無聲勝有聲。
迎晨的和服睡往下,溜了左邊的肩膀,圓潤甚是好看。
厲坤手,從這半邊敞開里探下去,在上膩歪著了一把,然后飛快收手,臉不紅心不跳的,好一個道貌岸然偽君子。
迎晨哪肯吃這樣的虧,瞪著杏眼兒,毫不手地抓住了他又立正的槍把,不輕不重的掐了兩下。
“嘶——”厲坤擰眉。
“下回你再弄我,我就弄它。”迎晨抬著下,像個王陛下。
厲坤忽的笑了。
他眾多表里,迎晨最喜歡他漫不經心的笑,有點張狂,笑的時候還會微微瞇雙眼,愣是能從里頭瞧出個三分輕佻,男人亦正亦邪,最是致命迷人。
就像此刻。
迎晨心有點兒蹦,心思一起,便收不住沖。
看著他:“厲坤。”
他有認真聽,“嗯?”
迎晨說:“我想嫁給你。”
萬俱寂,黑夜靜止。
厲坤著,眼神沒躲,沒藏。
但迎晨還是從里頭看出了一茫然以及不確定。哪怕一閃即逝。
“我鬧著玩的。”迎晨咧傻笑,輕松無所謂。
審時度勢,太會給自己找臺階下了。
良久,厲坤才極淡地應了一聲:“嗯。”
迎晨又陷了糾結。
這個嗯是什麼意思?愿意?還是敷衍?
厲坤坐直了些,輕輕拍了拍的,“很晚了,睡覺吧。”
兩人一先一后上了床,迎晨先是背對他,枕著右手側臥。過了一會,厲坤就箍住了的腰,把摟進了懷里。
背,有呼吸在脖頸間輕掃。
兩人之間,好像陷了一種古怪詭異的沉默里。
好在一覺醒來,這種覺拂了個干干凈凈,又都恢復自然了。
厲坤昨兒來的時候,帶了蛋和面。他一向起得早,松松垮垮的套了件T恤,便在廚房烙蛋餅。
迎晨被香味兒勾得異常興,圍著他左瞧瞧,右看看,還時不時地他屁。
“哎呀,你這翹而不膩,一掌下去還會回彈呢!”
厲坤笑得半死,“別鬧別鬧,待會油灑出來了。”
相比食,迎晨更喜歡做食的人。踮起腳,咬著厲坤的耳朵說了一句話。
聽完——“呸!”
厲坤耳尖都紅了。
迎晨心滿意足,人真會上癮啊。
“今天想去哪兒玩?”厲坤把蛋餅攤在碗碟里,問。
“看電影。”
“行,中飯呢?”
“買菜回來做吧?”
這個厲坤很贊同。他是一個懂養生的男人,自己在部隊里練了一銅墻鐵壁,早看迎晨的某些生活習慣不順眼了。
慢慢來,早晚有一天把它們統統改掉。
厲坤心里盤算著。
吃完早飯收拾一頓,兩人便準備出門,電梯還沒來呢,迎晨接到了一通電話。
聽了幾句,迎晨就變了臉。
厲坤忙問:“出什麼事了?別慌。”
迎晨神思恍然,“我爸,我爸病了。”
———
迎義章心梗復發,不敢挪,還是讓醫生到家里來吊的水。
厲坤送迎晨回大院,到門口了,他端坐著,沒有作。
迎晨莫名來了較真的勁兒,問他:“你不跟我一起進去麼?”
厲坤看了半晌,移回目看前面,清清淡淡的嗯了聲,“你進去看看吧。”
聯想起昨晚自己求婚失敗,雖然本就是八分玩笑話,但厲坤的種種反應,與想象中相卻甚遠。
心里一團麻紗突然就擰了個死疙瘩。
迎晨心浮氣躁,賭氣似的兇了句:“你是不是就沒打算踏進我家?”
厲坤瞅了一眼,了,到底還是落了個沉默以對。他掏出煙盒,抖了支煙,往里一叼。接著就是劃火柴。
第一下沒劃燃,見了鬼的,第二下也熄火。厲坤索把家伙丟在儀表盤上,咬著煙過干癮。
迎晨就不是能藏事兒的人。厲坤這態度惱了的火,刷的一下冒出零星:“默認了?”
厲坤形一頓,猛地摘了里的煙,擰頭看著。
這目,沖,抑,甚至還有兩分痛苦。
“迎晨,能不能好好說話?”
“你好好說一個,我聽聽。”迎晨原話掄回去,眼神筆直。
對視數秒。
厲坤緩緩轉過頭,低聲說了五個字:
“這是你們家。”
而一聽那聲“你們”,迎晨便什麼都明白了。
冤有頭,債有主,哪有那麼容易忘記啊。
梗在厲坤心頭的那刺,一下,就出。他尚有理智與定力,能夠劃分清楚:人是人,但仇人,也洗不白啊。
迎晨忽的沉默,那顆心瞬間回歸零度刻線以下。
冷靜得可怕。
不是怪責,相反,甚至有點理解。
人之間的矛盾,如果是源于格、誤會這些非客觀因素,好辦,時間可擺平大半。偏偏是這種兩人心知肚明的事實。
它客觀,有存在,并且沒法兒解釋澄清。
它像一道鋒利的舊傷口,稍有變天,便疾發作,陣陣作痛。
迎晨推門,下車。
厲坤抓住的手腕,很。
迎晨掙。
他再抓。
迎晨再甩開。
像是復讀機,一遍一遍地心酸重復。
最后,迎晨還是沒能被留住。厲坤看著的背影立在冬日天里,落寞至極。
———
屋里。
迎義章安睡,崔靜淑靜悄悄地從主臥退到外面,很慢地合上房門。
一轉,就與迎晨撞了個正著,崔靜淑張驚慌,討好著打招呼:“回來了啊?”
迎晨嗯了聲,徑直走去看父親。
迎義章五十多歲,臉上皮紋路剛毅,一道道的,跟刀劃過似的。
迎晨挨著床沿兒坐,靜靜看著他。
不多久,迎義章睜開眼睛,慢聲說:“什麼時候來的?”
迎晨音輕:“接到徐伯伯的電話,就趕來了。”
迎義章雖在病中,但氣看起來還不錯,紅潤,健康。這也讓迎晨稍稍安了心。
猜你喜歡
-
完結80 章

我終于失去了你
十歲那年,許諾撞見父親出軌,父母失敗的婚姻讓她變得像只刺猬,拒絕任何人親近。高考完的一天,她遇見了莫鋮,這個玩世不恭的少年對她一見傾心。莫鋮與許諾完全是兩個世界的人,一個熱情如火,一個患得患失,卻在不知不覺中,許諾慢慢動了心。不料,一次生日聚會上的酒後放縱,莫鋮讓許諾失去了所有,包括心中至愛的親人。剛烈的許諾選擇了一條讓所有人都無法回頭的路,她親手把莫鋮送進監獄。多年後,兩人在下雪的街頭相遇,忽然明白了,這世間有一種愛情就是:遠遠地看著我吧,就像你深愛卻再也觸摸不到的戀人。 一場來不及好好相愛的青春傷痛絕戀。十歲那年,許諾撞見父親出軌,父母失敗的婚姻讓她變得像只刺猬,拒絕任何人親近。高考完的一天,她遇見了莫鋮,這個玩世不恭的少年對許諾一見傾心。莫鋮:你向我說后會無期,我卻想再見你一面。許諾:全忘了,我還這麼喜歡你,喜歡到跟你私奔。洛裊裊:我永遠忘不了十七歲的夏天,我遇見一個叫趙亦樹的少年,他冷漠自私,也沒多帥得多驚天動地,可怎麼辦,我就是喜歡他,喜歡得不得了……趙亦樹:我不知道要去哪里,什麼時候去,我只知道,我想見她,見到她會很開心。
33.3萬字8 6890 -
完結320 章

總裁娶妻套路深
原本只想給家人治病錢,沒想到這個男人不認賬,除非重新簽訂契約,黎晴沒得選擇,只能乖乖簽字,事成之后……黎晴:我們的契約到期了,放我走。傅廷辰:老婆,結婚證上可沒有到期這一說。--情節虛構,請勿模仿
86.9萬字8 37856 -
完結476 章

偏要
楚意沒名沒分跟了晏北傾八年,為他生了兩個孩子。 病得快死的時候,問晏北傾,能不能為她做一次手術。 卻只得到一句,你配嗎? 而他轉頭,為白月光安排了床位。 這個男人的心是冷的,是硬的。 瀕死的痛苦,讓她徹底覺悟。 身無分文離開晏家,原以為要走投無路,結果—— 影帝帶她回家,豪門公子倒貼,還有富豪親爹找上門要她繼承千億家業。 再相見,晏北傾牽著兩個孩子,雙眼猩紅:楚意,求你,回來。 楚意笑笑,將當年那句話送回: 晏北傾,你不配。
66萬字8 58866 -
完結14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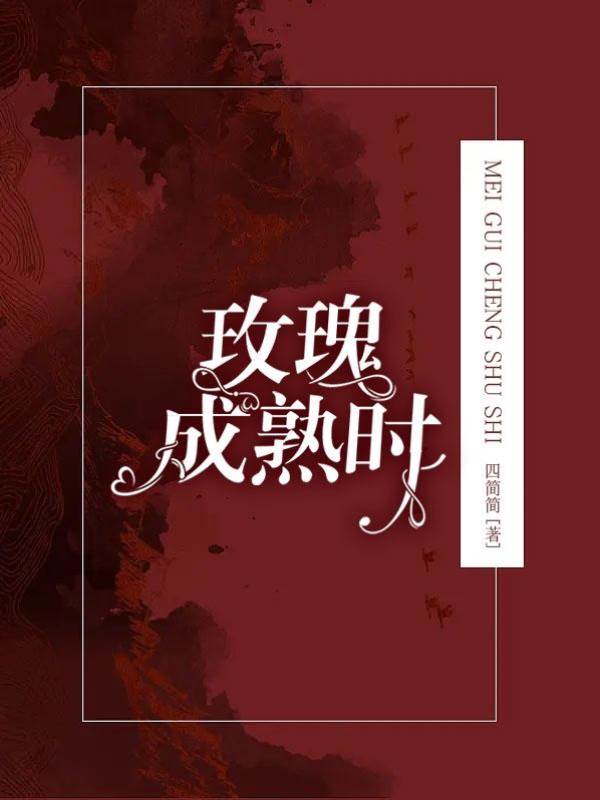
玫瑰成熟時
蘇落胭是京北出了名的美人,祖籍南江,一顰一笑,眼波流轉間有著江南女子的溫婉與嫵媚。傅家是京北世家,無人不知傅城深是傅家下一任家主,行事狠辣,不擇手段,還不近女色,所有人都好奇會被什麼樣的女人拿下。蘇落胭出國留學多年,狐朋狗友在酒吧為她舉辦接風宴,有不長眼的端著酒杯上前。“不喝就是不給我麵子?我一句話就能讓你消失在京北。”酒吧中有人認了出來,“那個是蘇落胭呀。”有人說道:“是那個被傅城深捧在手心裏小公主,蘇落胭。”所有人都知道傅城深對蘇落胭,比自己的親妹妹還寵,從未覺得兩個人能走到一起。傅老爺子拿著京北的青年才俊的照片給蘇落胭介紹,“胭胭,你看一下有哪些合適的,我讓他們到家裏麵來跟你吃飯。”殊不知上樓後,蘇落胭被人摁在門口,挑著她的下巴,“準備跟哪家的青年才俊吃飯呢?”蘇落胭剛想解釋,就被吻住了。雙潔雙初戀,年齡差6歲
23.5萬字8 17136 -
完結166 章

頂不住了,傅總天天按住我不放
[頂級豪門 男主冷傲會撩 女主嬌軟美人 後續男主強勢寵 雙潔]時憶最後悔的事情,就是招惹渣男未婚妻的小叔子。本來吃完就散夥,誰知請神容易送神難。一場意外,兩相糾纏。“傅先生,這事不能怪我。”傅霆洲步步緊逼,“ 所以你必須,我想你就得願。”傳聞中桀驁不馴的傅霆洲步步為營想偷心,其實最先入心的是他!
61.1萬字8.18 4030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