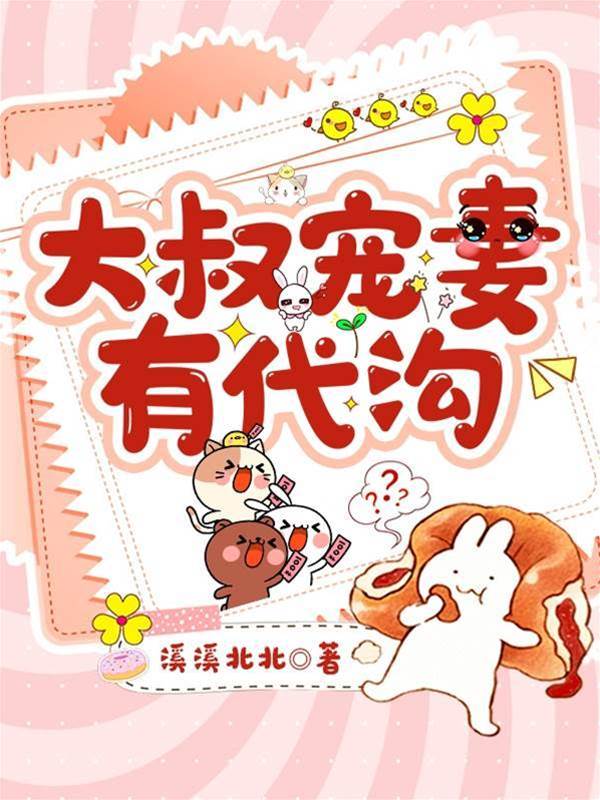《待你心里不挪窩》 第101章 薄情
易胭呼吸稍窒。
總等著蘇岸電話過來, 可臨到頭反而有點張。
唯恐電話接起, 打來電話的人不是蘇岸。
夜從落地玻璃窗外涌,手機屏幕夜里發出慘淡熒。
害怕太久沒接通話會自掛斷, 幾秒后易胭抓過手機接通放到耳邊。
沒出聲, 電話那頭的人也安靜。
一時間誰都沒出聲,連呼吸聲都聽不見。
片刻前易胭還猶疑打電話過來的人會不會是蘇岸, 此刻確定了,對方就是蘇岸。
可他沒有說話。
易胭坐在床上,雙手環, 下擱在膝蓋上。
原本有很多話問很多話講, 問他當年怎麼逃跑活下來的, 心暗策這麼多年,故意制造一個傻白甜的謊言,這些年他是如何過來的。
累嗎。
可等到接起電話,卻是一句也問不出了。
默契真是一種奇怪的東西, 二人保持著沉默,誰也沒打破這方寧靜。
也許是太安靜了, 易胭聽到了聽筒那邊的呼吸聲, 很輕很淺。
也不知過了多久,通話被掛斷, 耳邊那人呼吸聲被切斷的忙音取代。
易胭眼底緒寧靜,幾秒后眨眨眼, 沒哭, 也沒笑。
過了一會兒才將手機拿離耳邊。
又坐了會兒后易胭才有所作, 躺回了床上,睜眼干瞪天花板。
一分鐘慢慢閉上了眼睛。
睡意遲來,易胭思緒慢慢歸于混沌,清醒最后一刻,只剩一個念想。
不會讓他死。
也許是想通了什麼,竟是一夜好夢。
時間一晃又是兩天過去。
今日周凜到蘇岸房里喊他吃飯,推門進屋時,蘇岸背對門口著臂膀,正準備換。
后背白皙實,有舊傷,前幾日還沒好的傷口還纏著繃帶。
白紗布下滲,小臂上似乎有幾道新傷口。
周凜眉心一皺,沒待他多看,蘇岸已經穿好服。
黑襯衫遮擋了他視線。
蘇岸以前大多時候穿白襯,或許是最近傷原因,會沾,蘇岸最近都不再穿白襯,穿的一般是比較暗的服。
服穿好后蘇岸也沒轉,隔著床對窗口,骨節分明的長指慢條斯理系扣:“什麼事?”
周凜這才將門關上:“到早餐時間了。”
蘇岸嗯了聲,沒再說話。
周凜也沒離開,遲疑幾秒后問:“爺,你傷口是不是還沒好?”
這麼多天過去,按理來說蘇岸的傷口早該好了,可最近卻遲遲沒好。
蘇岸一般都是自己換藥,要不是方才推門進來正好遇上他換上,周凜有可能都不知道蘇岸傷口還沒好。
蘇岸沒怎麼當回事:“沒事。”
他手拿下帽架上的外套,穿上。
周凜皺眉,蘇岸已經轉往門口走去:“走吧。”
映沙和他們就住一個旅店,昨晚讓人他通知了他們兩個,今天一起吃個早餐。
早晨八點多,旅店一樓柜臺后連個看門的都沒有。
門口的流浪貓看到人站了起來走遠。
周凜跟在蘇岸側,往約定地點走去,路上人不多,偶爾傳來一聲狗吠。
街道轉角有家早餐攤,大概是開了有些年頭了,裝潢老舊,外面還掛著一個燈籠。
還沒走到門前,一眼便見坐在中間桌面向門口的映沙。
映沙一腳踩在桌底橫桿上,他們看到的同時也看到他們。
映沙抬起一邊手,懶洋洋朝這邊揮了揮。
蘇岸和周凜進門后落座。
說是吃早餐,映沙并沒有吃早餐,而是又在吃冰糖葫蘆。
錢宇剛起床不久,坐在旁邊,倒了杯水往里一灌。
旁還有兩位沒見過的生面孔,大概是做生意來的,其中一位長得似彌勒佛似的男人看映沙一直在吃山楂,道:“冰糖葫蘆有什麼可吃的,膩死了。”
聞言映沙眼風瞥了過去:“不好吃?”映沙噬甜,冰糖山楂上面是一層玻璃冰糖,甜度正是映沙喜歡的。
旁邊錢宇嗤笑一聲,這男人是撞槍口上了。映沙看著不容易生氣,說話總帶笑,看起來是最能開玩笑的一個,殊不知是最不能惹的一個。
果然下一秒映沙便將面前買的剩下的冰糖葫蘆推至那位客戶面前:“正好我吃夠了,你吃。”
“映沙小姐,你是不是聽錯了,我是不喜歡吃甜,不是喜歡吃甜。”
映沙稍歪了下頭:“我知道啊。”
男人一愣。
映沙角帶笑看著他,但雖是笑著,旁邊的人卻都能察覺出一森寒:“冰糖葫蘆可是我最喜歡的東西呢,我請你吃你不應該高興?”
錢宇抱手作壁上觀,角噙著笑。
與男人一同前來的另一個矮瘦的男子見場面不對勁,手肘撞了撞男人。
男人終于知道映沙不是開玩笑了,臉幾分僵。
誰都清楚生氣的映沙不能惹,的生氣可不是打罵幾句,而是一條命。他也清楚不能惹映沙,但沒想映沙這麼容易因為一句話生氣。
但所謂看人臉做事,男人這會兒也知道映沙生氣了,好歹也是生意場上老狐貍,立馬變了臉,討好拿過盤子上的冰糖葫蘆:“高興,怎麼不高興,能吃映沙小姐送的東西是我榮幸,我吃我吃。”
男人說完這句映沙也沒放過他,似笑非笑,目直勾勾盯著他,看他一顆顆山楂往里塞。
“冰糖葫蘆怎樣?”映沙這人就是變態,變態到格外喜歡惡意折磨人。
口腔里全是甜膩膩的味道,男人忍住搐的眉心,強撐起角:“好吃好吃。”
映沙這才作罷。
等折騰完人才若無其事看向蘇岸,仿佛剛看到他進來一般。
蘇岸就坐對面,背對門口。
映沙看著蘇岸面,道:“蘇警今天看著氣還是不怎麼好啊。”
這里坐的都是一幫亡命之徒,那個吃著糖葫蘆的男人聽到警二字軀一,立馬驚恐看向蘇岸:“警察?”
他指著蘇岸:“你們說他是警察??!”
錢宇道:“你急什麼?”
他嗤笑聲:“不過一個警察叛徒罷了。”
蘇岸無于衷,端起面前的水慢條斯理喝了一口。
周凜則是眉心一皺。
男人這一聽才放松下來:“哦,原來已經不是警察了啊,也是,就他們那行那點兒薪水,見我們這行來錢快的,肯定都心。”
說完估計想跟蘇岸攀上關系,說:“是不是兄弟?”
蘇岸卻是看都沒看他一眼,仿佛本沒聽到他說話一般。
男人有點尷尬,臉一僵。
映沙只笑不說話,錢宇漫不經心拍了拍手掌:“行了,吃飯。”
蘇岸最近胃口不是很好,早餐吃沒幾口便放下筷子。
他停筷的時候映沙咬著筷子看了他一眼:“蘇警,不多吃點?”
蘇岸低垂眼眸,淡淡一聲:“不了。”
“別怪我沒告訴你,多吃點啊,待會兒有得你折騰。”
蘇岸終于掀眸,眼風輕飄飄掃一眼。
映沙對上他視線,角勾了下。
蘇岸漠然移開目。
一行人吃完早飯往一個地方去。
這小鎮可以說在半山腰上,視野開闊,前后林木濃,是個逃生好去。
蘇岸沒走前頭,走在后頭,周凜跟他一起走后面。
山路坡度大不太好走,走著走著某一瞬蘇岸腳步忽然一頓。
他目不著痕跡掠過遠某一,同時腳步恢復自然,無人能察覺他不自然。
只有跟在他后的周凜察覺到異樣,加快幾步與蘇岸并肩。
前方那個長得像彌勒佛的男人一路上便沒停過,借著男人洪亮的說話聲,周凜用僅兩個人能聽見的音量與蘇岸對話。
“爺,不舒服?”
蘇岸雖然上負傷,但走起來毫無負擔,氣息都不紊一分,聲線還是很冷淡:“沒有。”
“不舒服了跟我說。”
“嗯。”
某一刻路過一個山時,映沙饒有興致停下了腳步。
打量這個山,不知又在想什麼玩意。
下一秒拐進里。
山高度一個男人高,寬度倒是很大能容四五人一起通過。
男人見映沙進,道:“映沙小姐,我們這還有正事兒干呢,怎麼在這兒坐下了。”
映沙坐在里一塊石頭上:“走累了,歇歇。”
映沙既然這麼發話,男人也不敢說什麼了,他還記得方才在小鎮上映沙驟變的緒,稍微忤逆一句這命便不在了。
所有人隨映沙進去。
里面沒有多余石頭,錢宇直接往地上一坐,其他兩位客戶看他這麼做,也跟著一起坐下。
除了蘇岸周凜還有跟在映沙邊的兩個男人。
映沙看著蘇岸:“嫌臟啊,蘇警。”
蘇岸很直接:“嗯。”
映沙哼笑一聲,接著道:“坐著有點無聊,要不我們來玩個游戲吧,怎樣?”
錢宇靠巖壁上,曲著一條,手掛在膝蓋上,吊兒郎當說:“好啊。”
男人也附和:“行行行。”
映沙就單純問一聲,不可能真的聽取他人意見。
忽然吹出一聲口哨,俏皮不已。
里的人除了映沙自己人,其他人都不知口哨多種用。
口哨聲剛出,沒在看的蘇岸忽然抬眸看,眼睛里倒是無波無瀾。
映沙說:“別急啊蘇警,我來的可不是上次讓你人嚇破膽的玩意兒。”上次阿茶村里映沙用蛇恐嚇過易胭。
蘇岸仿佛對說的話完全沒反應,不管是映沙話里代指的易胭,還是蛇。
他全都無于衷。
錢宇明顯也觀察到他的冷漠,角一勾:“真他媽薄啊。”
映沙也笑。
道:“不過我來了更好玩的東西呢。”
話音一落,山門口忽然有人推了一個人進來,人眼睛上蒙了黑布。
是易胭!
周凜在看到人的時候,眉心一皺,下意識看向了蘇岸。
然而側的蘇岸視線卻只是在人上停頓一秒。
下一秒仿佛不認識眼前人一般,視線不在上稍作停頓,視線冷漠掠過。
猜你喜歡
-
完結165 章
神秘老公不見面
為了回報家人十八年的養育之恩,她必須要代嫁,而那個男人半身不遂并燒的面目全非。 新婚之夜,她被灌下一碗藥,只能感覺到強壯的身體在她身上...... 從此,她日日夜夜伺候那個面目不清不能自理的男人! 傳說,霍家怪事之多,尤其是夜深人靜之時! “明明警告過你,晚上不要隨便走動,你看見不該看的,就要為此付出代價!” 他帶著邪佞的笑容緩緩而來將她逼迫于墻角。 烏子菁手執一張照片,同一張臉,卻出現在三個人身上? 究竟誰才是自己的老公,夜夜與她歡愛的又是誰?
40.2萬字8.44 62549 -
連載229 章

穿成影帝的炮灰前妻
楊千千是娛樂圈著名經紀人,她工作非常努力,最後她過勞死了。 然後她發現自己穿成了書裡和自己同名的一個炮灰,男主的契約前妻。 書裡原主因為不想離婚而下藥男主,然後原主懷孕,她以孩子為籌碼想要得到男主的感情,可是最後被男主以虐待兒童送進了監獄,最後也死在了監獄。 現在楊千千來了,對於男主她表示:對不起,我不感興趣。 楊千千穿書後的想法就是,好好工作,好好帶娃,至於孩子爹……親爹沒有那就找後爸!!! 某影帝:後爸?不可能的,這輩子你都別想了,這親爹他兒子要定了!!!
21.1萬字8 18876 -
完結517 章

婚不設防:帝少心尖寵
日久生情,她懷了他的孩子,原以為他會給她一個家,卻冇想到那個女人出現後,一切都變了。靳墨琛,如果你愛的人隻是她,就最好彆再碰我!
92.1萬字8 67349 -
完結1023 章

離婚後陸總他真香了
三年前的一場鬨劇,讓整個A市都知道了許洛婚內出軌,給陸澤臻戴了一頂綠帽子。三年後再次相見,陸澤臻咬牙切齒髮誓要報複,許洛冷笑不在乎。就在眾人都以為這兩人要刀風劍雨,互相對打的時候,一向凜冽囂張的陸總卻像是被下了蠱一樣單膝跪在許洛麵前,滿臉柔情:“許洛,你願意再嫁給我一次麼?”
189萬字8 37157 -
完結54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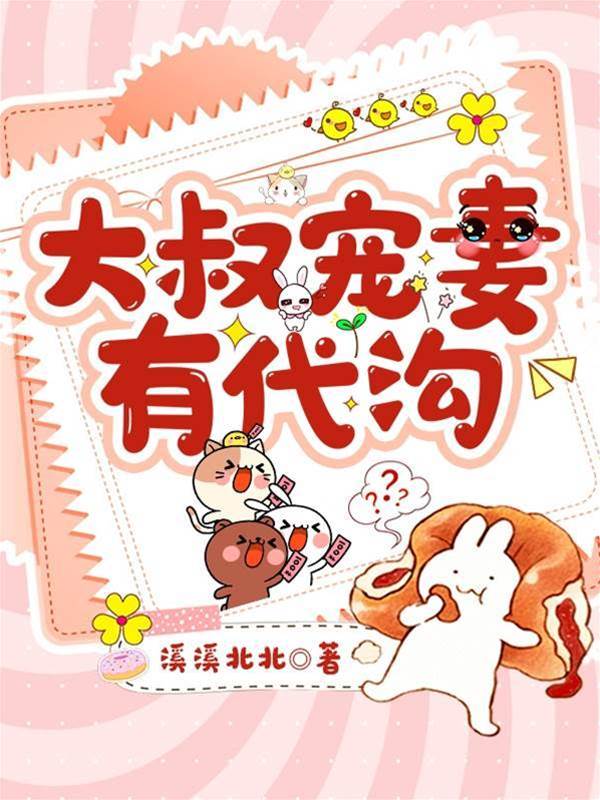
大叔寵妻有代溝
等了整整十年,心愛的女子終于長大。略施小計民政局領證結婚,開啟了寵妻之路。一路走下,解決了不少的麻煩。奈何兩人年紀相差十歲,三個代溝擺在眼前,寵妻倒成了代溝。安排好的事情不要,禮物也不喜歡,幫忙也不愿意… “蘇墨城,不是說,你只是一個普通的職員嗎?怎麼現在搖身變成了公司的總裁。” “蘇墨城,不是說,以前你根本就不認識我嗎,那你父親和我母親之間怎麼會是這種關系?”
55.3萬字8 5153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