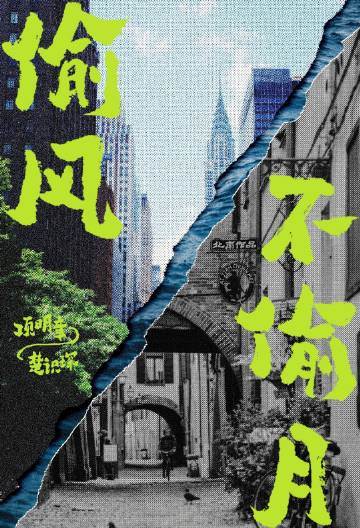《一屋暗燈》 第10章
預警,強制強制,是完完全全的強暴,沒有道理的強暴,接不了的勿點
關于宋星闌為什麼知道宋謹住在這兒,關于他為什麼會開得了大門,甚至關于他今天晚上為什麼會來這里,都已經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此刻,他用一把手銬,拷住了宋謹的手腕。
后頸上的手突然松開,宋謹立刻轉過,抬起尚且未錮的左手,拳頭往宋星闌的臉上砸。
朦朧淡薄的月融合在黑暗里,照得宋星闌半邊側臉微微發亮,他抬手接過宋謹的拳頭,另一只手拽著手銬一用力,在宋謹吃痛的氣聲里將他的兩只手徹底拷在了一起。
“宋星闌!”宋謹在宋星闌坐到他的腰上時低狠地出聲,“你要干什麼?!”
宋謹真的毫不懷疑,宋星闌今天會殺了他。
宋星闌雙手撐在宋謹耳側的床上,慢慢俯下,宋謹抬起被拷在一起的雙手抵住他的肩,酒氣越近越清晰,宋謹里本能的警惕就越強。
他聽到宋星闌開口,說了一串數字,宋謹意識到那是一個車牌號。
“什麼?”宋謹睜著眼,拼命想要看清宋星闌的臉,卻始終只能捕捉到一個廓,和他被電風扇吹得發的發梢。
“你同事沒跟你說他差點被車撞嗎?”宋星闌俯在宋謹上方,緩緩道。
于是關于唐閔手肘上的傷,關于他說的有輛車往他上撞,在此刻都得到了答案。
宋謹想都不敢想,他從來都沒想過,這件事居然和宋星闌有關。
“你有病嗎宋星闌!”宋謹終于反應過來,發著抖朝他吼,“你朝我發瘋就算了,關他什麼事?!”
宋星闌對他有再多的不滿再多的惡意,宋謹雖然不愿意承,卻尚且能夠理解幾分,只是他完全不明白為什麼要把毫無關聯的人牽扯進來,不論是對人還是對事,都看不出與唐閔有任何關系,那麼這樣做的意義在哪里?如果唐閔真的出了什麼事,宋謹都無法想象后果。
“你們關系不是很好麼。”宋星闌掐住宋謹的脖子,湊到他面前低聲道,“他要是出了什麼事,你是不是就不活了?你看看,現在他就是摔了一跤,你就急這樣了。”
宋謹不知道宋星闌的這種理解從何而來,他們的思維好像從來就不在一個頻道上,看待事的角度和方式總是天上地下,千差萬別。
“因為我跟你不一樣,我不會找無辜的人麻煩。”宋謹說,“宋星闌,你惡不惡心?”
“不惡心,就像你說的,我跟你不一樣,你是同,我不是。”宋星闌說著,掐了宋謹的脖子,聲音都狠上了幾分,“他有朋友,看不上你這種人,犯點賤,別一見了男人就不要臉。”
宋謹花了好幾秒的時間,才明白宋星闌里的“他”是誰。
他從來只把唐閔當朋友,可惜在宋星闌的眼里,好像對方只要是個男的,就能讓宋謹垂涎。
瘋子瘋子,真的是瘋子。
“宋星闌……”宋謹突然陷了怎麼也跳不出的絕里,就像一個龐大的漩渦,無論他怎麼解釋,怎麼自證清白,其實都沒有用。
“你放過我……”宋謹睜眼看著近在咫尺而他卻始終無法清的廓,在瀕臨窒息的斷續呼吸里艱難地開口,“我走得遠遠的行不行?”
宋星闌卻沒有回話,他稍稍抬起手,將宋謹的雙手往上推,按在宋謹的頭頂上方,另一只手往下,順著薄薄的T恤下擺探了進去,微涼的手心上了宋謹細瘦的腰。
明明脖子上已經沒有了遏制,宋謹卻在這一秒里到了滅頂的窒息,他僵著子,微微張著,卻仿佛被定,一句話都說不出來,連呼吸都微弱得可以忽略。
直到宋星闌的手指要到前,宋謹才如夢初醒,他啞著嗓子,聲音里是幾崩潰的抖,虛得連尾音都快聽不見:“你要干什麼?”
“你說呢?”宋星闌反問他。
話畢,他將宋謹翻過,從后起T恤,然后手指勾著宋謹的腰往下扯。
宋謹是在此刻才發現,原來從前的一切都不算什麼。
侮辱也好,恨意也好,報復也好,甚至那個暴的吻,都可以當做是宋星闌發泄和懲罰的途徑,宋謹不想再提,也拼命地想要避及,可他無法想象和宋星闌之間的,有關的一切。
那還不如殺了他,宋星闌是他的親弟弟啊。
“宋星闌——!”宋謹的側臉抵著枕頭,在宋星闌的制下無能為力地掙扎,他發著抖,“我是你哥!”
“我的就是我親哥,你是嗎?”宋星闌的手隔著上宋謹的部,他在宋謹的背上,低頭湊到他耳邊,問,“是的吧?”
“求你了……”宋謹的一顆心幾乎快要炸裂,往下一秒他都不敢多想,只是潰不軍地求道,“宋星闌,我求求你,別這樣,我保證以后再也不出現在你面前……我求你了……”
“別哭啊。”宋星闌的聲音里帶著鷙譏諷的笑意,“哥,做我的年禮不好嗎?”
他說:“別擔心,這次我不會再剪碎了。”
從那年被剪碎的生日禮,到宋星闌曾經說過的那句“惡心到我想把你弄碎”,宋謹才知道,這些意味著什麼。
有些報復的從一開始就有跡可循,只是宋謹低估了宋星闌的惡劣程度。
這一聲隔了十幾年再次聽到的“哥”,不啻于一把割裂所有理智與道德的利刃,刀尖抵著宋謹的心臟,要將他往深淵下推去。
宋星闌的手指順著探進去的時候,宋謹覺得有什麼東西裂開了,碎片砸在他的上,將他埋得一點都不剩。
宋謹趴在枕頭上,半闔著眼,茫然又驚懼地看著天窗外模糊的月,他的手腕早就掙得鮮外溢,腥味和手銬的金屬味摻雜在一起,冷冰冰的銹味。
他豆-丁-醬⑽⑷05⑼⑹⑹⑶⑺寧愿宋星闌殺了他。
從未經事的后因為本能的抗拒和的僵而顯得干難,宋星闌嘖了一聲,一手按著宋謹的腰,一手從自己的子口袋里出一個安全套,用牙齒咬開包裝袋,將套子戴在手指上,就著安全套里的潤重新往宋謹的后探去。
冰涼的安全套裹著手指強地深,宋星闌并沒有什麼耐心擴張,幾下之后他就將手指了出來,取而代之的是滾燙的。
宋謹以為自己已經不抱希了,可當后真正抵上那東西時,所有的恥和背德重新一涌而上,他突然支起手肘掙扎著要往前逃,卻被宋星闌箍住腰摁在原地。
“我求你了……”宋謹哭著說,“宋星闌,別這樣……求你……”
他很哭,可是在這樣走投無路的時候,眼淚就像那些岌岌可危的自尊,那些他勉強擁有的,不想失去的。
他的哀求從來不會起作用,宋星闌著宋謹的后背,強地將送進了他的里。
黑暗的視野像是被撕裂,出滿目猩紅,宋謹猛地仰起頭,無聲地張著,眼淚順著眼尾劃過側臉,掉在枕頭上。
一切都晚了,一切都完了。
宋星闌并不給他緩沖的時間,進之后便不容置疑地送起來,宋謹覺得后像是有一烙鐵,燙得他發痛,每一點細微的都是撕心裂肺的灼痛,痛得他一點聲音都不出來,痛得他快要把下的床單抓出裂痕。
老舊的床被撞得吱呀作響,在靜謐的夜里宛如,宋謹的背上淌滿了汗,多數都是因為疼痛,的肩胛骨在黑暗里若若現地泛著冷白的。
太疼了,疼到宋謹連絕和恨意都被下,只想求宋星闌輕一點。
可宋謹偏偏咬著牙一聲不吭,任憑眼淚流了滿臉,卻連半泣都不,更別說是懇求。
但宋星闌太了解宋謹的痛點所在,他一邊在宋謹的里狠頂,一邊咬著宋謹的肩,問他:“被親弟弟的滋味怎麼樣?”
“宋謹,你自己聽聽你下面的水聲。”
“你媽的房間就在樓下吧?”
宋謹怎麼都想不到宋星闌會在這個時候提起母親,一句話就像千噸重的洪水,輕輕松松沖破看似堅固的堤防,將宋謹所有的緒堆到極點,再拍散在水里。
而偏偏這個時候,過后里的某一點,恐怖的快陡然沖上脊柱,隨著近乎麻木的痛意織而上,清晰刻骨。
就像明知道罌粟帶毒,被迫著嗅了一口,而后眼見著自己臣服在它所制造的幻境之下,清醒地看著自己沉淪,輸給與生理的本能。
視覺在黑暗的線里被蒙蔽,將功能分散在其他的里,一切覺都被倍放大會,好像掉進熱浪起伏的水中,快與痛、息與悶哼、汗水與淚水、委屈與恥辱,每一個都是漩渦,淪浹髓,要他不能。
猜你喜歡
-
完結109 章
情予溫寒
一個(偽)性冷淡在撞破受的身體秘密後產生強烈反應然後啪啪打臉的集禽獸與憨憨於一身,只有名字高冷的攻。 一個軟糯磨人卻不自知的受。 一個偽性冷、偽強制,偶爾有點憨有點滑稽的故事。 為何每個看文的人都想踹一jio攻的屁股蛋子? 面對“刁蠻任性”又“冷漠無情”舍友,他該何去何從?
25.9萬字8 36849 -
完結12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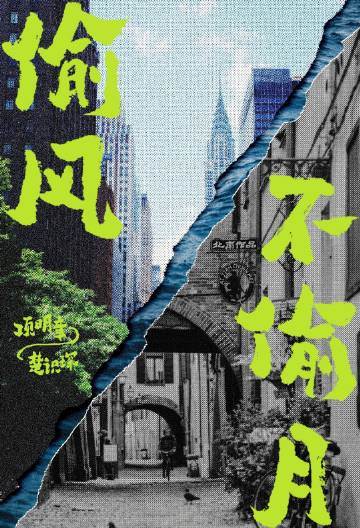
偷風不偷月
穿越(身穿),he,1v11945年春,沈若臻秘密送出最后一批抗幣,關閉復華銀行,卻在進行安全轉移時遭遇海難在徹底失去意識之前,他以為自己必死無疑……后來他聽見有人在身邊說話,貌似念了一對挽聯。沈若臻睜開眼躺在21世紀的高級病房,床邊立著一…
39.3萬字8 612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