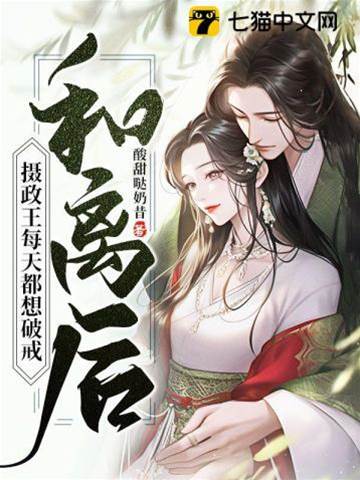《將軍帳里有糖》 第58章 娘親(下)
大火驚了整個大悲禪院, 一直燒到了天邊泛起了蟹殼青,這才算罷。
尼師們灰頭土臉地坐在寮室前小歇,那知客僧惠空衫被燒的襤褸, 滿頭大汗地盤坐在地。
“師父,這里頭的貴人什麼來歷?”一旁的小尼師忐忑不安地側頭,問的小心翼翼,“方才咱們去滅火,來了三四十人, 說是的護從, 把咱們趕到了一邊兒,自個兒滅火去了。”
惠空勉強保持著鎮定,念了聲佛號。
“這貴人今次頭一回來, 我也不認得……”惠空抬頭看了看被燒的只剩下個木頭架子的東寮室,“這東邊那小子不知所蹤,西邊這貴人倒有點兒不好惹。”
想到這里,心里登時便有了計較,正思量間,一個輕輕杳杳的婦人走了出來, 正是舒蟾。
“惠空尼師,我家夫人有請。”
惠空心里一咯噔, 心里嘆了口氣,住持閉關,萬一這貴人發難,誰能救得了呢?
心里害怕, 該去的還是要去,進了那貴人暫歇的涼亭,便見那涼亭垂下的花枝間, 藕花影做底,黛綠為畫筆,勾勒出一個冰玉骨的人。
惠空不敢高聲語,溫言問詢,“夫人大安,小庵疏忽,竟使寮室走了水,險些釀大禍。”
人慢慢兒地把臉轉過來,靨清淺,眼圈卻紅腫,顯是剛剛哭過的樣子。
“東寮室住的,是什麼人?”輕輕一問,倒是聽不出悲喜。
“……是個模樣俊俏的小哥兒,拿了枚玉凈瓶來問惠航師父的行跡……”無緣無故地問起東寮室的年,指不定同這縱火有些牽連,惠空腦中百轉千回的,轉了許多念頭,話說一半,卻見眼前這位夫人拿了帕子啜泣起來。
舒蟾慌的上前扶住了夫人,悄聲勸道:……您這麼哭,耽誤事兒。”
夫人一聽很是有道理,忙拭了拭淚,看向了惠空,“你收多銀子?”
惠空賠了笑臉,斟酌著用詞。
“嗐,我佛慈悲,住資一百兩。”有點懊惱,“早知道此人縱火潛逃,就不該引狼室。”
涼亭小風嗖嗖,惠空覺得夫人的眼也似小刀嗖嗖,扎在的腦門上。
“……一百兩?”夫人視線寒涼,冷冷地落在惠空臉上,“看來尼師不僅臉黑,手也黑。”
惠空被這忽如其來的責問嚇得一哆嗦,還沒來得及想明白,下一波責問如涌而來。
“我兒肩不能扛手不能提,也不知道哪輩子攢了一百兩,全被你給誆騙去了!”站起,走到惠空的眼前,居高臨下地出手,“退銀子!”
惠空還沒理清這二人的關系,就被夫人這個手要錢的姿勢給嚇呆了。
“夫人這怎麼話說的?那明明是個小子,您卻說是您姑娘……”
夫人拿來問詢,本就是想弄明白雪團兒來此的原因,此時從口中得來了玉凈瓶一事,更是十拿九穩,揮了揮手慧空下去了,臨了還要挾了一句,“明兒就把香油錢要回來!”
惠空丈二和尚不著頭腦,灰溜溜地下去了。
舒蟾忙上前來,扶著自家夫人的手臂問道,“這火來的蹊蹺,方才已命人去查了,只是姑娘一事該當如何?”
夫人眼睛一霎,眼淚落雨似的淌下來,一顆心像是落不到實,澎湃地像是錢塘涌,實在坐不住,在亭中繞著圈子。
便是定國公夫人南棠月,出滇王府,大庸武神老定國公甘菘乃是的公公,甘菘沒有妾室,和老妻育有一子三,長子甘瓊承繼爵位,另領了工部治水的差事,定國公府府中人事清白,南夫人育二子一,雪團兒便是定國公府頂頂寵的小兒。
雪團兒八歲那年被略賣,南夫人幾度昏厥,國公府上下大,報的同時,連續十天的功夫,南夫人親率護衛在城門、碼頭各地四搜索,結果全無的下落。
因著大悲禪寺慧航法師的佛偈,南夫人并未將雪團兒而掛著的玉凈瓶上報,畢竟脖間掛著嵌珍珠的寶石項鏈,手上帶著同套手鐲,帽穿戴皆有畫像,一定能找回雪團兒。
可丟失的時日越來越久,雪團兒毫無音訊,南夫人再也按捺不住,開始親自尋找,一年倒有大半年的時間領著護衛奔波在外。
今次正是同慧航師父約定的時間,南夫人攜護衛由帝京而來,祈盼佛祖能給些啟示,未曾想,差錯地,竟然找到了兒。
此時護衛已然追去,在涼亭板等,只覺得無法形容的激在中涌,時時刻刻快要昏厥過去。
在原地打轉,一句一句地往下吩咐。
“周護衛去追雪團兒,咱們家里也要準備起來,打發人回去稟告老公爺老夫人,雪團兒的院子趁早灑掃……還有從前吃的,一樣一樣地都要準備起來,從前不是想聘貓兒?給專辟一個小院兒,聘上十來只貓貓狗狗的,讓玩兒,哎從前我總說玩喪志,現下想起來,真是后悔,往后讓放心大膽地喪,斗蛐蛐兒、斗羊斗狗的,哪怕要斗牛……”
舒蟾在一旁聽著南夫人絮叨,拭了拭淚,“奴婢瞧著姑娘雖瘦弱,可卻有力氣的很,扮起男兒來,實在令人難以分辨,姑娘談吐舉止也大方……您就放心吧。”
南夫人方才已經問了舒蟾無數次,雪團兒同的對話,雪團兒現如今的打扮,此時又聽了一遍,又攥著帕子哭起來,“……也不知道了什麼罪,才會扮了男人……”
舒蟾忙去勸南夫人,“姑娘那個靈勁兒,不像是個欺負的,您且放寬心,一時把人尋回來,您好好地疼……”
南夫人想著方才替自己擋的那一刀,愈發地心痛起來,“大約母連心,即便認不出來我是的母親,可竟然以軀替我擋刀,我的孩兒啊……”想起好在黑夜里有男子救了雪團兒,更加地后怕,“吉人自有天相,要好好謝謝那人才好。”
這火來的蹊蹺,像是特特針對南夫人一般,舒蟾了,猶豫了一時,道,“夫人,上回咱們在明寺,見那一位假姑娘時,夜里也差點走了水,您可記得。”
南夫人嗯了一聲,腦中清明。
究竟是誰心積慮想要燒死自己,腦中有那麼一個人,呼之出,只是不知道那人為何要這麼做。
正說著,南夫人邊另一名大丫頭折桂提了一個小包袱進來了。
“……東寮房只燒了半面墻,里頭有一個小布包,想是姑娘隨帶著的。”
南夫人接的迅捷,手指了幾,打開了布包。
泰半行李都在馬車上,這小布包乃是青陸隨背著的,打開一看,幾兩碎銀子、幾顆油紙包著的糖,驅蚊子的小繡囊,再有一條繡著月下海棠的帕。
南夫人將帕攥在了手里,抵著下無聲地掉眼淚。
的閨名南棠月,正是取自月下海棠,彼時掖在了雪團兒的袖兜里,這時候再看,簡直心窩子。
舒蟾同折桂陪著哭了一時,便聽南夫人以手做拳,錘著自己的口哭出聲來。
“我苦命的孩子,何曾背過這樣的布袋子?”指著那扎心窩子的布袋子,“皮,從小不得布,便是棉布都沒穿過,里里外外,哪一件不是帛做的?還有這全是油漬的糖,當個寶似的藏在布袋子里頭,這是吃了多的苦頭吶。”
再去拿拿驅蚊子的繡囊,看著那針腳,心口痛的像針扎。
“再看這繡囊,針腳跟拿狗爪子的一樣,那不就是雪團兒的紅活兒麼?丑的很秀氣,一看就是我的孩子出來的……”
這般哭了許久,出去追擊的護衛還沒回還,南夫人本就經了煙熏火燎,泛起了偏頭痛,這便往大悲禪寺另一寮房去暫歇了。
這一廂南夫人如騰云駕霧、喜不自,那一廂青陸追著來人,一路到了潞河邊的山林深。
天微微發藍,還是清寂的夜,河邊上水浸鞋,寥寥幾聲鳥雀嚶鳴,十分清沁的晨,沐下了一個清俊的人。
辛長星斜倚一人抱的樹木,眉頭蹙,而他的前已然被浸,因穿霜的常服,那跡更加的目,在他的側旁,青陸小臉煞白,手足無措地盯著辛長星左上的那一柄沒極深的匕首。
“我拔了?”青陸膽戰心驚,小心翼翼地握住了那柄匕首的把,“我真拔了啊?”
辛長星的眉間蹙了一道深澗,可眼神卻溫,他極有耐心地向點頭,“你已經問了我二十遍了。”他用眼神鼓勵,“手吧。”
青陸張極了,再度確認了金創藥和布條的位置,狠了狠心,兩個手握住了匕首把,使勁兒地拔了出來。
猜你喜歡
-
完結433 章

農女為商:撿個王爺來致富
「無事」青年柳小小機緣際會到了古代,卻成了一個還沒進門就死了丈夫的「掃把星」。爹不疼娘不愛就算了,還要繼續把她嫁給「公公」沖喜!行吧,既然你們要這樣做,那就別怪我不客氣了,柳小小開啟了實力虐渣爹,懟渣孃的狀態。之後,本想手握靈泉發家致富奔向小康,偏偏有那不長眼睛的鄰居和親戚湊過來非要「借光!」光,沒有。懟,管夠!當日你們對我百般刁難,如今我讓你們高攀不起。隻是,我後麵那個尾巴,雖然你長的是高大帥,可現如今的我隻想發家不喜歡男人,你為什麼要一直跟著我!!!尾巴在身後委屈巴巴的看著她:「我賬房鑰匙在你那呀,我沒錢,所以隻能跟著你了呀。」柳小小:「……」誰特麼想要這玩意,如果不是你硬塞給我我會接?
74.2萬字6.4 76356 -
完結105 章

盲妾如她
俞姝眼盲那幾年,與哥哥走散,被賣進定國公府給詹五爺做妾。詹司柏詹五爺只有一妻,伉儷情深,因而十分排斥妾室。但他夫妻久無子嗣,只能讓俞姝這個盲妾生子。他極為嚴厲,令俞姝謹守身份,不可逾越半分。連每晚事后,都讓俞姝當即離去,不可停留。這樣也沒什…
49.6萬字8 28752 -
連載205 章

食全食美
餐飲大王師雁行穿越了。破屋漏雨,破窗透風,老的老,小的小,全部家產共計18個銅板。咋辦?重操舊業吧!從大祿朝的第一份盒飯開始,到第一百家連鎖客棧,師雁行再次創造了餐飲神話!無心戀愛只想賺錢的事業型直女VS外表粗獷豪放,實則對上喜歡的女人內心…
75.2萬字8 15211 -
完結56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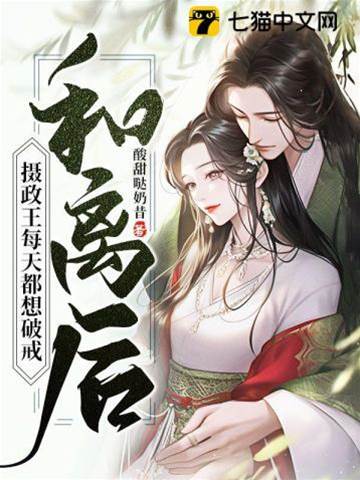
和離後攝政王每天都想破戒
葉芳一朝穿越,竟然穿成了一個醜得不能再醜的小可憐?無才,無貌,無權,無勢。新婚之夜,更是被夫君聯合郡主逼著喝下絕子藥,自降為妾?笑話,她葉芳菲是什麼都沒有,可是偏偏有錢,你能奈我如何?渣男貪圖她嫁妝,不肯和離,那她不介意讓渣男身敗名裂!郡主仗著身份欺辱她,高高在上,那她就把她拉下神壇!眾人恥笑她麵容醜陋,然而等她再次露麵的時候,眾人皆驚!開醫館,揚美名,葉芳菲活的風生水起,隻是再回頭的時候,身邊竟然不知道何時多了一個拉著她手非要娶她的攝政王。
99.6萬字8 900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