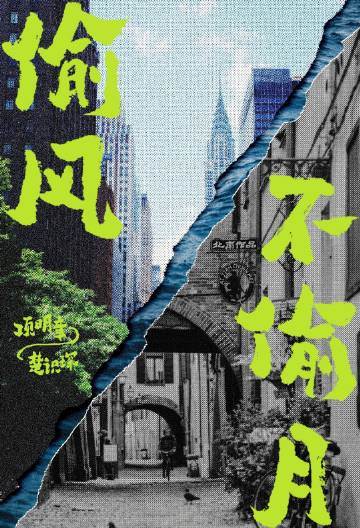《我靠美顏穩住天下》 第5章
如今是二月初,寒風凜冽。宮的醫千方百計地讓皇上的況于一個平穩的狀態,顧元白也很是配合,還好除了那一場快要了他命的風寒,之后倒沒出過什麼事。
閑暇有空時,他盡力回憶《權臣》這部劇中的劇。《權臣》正是《攝政王的掌心玉》這一本耽文的改編劇,的劇顧元白并不了解。
他只知道這部劇很歡迎,但比劇還歡迎的就是里面的社會主義兄弟。
顧元白對這種的社會主義兄弟于一種“聽過,悉,但不了解”的狀態,他對書中的兩位主角也很陌生,但派人探聽一番之后,發現這兩位主角到目前為止并沒有喜歡男人的苗頭。
顧元白洗了把臉,接過巾去水,隨口問道:“京城中是不是也有南風館?”
田福生接過圣上手中的巾帕,回道:“是有,聽說還不呢。”
顧元白一笑,也難怪等他死了之后薛遠也只是做了一個攝政王。
書中的兩個主角都是男人,彼此雙方都不是南風館中可任人魚的男人。薛遠留不下子嗣,沒有子嗣還上個屁的位。
想必等他死了之后,未來的攝政王只能在宗親中扶上一個傀儡皇帝。只要接任者夠聰明,能忍能熬,未必沒有出頭的機會。
站在一旁的田福生瞧著圣上角笑意,心中揣測萬千。
圣上突然問起南風館,難不圣上也想寵幸男子?
但整個京城之中,能配得上承恩圣眷的又有誰呢?
圣上如此尊貴,南風館的人是萬萬不能面圣的。
田福生腦子轉來轉去,忽而定住在一個仙氣塵的人上。
正五品禮部褚郎中的兒子褚衛。
臨近元宵盛宴,宮中守備森嚴,那自稱是采花賊的賊子被嚴刑審問,兩日之后終于松了口,審訊的人前來稟明了顧元白此事。
“賊子肯說了,只是想要再見圣上一眼。”
審訊的人道:“臣懷疑這人懷有異心,還請圣上定奪是見還是不見。”
圣上今日換了稍薄的靛藍披風,厚重的披在他的上,襯得他的白得如雪,聽聞此,點頭允了:“將他帶上來,朕倒要看看他能說什麼。”
過了一會兒,就有人將那個刺客抬了上來。應要帶到圣前,所以還特地給刺客沖去了上的跡,一囚干干凈凈,但仍有濃重腥味。
顧元白走上前,立在不遠:“你要同朕代什麼?”
刺客被審了兩日,他的臉上黏著發,蒼白失,瓣干裂,眼底充斥著。在外的手指上傷痕一道挨著一道,但一雙眼睛卻格外有神。
虛弱道:“草民要是說了,圣上就能放過小的了嗎?”
刺客費力朝著顧元白的方向看去,瞧清了圣上之后,一張失憔悴的臉又慢慢漲紅了。
顧元白聞言一笑:“你要是說了,朕就讓幕后之人陪你一同上黃泉。”
刺客聽了,委屈抱冤道:“圣上明鑒,小的背后真的沒人。”
顧元白正要說話,間一陣意竄起,他微側過,抵咳了起來。
一時之間,整個宮殿之只有他的低咳聲,刺客抬頭一瞧,瞧見小皇帝咳得眼角都潤了。
能把他狠狠折磨兩日的皇上,能看著他這幅凄慘模樣卻面不改的天下之主,卻會因為這小小咳嗽而紅了眼眶,這麼一想,刺客就覺得心頭的意更深,跟有羽在輕撓似的。
刺客誠心實意道:“圣上,您真的要快點將小的放走了。”
顧元白冷笑一聲,聲音因為先前的咳嗽而顯得有些沙啞,“還敢威脅朕?”
刺客搖了搖頭,“不是,而是您再不放小的離開,家父就要打斷小的這一雙了。”
田福生著嗓子冷哼了一聲,“你的父親是誰?”
刺客咧開一笑:“家父李保,小的家中排行老幺,姓李名煥。”
殿中一片寂靜,顧元白猛地上前,他臉難看地走到刺客旁,蹲下掐住刺客的下,“竟是我太傅的幺子?!”
田福生在一旁難掩驚訝,他震驚地看著刺客,這竟然是……這竟然是曾經的太子太傅李保的兒子?
刺客幾乎被打的廢了一半,他垂著眼睛去看圣上著他下的手指,指尖發白,可見圣上是用了多大的力,生了多大的氣。刺客苦笑著說:“我自己犯了大錯,所以由著圣上懲治了我兩日。這一的傷不躺上一年半載是好不了的,若是圣上出了氣,還請圣上念在小的主告知的份上,饒下小的這一條賤命。”
顧元白松開了他,表晴不定。
刺客苦惱道:“若是圣上還氣,那也請圣上容我回家稟告家父一句,家父已七十高壽,不得驚嚇,待小的回稟之后再全由圣上懲治。”
顧元白就是因為如此,才不能將李保喊到宮中認罪。
讓他認罪是應該,但萬一死了,這老先生德高重,桃李天下,死在哪都不能死在皇上的怒火之下。
顧元白被活生生氣笑了,他口一陣氣悶,田福生驚一聲,踉蹌地跑過來著他坐下。
殿中一片混,刺客沒想到會這樣,他睜大著眼睛,看著一群人圍在皇上邊。
“他知道朕不會告訴李保,”顧元白手的發白,“他知道朕得看在他父親的面子上饒他一命。”
田福生急道:“他刺殺圣上,這都能誅族了!”
“那是朕的太傅!”顧元白咬著牙,小皇帝能登上皇位,李保的相助必不可,小皇帝對李保也是多為親近。更何況這小子聰明得很,膽子大得很,從始至終只說自己是個采花賊,連近都未近,哪來的刺殺?
足足過了一刻鐘,醫趕來為皇上把了脈,刺客躺在擔架上,殷殷切切朝著人群中看去。
他當真是不了,全都在疼,此時看到這一幕,心中不由惴惴,真的有些后悔了。
刺客積攢著力氣,大聲道:“圣上要是還惱,就繼續罰我吧,我李煥賤命一條,再多的刑罰也得住!”
不知是誰狠狠踢了他一腳,厲聲喝道:“閉!”
一炷香后,顧元白才面蒼白地揮退了眾人。
李煥看著他的神,咽下間的。
那日李煥帶著青樓子在河邊踏青,與子戲耍時雙雙跌落水中,水中有蘆葦,能氣,那番在水底調的覺更為刺激,李煥便不急帶著子起。等他從水中浮出一顆頭換氣的時候,恰好就一眼瞧見了正往河邊走來的圣上。
李煥不由沉下了水底,河水渾濁,他抓著青樓子鉆到了蘆葦叢中,蘆葦叢集遮眼,他生怕旁邊的子會弄出什麼靜,便捂著的,鎖住的四肢,從隙之中瞧著岸邊的人。
岸邊的人低頭看著水,卻不知道蘆葦叢里還有人在看他。
李煥明明不是在水底,卻像是窒息一般的屏住了呼吸,等圣上離開后他才抓著子上岸。因為無知無覺中的張,他差點害了一條人命。
誰能知道那日的人竟然是圣上?他看的竟然是圣?
顧元白緩了一會,眼中沉沉,他冷聲問:“是誰放你進宮的?”
李煥張張,沉默。
“無論你說與不說,朕都不在意了,”顧元白,“誰能知道你說的是真是假,朕會親手查。查到源頭之后,朕到時候再請小李公子進宮,看朕有沒有抓對了人。”
圣上一字一句,字字平緩,沒有一個重音,但李煥卻背上一寒。
顧元白又笑道:“來人,將李公子送到太傅府上,帶著上好的藥材,讓百名宮侍跟在后頭。給朕大張旗鼓、熱熱鬧鬧地將人送到李府!”
侍衛長神一肅,“臣遵旨。”
“若是太傅問起,”顧元白,“那就實話實話。要是太傅想宮請罪,那就讓他等他兒子傷好了再說。”
“是。”
李煥苦笑著被眾人抬出了宮殿,這番大的陣仗,怕是圣上出宮也用不了。
圣上覺得刑罰他兩日還不夠出氣,還打算這樣舉一番,他原本還以為圣上不會告訴父親,免得父親氣急攻心下一命嗚呼。
卻沒想到在圣上的心里,與家父的分是有的,但家父即便是被氣死了,也比不上讓圣上消氣。
這下子父親就算是被氣死了,天底下的人也都會說是被他這個逆子氣死的。不僅如此,還會念圣上仁慈,念圣上對李府的恩德。
自此以后,他的父親便再也沒法厚著臉去說自己與圣上的分了。
“唉,”李煥長嘆一口氣,跟邊人閑聊道,“侍衛大哥,若是我父親沒有問起,還請侍衛大哥莫要主相告。”
侍衛面無表,還有怒。
李煥沉默了一會,突然張開了一直握起來的拳頭,拳頭里面正纏繞著一青,他作艱難的將這青收進了懷里,著天邊出起了神。
猜你喜歡
-
完結150 章

男配拯救偏執男主后
謝一唯看了一本大男主小說。 男主被身邊所有人算計,最後黑化,用殘忍的手段解決了所有人。 而謝一唯穿了,就穿成了那個放火把男主燒毀容的惡毒男配。 死的最慘那個。 謝一唯:“……” 還是抱大腿吧。 穿進去的時間還算早,男主還算是一朵白(假的)蓮花,他抓緊時間拼命的對男主好。 “你可要記住了,我對你最好。” “我對你可最好了。” 後來他使出了吃奶的勁兒把男主從大火中救出來,自己痛得邊哭邊道:“你、你特麼要是死了,我……” 霍珩朦朧間,就只看見一張清秀的臉蛋兒為他哭得不成人樣,然後暈在他身上。 真漂亮,當時他想。 重生後霍珩就一直跟著謝一唯,謝一唯立志要幫這位苦命的男主早日走上巔峰,把黑心肝的白月光和廢物哥哥早點解決。 霍珩什麼都聽謝一唯的,就是晚上睡覺的時候,懷裡會滾進來一個溫香軟玉的身體。 他小心又萬分珍重地抱著,心底瘋狂而又黑暗的佔有欲慢慢發芽。 後來有一天霍珩突然恢復了上一世的記憶,知道了謝一唯對他做的所有事。 謝一唯還如往常一樣,心情不好的時候就會找霍珩:“那群傻逼,明天我們去教訓他們一頓好不好?” 霍珩手微僵,隨後掩下眼底的陰婺,低聲應道:“好。” 晚上睡覺時,謝一唯的夢遊症又犯了,摸索著滾到霍珩懷裡,找了個舒服的位置睡了。 霍珩看著懷里人人畜無害的面容,指腹在謝一唯頸側微微摩挲,在幽深的夜裡殘忍又繾惓道:“要是這次再敢背叛我,我一定會打斷你的腿。” 鎖在我身邊,哪兒也不准去。 不久後的謝一唯扶著酸痛的腰,慌得一匹:“我掉馬了?我掉馬了?特麼我什麼時候掉的馬!”
31.8萬字8 11077 -
完結12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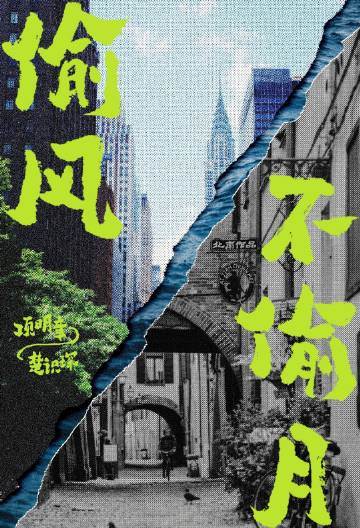
偷風不偷月
穿越(身穿),he,1v11945年春,沈若臻秘密送出最后一批抗幣,關閉復華銀行,卻在進行安全轉移時遭遇海難在徹底失去意識之前,他以為自己必死無疑……后來他聽見有人在身邊說話,貌似念了一對挽聯。沈若臻睜開眼躺在21世紀的高級病房,床邊立著一…
39.3萬字8 612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