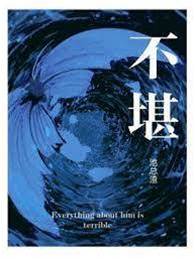《豪門離婚后》 第177章 清算出局(3)
……
這場激烈的x事一直持續道溫南書連求饒的力氣也沒有了,到了晚上,裴煜拿熱巾給溫南書了子,才發現下午急昏了頭,竟然忘記溫南書的腳傷著。
裴煜仔仔細細的看了溫南書的腳踝,就坐在床尾一邊用手掌攏著溫南書的腳心給他暖腳,一邊給何寄打電話。
何寄對裴煜下午的消失一句話也沒有多問,只是當何寄跟裴煜說到溫南書答應顧久笙的條件時,裴煜忽地沉默了。
他看著溫南書的睡,安靜而順。
裴煜自十幾歲起就知道這個年他,十幾年過去,他自己的心早就不止于在他上,那個穿著發白校服的謙虛年也被他圈在家里了終日圍著他轉的全職太太。
溫南書的眉目不再稚青,邁而立之年,可他的心卻好像早就融了骨,只是他一直沒發覺。
地板上是裴煜下午氣急甩在地上的牛皮紙袋,那里面的照片裴煜看過,其實他對那些人大多都是想不起來的,他們在裴煜眼里不過是床s上的一時愉悅,或者是生意上甚至可以送人的裝飾品,這些東西他永遠不會帶回家里去,更遑論頂替溫南書的位置。
這些年他一直覺得這樣就夠了,可后來他才知道他大錯特錯。
裴煜無法想象,當這些照片攤在溫南書眼前時,他是懷著怎樣的心去見的顧久笙?怎樣答應下足以毀掉他整整付出三年心換來的鮮花獎杯、掌聲和績,他的心是不是也在滴?還是他被人潑的兜頭臟水都無所謂,也不愿他的襟上沾了半分水花。
所以溫南書去了,也做了選擇,可他什麼都沒說,甚至他回來那樣迫他認錯,溫南書也認了。
裴煜有時候甚至覺得,從來都不是他把溫南書圈在邊,而是自己的韁繩一直都在溫南書手里。
溫南書早就用他勝以萬千人、世上獨獨一份的偏把他寵壞了套牢了,溫南書放縱他時他可以肆意妄為,而一旦溫南書收手離開,他這匹烈馬就猶如被丟棄在荒蕪之地的喪家之犬,再也尋不到回家的路。
“裴總?”
何寄許久沒有聽到電話那頭有聲音。
裴煜回過神,只是愈發握了溫南書剛剛被他暖回來的腳心,看他睡,可對著電話那頭的口氣卻冷的很:“把財務部和法務部這兩年查出來的資料統統發給裴志洪和裴瀧。告訴他們,裴氏這杯羹是我給他多,他們才能吃下去多。想要別的,就換個地方吃牢飯吧!”
…
在紫檀路的一幢別墅,裴志洪和裴瀧坐在沙發上,外面的保鏢從下午起就忽然把這里圍的嚴嚴實實,裴瀧坐不住了:“裴煜他到底要干什麼?!他這是非法拘!!他知不知道我手里有什…!”
他的話沒說完,他自己的助理走了進來,遞給他一個文件袋,說是外面有人送進來的。
“這是什麼?”裴瀧不耐煩道。
裴志洪倒是心中倏地作警,一把拿過打開,只剛出那一疊,裴志洪的臉就瞬間變了。
“爸?您怎麼了?這是什麼?是不是裴煜那家伙派人送來的?!”
裴志洪已經年過五十,鬢角發灰,他眼角的皺紋被眼里倒映出的那張紙震驚加深,紋理像滾石的壑。
“爸!到底怎麼了!!我要去找裴煜算賬,他…”
“回來!!”
裴志洪然怒斥道,他拿著那疊足以將他送進監獄永無天日的證據,不可置信。這幾年他在裴氏貪污的每一筆公款竟然都被裴煜查的清清楚楚!他自以為做的足夠蔽,沒想到…!
驀地,裴志洪瞪大了眼睛!一個更大的令他震驚的念頭浮現在他的腦海,他們這幫董事會里的老家伙手里沒有一個是干干凈凈的,而這幾年裴煜一點點架空他們的權利,看似分到手里的錢只多不,卻只是哄得那些老家伙們開心罷了。
細想之下,這些不過都是仗著裴煜心,核心決策層早就被一點點換了裴煜的親信,而他們這幫人……,或許在裴煜在位的這幾年里,早就將他們藏在保險箱里的賬本查的一清二楚,把他們后半輩子的安危牢牢握在手里了。
可他是怎麼做到的…,
裴志洪忽然驚醒,這次他籌劃中最為迎合他的,似乎是當年跟著裴嶸山打江山的……
裴志洪腦中乍起一道閃電,突然手捂住砰砰震的心臟,冷汗直下,裴瀧開始慌的:“爸!您怎麼了?!”
裴志洪道:“——撤了!!把咱們手下現在做的全都撤了!!!他們停下來!!”
“爸!這…?!好,我去!!”裴瀧縱然不知道為什麼裴志鴻這樣驚懼,但是看見父親這樣厲聲急,只好趕快吩咐手下書去辦。
另一邊,早上,溫南書從睡夢中醒來,裴煜已經醒了,正在給他收拾醫院里的行李。
“醒了?腳痛不痛?”
溫南書了兩下,比起腳,他真真覺得這會兒腰和后面更痛,好似還腫了些。裴煜昨晚怕打擾他休息,讓他翻過,給他后面涂藥。
藥膏有消腫保養的效用,溫南書此時也顧不得什麼臉面了,總比讓小護士進來涂的好,這麼安自己任由裴煜拉下他的子熬了過去。
裴煜自然是心疼又后悔,涂完了還在溫南書尖親了一口:“下次不這樣做了。”
“嗯…”
溫南書被裴煜吻在這樣親敏的地方,渾像過了一陣細弱的電流,直傳導到心臟,熱的他臉發紅,他臉皮向來比不上裴煜,只得手給自己提上子。
忽地,溫南書想起顧久笙的話,縱然裴煜之前也嫌過他在床上沒趣,不過什麼吸助劑之類的,從他跟裴煜上s床的第一天到現在,裴煜提都沒提過。
溫南書索不想了。
裴煜給他涂完藥,繼續收拾行李。
“藥我給你放在夾層了啊,都了字條。”
雖說裴煜收拾的整齊度跟溫南書自己整的沒法比,但好歹這些以前他從不會做的事,現在都自然而然的做了,倒讓兩個人之間多了許多平常夫夫的煙火氣。
溫南書今天要啟程飛去黎,助理已經給他從家收拾好了行李,連帶著兩只貓也安頓好了。
溫南書起洗漱,突然在枕頭上發現一白發,溫南書心頭猛地一跳,
原來不止人畏懼老去。
“怎麼了?”裴煜瞧見他發呆,過來就看見溫南書手里的那發。
“最近你承的力太大了,等去了黎,咱們就不理會這些了。”
裴煜安他,只當是這半個月讓溫南書承的力太大,任誰被外界故意歪曲的惡意罵地那樣無完,能安安穩穩睡好每一個覺的?更別說什麼委屈都習慣默默往心里咽的溫南書。
溫南書握著那發,倒是和裴煜想的不太一樣。
“…我開始老了,裴煜。”
他的過病重重創,長達幾個月的冰冷治療和一場八個小時的手把他的從里到外都掏的骨瘦嶙峋,一度肋骨清晰可現,丑陋不堪,這在三年前就消耗太過了。
“或許我會比別人老的快些…,”
“怎麼會,慢慢就養回來了,你瞎琢磨什麼,再說了,”
裴煜拍掉他手心里的白發,干脆坐在床邊,從背后擁住他的肩膀后一起后靠在床上,讓溫南書枕在他懷里。
裴煜五指攏住他的手指,慢聲道:
“再說了,你永遠不老不電影里演的妖怪了?那可不行,我還得拉著你陪我一塊兒白頭偕老呢。”
溫南書瞧著裴煜,鼻子默地一酸,在心里應了聲好。
吃早餐的時候,裴煜去外面給他簽字辦手續,溫南書見裴煜扔在沙發上的外套里掉出一張紙,便準備給他撿起來。
溫南書原本不打算看的,只是紙張上面的標志眼,是一份玫瑰訂單,正是出自上次溫南書說好看的那個英國莊園。
這上面訂購的數目驚人,聯想起上次不過一束的價格,溫南書不太看敢看總金額的那一欄,只覺得數量足夠布置一整個會場也富裕,再看后面的英文備注,應該是特別定制需要培育的品種與,要生產一整個季度才能貨。
溫南書拿著那張訂單,突然覺得,如果不是殺出了這件事,大概裴煜已經開始著手準備他們的復婚了。
…
溫南書和團隊一行人到了機場,裴煜代他好好休息,拍戲不要太累等等,他理完事就過去陪他。
溫南書點點頭,他昨天做的太累,整個人神懨懨的,裴煜惜的了他后頸順的碎發,毫不避諱旁人,直讓團隊的工作人員吃飽了一肚子的狗糧。
不工作人員都是昨天從頭條新聞上,看到方思澤當著那麼多記者的面出來溫南書和裴煜已經離婚才知道這個驚人消息的。
猜你喜歡
-
完結335 章
假駙馬,真皇后
1. 賀顧為了太子出生入死、平南定北,最後新皇登基,卻落了個被滿門抄斬的下場。 重回十六歲,擺在他面前的有兩個選擇: 再一次接過太子遞過來的橄欖枝,成為其心腹。 賀顧:我呸! 或者娶了那位傳聞中高貴冷艷、十分厭男的長公主,成為一個不能入仕、吃軟飯、而且可能還要做一輩子處男的可憐駙馬。 賀顧:……不就是軟飯嗎,吃就吃! 2. 後來賀小侯爺在長街上邂逅了出宮打獵的長公主。 長公主紅衣黑馬、肌膚賽雪,遠遠瞥他一眼,那眸光凌冽如秋水。 賀小侯爺一眼盪魂。 ……手裡這碗軟飯,它忽然就香了起來。 3. 萬萬沒想到的是,千辛萬苦做了駙馬,才發現長公主他不太對勁。 沒錯,是他,不是她。 原來要當一輩子處男都是騙人的,這人簡直不要太行好嗎?
78.3萬字8 17476 -
完結8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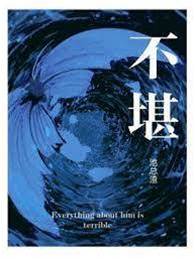
不堪
和他有關的所有事,都是不堪 【三觀不正,狗血淋頭,閱讀需謹慎。】 每個雨天來時,季衷寒都會疼。 疼源是八年前形如瘋魔,暴怒的封戚所留下的。 封戚給他留下了痕跡和烙印,也給他傷痛和折磨。 自那以后,和他有關的所有事,都是不堪。 高人氣囂張模特攻x長發美人攝影受 瘋狗x美人 封戚x季衷寒 標簽:HE 狗血 虐戀
20.2萬字8 574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