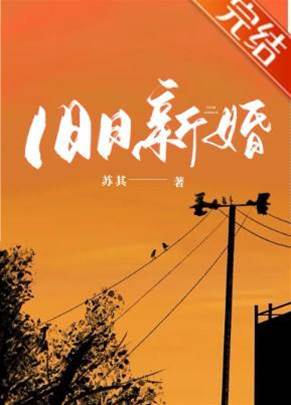《凝脂美人在八零》 第70章
雖然他家的溫馨說給他生小孩兒, 說得跟玩笑似的。
可沒有男人不喜歡心的人愿意給自己留下后代,這是兩個人的結晶, 也是的延續與見證。
他當時“嗤”了一聲, 上的,但心里卻還是像泡了溫泉一樣,暖洋洋的舒服, 周都舒暢起來。
高興的帶著下去吃飯, 親手給蟹, 將剝好的蟹放到的盤子里,看著紅通通的小等待他的喂食,一邊吸著雪白的蟹, 一邊吃著香噴噴的蟹黃,好吃著還抿了好幾下。
飯館的大閘蟹個大, 又新鮮, 溫馨一個勁兒的說好吃,還了一個蟹, 親手給他放到里面, 笑嘻嘻的要他也嘗嘗, 對男人好, 補腎又壯。
閻澤揚心里嗤之以鼻,他還用補腎,壯?笑話!
不過,還是順著手指上晶瑩的蟹吃了,這是趣, 是溫馨的小甜。
溫馨在閻澤揚心里是什麼樣兒的?或許自己并不知道。
只有閻澤揚自己知道,時而溫,時而俏調皮,有時大膽放浪,有時又害膽怯。
看著很依賴自己,可有時候的神世界又是完全獨立。
有時候驚的就像小兔子,可是有時候,什麼都不怕,甚至對這個世界都不以為然,哪里都敢去,什麼都敢試,有點游戲人生的樣子。
他猶豫了許久,都不曾把他猜測的一切說出來,是因為他怕他猜測的那些東西,只一個泡沫,一旦破,他將一無所有。
如果非要形容,那麼在閻澤揚的心中,是他的人,是他折斷翅膀留在他邊,只屬于他的,未來世界的小仙。
……
晚上回到家里,兩個甜甜,心滿意足的將架在上,看著潔的背影,盡興的擺腰與共赴極限的快樂巔峰,他和這方面出奇的和諧。
第二日早上,他神清氣爽,見時間還早,他就將懶的兩天沒洗的服,蹲在浴室里給洗的干凈凈,全部晾好了,小也給放在了會充足的地方,還有一個面,黑碗狀的東西,以前閻澤揚不知道這是什麼,后來才知道原來這是包著那一對小可的東西。
一個大男人,手里拎著兩個碗狀布料,想到第一次見到時的景,他角微揚,大手別扭的在幫洗著。
雖然這東西他不知道怎麼洗,有種無從下手的覺,但最后還是給洗干凈了。
下去給買了早餐,溫在了鍋里,大廳也收拾干凈,吃的零食、干果,還有茶幾上喝了一半的茶水,以及柜子上擺放得雜的書,都被他一一歸整,收拾好,才取了門口的軍裝,穿了起來。
然后拿著帽子走進了臥室,坐在床邊看了一會兒,給理了理鋪滿了整個枕頭的黑亮發。
才起走了出去,將門關上,戴上了帽子,在清晨的夜里,開著車回到了駐地。
車剛一駛進大門,就有警衛兵跑了過來行禮,“團長,昨晚京都軍區發過來的包裹,加急件。”
閻澤揚看了一眼,手接了過來,上面寫著滬州市一三七部隊閻團長親啟,“我知道了。”隨后將車開了進去。
下了車,他手里拿著東西直接走進了辦公室。
將包裹扔到一邊,摘了帽子,走公桌前,拿起電話拔了過去。
轉接后,閻澤揚直接沉聲問道:“包裹怎麼回事?”
“團長。”對方說道:“昨晚打電話,他們說你不在駐地,是這樣的,我還沒搜集到東西,你讓我查的那個人就出事了,和一個同班的男同學搞男關系,第二天報警告對方強干,男同學被抓了起來,他家里有個親戚在公安線上,最后查明兩人是對象關系,那個同學還收了男同學價值二百塊的東西和錢,是你我愿,這件事影響很大,學校已經將兩個人全部開除了。
我趁機拿到了那個人除了行李其它所有的東西,其中有一個本子上面寫的東西很奇怪,上面還有團長的名字,我覺得團長你應該看一下,這人不知道是不是間諜,是否會對你有所不利,現在已經被家人接走了。”
閻澤揚掛了電話。
想了下,轉取過那個包裹,撕開外層紙包,里面是一沓紙質東西。
既然已經郵過來,電話里的人就將所有覺得可疑之都郵了過來。
閻澤揚坐回了椅子上,將其中的幾封信看了看,都是以前溫馨給郵寄的信件,他匆匆掃了一眼,被他扔到了一邊,剩下的就是宋茜在學校寫雜志報紙的稿子,都是底稿,有的已發表,有的石沉大海,上面都有標記。
閻澤揚皺著眉頭,翻了翻,全是些悲春憫秋的容,要麼就是一些博人眼球的小故事。
他又看向了最后那個像日記本一樣的東西,里面除了一些寫劃的草稿,就是一些靈記錄,并沒有什麼可疑之。
翻到了最后,有一頁,被折了一角。
他將那一角展開,凝眸看了過去。
在看到他的名字的時候,他瞳孔微微了一下。
這張紙用筆劃拉得很匆忙,顯然不知是心很還是想掩飾什麼,字跡是不清楚的,而且寫得很簡略,只標了關鍵詞,估計只有本人看了才清楚什麼意思。
一開始是按人名排列,第一個是男主,后面是他的名字。
下面只有兩個字,主,后面是空的,再后面是配一配二配三……
男配一二三四……八。
在配那里,寫著兩個悉的字,溫馨。
閻澤揚已經沉下臉了,繼續看了下去
接著就是以年份排列,每個年份后面都跟著幾個凌的詞。
七八年后面是高考和京都字樣,后一年是大學、配一、閻家的字眼。
八零年仍然標著閻家,地址、通信、男主調職,配一逃離南下。
再后面幾年,結婚、畢業、特權。
再后面私營、創業……
一開始閻澤揚只是匆匆掃一遍,可是隨著后面日期越來越多,一直標到了2018,閻魔頭才直了脊背,俊臉冷厲,眉頭輕蹙,開始仔細的分辨上面每一個年份后面的關鍵詞。
越看他面越沉,甚至還是香江、回歸字樣。其中出來的人名越來越多,而他的名字也時不時夾雜其中。
他盯著手里這個東西,思緒飛,2018?為什麼那麼巧合?這到底是那個人臆想出來的,還是……
難道與溫馨一樣?
有一年后面還標出了三個字,溫馨,死!并用畫了好幾個圈。
就在他看著這個東西,心疑慮重重,冷靜之中夾著莫名的慌恐,又有一憤怒之意的時候。
“報告!”手下一個連長敲門走了進來,給他一份連里士兵的訓練計劃,連長是很忐忑的,他們邊是這次查的能訓練績不太好,他就怕團長給他一通臭罵的。
但沒想到計劃了,閻團點了點頭就擺手讓他出去,連長出去的時候,還覺到不可思議,閻團居然什麼也沒有說,還以為他要被罵得狗淋頭,他還準備了,團長要罵他,他去回去罵死那群不爭氣的兵崽子。
打發走了人,閻澤揚再次拿起了扣在桌子上的筆記本,看著那幾頁記錄,越看越似冥冥之中像是這些真的能發生一樣,那種覺好似心口得千金重石,某種他無法預知的東西,正緩緩向他揭開了真面目。而他,卻猶豫了,不敢去輕易面對這樣的真相。
可是退怯又絕對不是一個男人,甚至一個軍人的作為。
半月后。
閻澤揚挪出了一整天的時間,帶著親信趙東升風塵仆仆的趕往了桓樺市。
他已經調查過,這個宋茜六月初被學校開除后,回到了宋家,第二天就被嫁給了一個傻子,房的時候,將對方家里的傻兒子那東西給踢了,在傻子哀嚎聲和家中套的尖聲里,宋茜找到機會狼狽的逃了出去,后來在火車站跟著一個三十歲的男人,上了火車,一路到了桓樺市,后因沒有份證明,被男人囚在家中,在偶然反抗當中,瞎了對方的眼睛,再次逃了出去。
因為沒有份被公安拘捕后,與那個男人雙雙獄,八月中以傷害罪被判了二十年刑罰。
閻澤揚再次見到的時候,是在桓樺市第四監獄會見室,二十歲的宋茜,著灰白的監獄服,戴著手銬腳鐐,因為剛獄不久,神慌恐,走了進來的時候,一見到閻澤揚。
一下子就沖了過去,卻被后面的獄警死死拽出了拷,摁在了會見室桌子對面的凳子上。
“閻澤揚,你把我弄出去,我求求你了,你要我做什麼我都愿意。”宋茜的緒非常糟糕,激有都在抖,近看能看到臉頰的腫塊和角的傷。
猜你喜歡
-
完結89 章

寒鴉
時隔十年,溫舒唯再見到沈寂,是在印度洋北部的海域。那天,陽光和煦,海鷗飛行的路徑畫成了海岸線。男人軍裝筆挺高大英俊,靠著軍艦護欄沖她輕輕一挑眉,淡淡地說:“挺巧啊,溫同學。”一樣的散漫又冷淡,玩味又無情。和他當年左手拎著校服,右手擰她下巴強吻她的樣子,一模一樣。*婚后某日,溫舒唯從沈母口中得知,沈寂自幼便喜食生牛肉,嘖嘖感嘆:”長得這麼,沒想到這麼重口味。“當晚,兩人玩手游,溫舒唯慘遭自家老公血虐。她氣呼呼的,手機一摔叉腰怒道:”好氣哦,今晚去給我睡廚房!“沈寂聽完沒什麼反應,一把將姑娘抱起來就往廚房走。溫舒唯:”……?“沈寂:”廚房也不錯。“溫舒唯:”……???“沈寂:”畢竟我重口味。“
37.6萬字8 18930 -
完結63 章

愛如夏花般璀璨
餘歆檬愛了一個男人十二年,卻被他親手挖了腎,丟進了監獄三年。三年的折磨,一千多個日夜,把她對他的愛消磨殆盡。再次見麵,他紅了眼,她卻微笑著說:“先生,我們認識嗎?”她想遠遠的躲開他,他卻死皮賴臉的纏上了她。 …
5.9萬字8 35561 -
完結134 章

鎮國戰尊
“我決不能把這個世界,讓給我所鄙視的人!”三年前,他是人人口中的廢物。三年後,他是第一戰尊,身披金甲榮耀歸來,只爲給她全世界……
17.1萬字8 162224 -
完結17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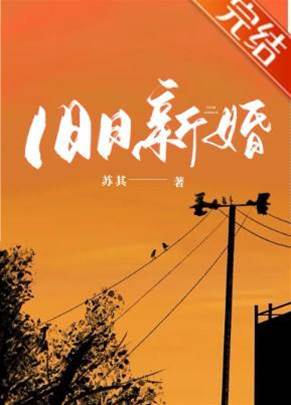
立冬/舊日新婚
秦南山是聞依最不喜歡的男人類型之一,刻板嚴肅,沒有喜好,沒有激情,像密林深處一潭死水,石頭扔進去,波瀾不驚。 一夜混亂,聞依更新認知,不全無可取之處。 一個月後,聞依看着試紙上兩道鮮明的紅槓,陷入沉思。 從懂事起,她從未想過結婚生子。 - 秦南山二十八歲,A大數學系副教授,完美主義,討厭意外,包括數學公式和人生。 聞依找上門時他一夜沒睡,逼着自己接受這個意外。 領證、辦婚禮、同居,他們被迫進入一段婚姻。 某個冬日深夜,聞依忽然想吃點酸的,換好衣服準備出門。 客廳裏穿着整齊加班的秦南山看向玄關被她踢亂的鞋子,眉心緊擰,耐着性子問:“去哪?” “想吃酸的。” “非吃不可?” “嗯。” 男人垂眸看錶,十二點零七分。 他心底輕嘆一聲,站起來,無奈道:“我去給你買。”
31萬字8.18 19276 -
完結250 章

夏歇
京大迎新晚會,身旁學姐指着臺上演講的學生會主席段宵:一位出名的恃帥行兇貴公子。 看着單純的夏仰,學姐語重心長:“你可千萬要離他遠點!” 夏仰乖乖挪開視線,莞爾:“放心,我不吃這款。” 話落,演講結束的臺下掌聲雷動。 而她剛進後臺休息室,就被一隻手掌強勢扣住,懲罰的wen洶涌而至。 男生摩挲她微腫的脣瓣,冷嗤:“這不是挺會吃?” * 夏仰和段宵,是蛇與農夫的關係。她欠他一次,他發狠討回來。 所有人都說他被攪和進一灘淤泥裏。 後來她提出要走,段宵卻不肯。 荒唐夜,他壓着狠勁,一字一句威脅:“說,不分手。” “不準再裝不熟。”
37.7萬字8.18 4173 -
完結178 章

嬌寵卿卿
康寧十三年,先帝駕崩,臨終前留下一道聖旨—— 尊定國侯府七姑娘爲新帝之後妃。 聖旨一出,滿朝沉默。 世人都知,這位七姑娘是定國侯府掌上明珠,自小受盡疼寵,偏生是個溫柔似水的性子,而當朝新帝又是個無情狠戾的主,當日,定國侯府上下如喪考妣。 誰知,還沒半年,一道封后的聖旨曉諭六宮。 再沒一年,一向不解風情的帝王竟然跪起了搓衣板。 滿朝文武:這是什麼操作? 初見時: 美人盈盈一拜,嬌柔婉約,“臣妾恭迎皇上萬福金安。” 新帝靠在金鑾椅上懶懶輕笑,呵,就知道一早想對朕圖謀不軌。 再後來: 寢殿之內,美人輕顰眉梢,似是不愉。 雷霆不驚的年輕帝王忙輕聲哄勸,“卿卿,你再看朕一眼好不好?就一眼。”
27.1萬字8.18 1772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