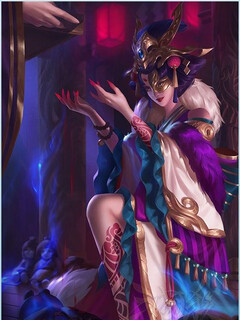《黃河鬼棺》 3千年古墓-第一章 噩夢驚魂
我們三人都茫然的搖頭,這個問題黃智華不用問我們,只要一查就明白,我們被關在警局的員工宿舍,還有人專程看守,晚上想要出去,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爺說:黃先生,生什麼事了?丫頭也瞪著一雙水靈靈的大眼睛,忽閃忽閃的看著黃智華。
黃智華了口氣說:我也知道這事不可能是你們做的只是——實在是太離奇了。
我忙追問生了什麼事。黃智華看了看四周都是豎著耳朵想要聽的警察先生,皺著眉頭,讓我們到他的辦公室說話。
到了黃智華的辦公室,還沒有來得及坐下來,他就直接開門見山地說:“那個王全勝的失蹤了……”
“什麼”,我聞言直接就跳了起來,回想到昨晚夢中經曆,不覺冷汗淋漓,一涼氣從脊背涼嗖嗖地爬了上來,甚至我整個人都忍不住輕微地抖起來。
爺也變了臉,結結地問:“怎……怎麼回事?”
丫頭啊了一聲,本能地就向我上靠了過來,很是害怕,不過幸好並不認識王全勝,也不知道這人是怎麼死的,所以雖然聽著覺離奇,心生惶恐,比我卻是好得多了。
黃智華解釋說,昨天他們把王全勝的運了回來,由於他也是接過黃河龍棺的人,昨天我老實地向他待過我們見過王全勝,還從他手中買過青銅,並且也是從他的口中得知黃河龍棺的消息,所以黃智華他們在運回王全勝的後,並沒有解剖研究起的死因,而是直接送去了殯儀館,準備聯系上他的家人後再做理。
可是今天一大早,殯儀館的工作人員就打來電話,說是丟了一,王全勝的不翼而飛了。
這年頭好象什麼東西都可能會丟,可是—-丟也太荒唐了。再說王全勝不過是一個普通的黃河水鬼,整天在黃河裡撿垃圾討生活的人,上要是有錢,也就是那個丟了的五千元,如今還在我手裡,誰會這樣一?
如果說王全勝的不是別人出去的,那麼就剩下一種可能—-他自己走出去氣?
自己走出去?這個比丟了更加荒唐。我頹廢地坐在黃智華對面的椅子上,靠在椅背上,閉上眼睛,就是王全勝那張蒼白地臉,帶著猙獰地笑容,惡狠狠地盯著我。
王教授的和老卞的,可以跑去廣川王陵,那麼王全勝的跑出去氣,實在是太正常了,再說—-王全勝本來就是死了半年多才出現的,這個裡面絕對有古怪。
正在我胡思想的時候,猛然,擺在辦公桌子上的電話急劇地響了起來,把我再次哧了一跳。我最近有點草木皆兵,杯弓蛇影的覺,再這樣弄下去,我不死也會早晚得神病。
黃智華手接了電話,那一頭不知道有人說了什麼,他頓時就變了臉,匆匆地說了一聲—-我就來。
放下電話,他問爺:“南宮門口的那張招待所,你開的?”
爺不解,點頭說是,我們就是在那裡被黃智華給“請”來的,黃智華自然也把我們的十八代祖宗都查清楚了,怎麼會不明白南宮門口的招待所是爺家的產業?
“你那裡出了人命司,有個客人今天死在了房間,而且王全勝的也出現在案現場……”黃智華的臉非常不好看。
什麼?我簡單不敢相信,王全勝死後居然再次向了爺家的招待所,他去那裡幹什麼?我轉念一想,已經明白,如果說真的存在“魂不散”的事,那麼王全勝勢必是去招待所找我去了?
找我索命,還是想要回他的那五千塊錢?
我的心髒“砰砰”地直跳,幾乎要從口腔裡跳出來,迫使我不得不張大了口才能夠呼吸。
黃智華看了看我們三人的臉,似乎下定了某種決定,問道:“不如這樣,一起過去看看,這件事你們三人多都有點關系。”
命案生在爺的招待所,而王全勝的死卻只有我一個人知道,我也非常想要去看看,已經死了半年多的王全勝,到底是什麼模樣,雖然是很害怕,但還是點頭應允。坐上黃智華的那輛越野車,警笛聲非常囂張地一路呼嘯著直奔南宮門口。
在爺家的招待所門前下了車,原本這個時候,招待所的門口是最最冷清的,如今卻熱鬧得很,好多好事之人聽說出了人命大案,都忍不住探頭探腦地過來,想要一探究竟,增加茶餘飯後的談資。但招待所的門口被警員叔叔團團圍住,誰也不能輕易進。
黃智華剛剛一下車,由於他本是軍方人士,實話說—-這些員警叔叔還是很拍著他的馬屁,所以,很快就有一個年輕的小警員跑了過來,行了一個標準的軍禮,報告說,現場沒有,就等他來了。
黃智華不置可否答應了一聲,我們三人也先後下了車,跟隨在黃智華地後。爺低聲音在我耳邊說道:“謝天謝地,我這次正好在警局吃免費飯,倒是直接擺了嫌疑,要不,你說這豈不是天大的麻煩?”
丫頭白了爺一眼,我知道爺說得有理,但卻被他說中了心病,也忍不住狠狠給了他一個老大的白眼。
黃智華在一個小警員的帶領下,快步向裡面的房間走去。
“就是這裡了?”眼見小警員在某個房間門口停了下來,黃智華問道。
我抬頭看了看這個房間,忍不住就肚子打。我每次來太原,只要住下,勢必都是住在爺的招待所裡,而且,一來二去的和爺混了,他知道我喜歡靠南的這個房間,只要這個房間空著,絕對都會安排給我。
而這個房間,就是當時王全勝死的那個房間。
黃智華已經一腳了進去,爺和丫頭也忙不迭地跟了進去,只剩下我還猶豫在門口,我的頭上再次冒出冷汗,手心冰冷,漉漉地難,背心裡卻仿佛有一把火燒著,本能地我不想去見到那個王全勝,也不想去看另外一個死者。我想要拔逃跑,但天下之大,我跑向何才能夠避開那個來自上古時期的詛咒?
著頭皮,我也走進了房間。案現場還保持著原樣,幾乎,我是一眼就看到房間的電視櫃子邊上的角落裡,一個人影……不,是鬼影,就那麼蹲在那裡,和半年前簡直就是一模一樣……
他的臉面朝著牆壁,看不清楚表,上穿著的,就是當時那件服,當然,是不會講究自己換服的。
我強下心中的惶恐,抬頭看向另一個死者。那個人靠在床沿邊,年紀不大,是個三十左右的男人,相貌普通,死狀卻是離奇古怪,兩腳半蹲著,手臂向前著,似乎是想要什麼東西,又象是想要和什麼人搏鬥,上披著服,下僅僅穿了一條,長就擱在旁邊。
由於房間向南,如今太很是明朗地照進房間,正好照在那個死者的臉面,我看著他的角一種詭異的弧度裂開,仿佛在笑,猙獰地笑,而在他的脖子上,明顯地有著手指掐出來的青黑淤青。
他是被人掐死的?但離奇地是—-我聽說掐死的人與吊死鬼一樣,都是舌頭出老長老長,窒息而死,而這個人的舌頭並沒有出來,甚至他的角還帶著笑容,詭異而猙獰。
猛然,這人的死相非常悉,好象在什麼地方見到過,但是一時卻怎麼都想不起來。
丫頭在旁邊輕輕地拉了我一把,眼圈子紅紅的,似乎就要哭了出來,低聲道:“許大哥,你看那人……他的模樣,是不是與單軍死的時候一模一樣?”
被一提醒,我忍不住“啊”地一聲了出來,對了,這人的死相,不就是與單軍死的時候一樣,當時—-單軍死了,老蔡說是什麼七笑,說是要請個人坐著,想法子讓他哭出來,結果那個老頭做了一天一夜,將我了進去,說是單軍要看看我?還把一塊青銅片給了我?
這絕對是一個噩夢,我還陷在夢中沒有清醒。我再次想起,在黃河龍棺的墓道裡,似乎有著一些壁畫,最後的一副,好象也是這個模樣……只是那些浮雕壁畫,只怕也早就被王教授等人搬進某個博院了。
黃智華帶上手套,翻看床邊那的眼皮子看了看,瞳孔已經明顯地擴散,顯示著人已經死得不能再死了。然後,他又走到王全勝前,出於本能地想要去翻看他的瞳孔,這個時候,我就站在旁邊,看得清楚,就在他翻看王全勝眼皮子的時候,那雙已經擴散的瞳孔,不……應該說,有點腐爛的眼框子,居然出一縷兇,狠狠地盯著我……
“奇怪,這不象是新鮮的啊?”黃智華仿佛自言自語,我的心裡升起一個老大的疙瘩。
猜你喜歡
-
完結66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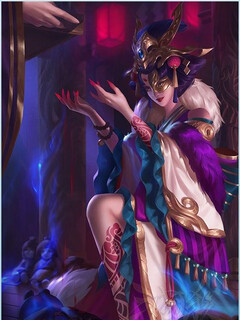
愛上千年女屍
稀裡糊塗變千年保存完好的女屍?顧長生表示,她見鬼了,然而別人香妃身帶奇香能引蝴蝶,為啥到她這裡,蝴蝶沒有詛咒纏身,另有冥王大人捧在手心寵愛?顧長生每天在爆炸的邊緣試探,她就想回到原來的生活怎麼就那麼難?某少年蹦躂出來道:“主人,這就是你的生活。”
62萬字8 33672 -
完結181 章

恐怖洞房夜
新婚夜,老公說要給我一個驚喜,沒想到――他卻吃了我!他說蘇家曆代只要右肩有月牙胎記的都被他吃掉了。重生到十歲那年,他一邊啃著我姑姑的手指一邊說:“養你十年,再生吃。”為了不重蹈覆轍,我仗著前世的記憶和多生的一雙鬼眼,意圖逆天改命!誰知突然冒出一個帥氣的教書先生:“不想被吃?我能幫你。”“怎麼幫?”教書先生妖嬈纏上身。
52.1萬字8 1915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