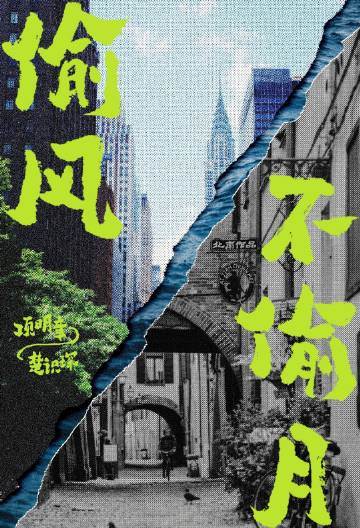《玩家》 第22章
宴禹有心想道謝,又不想告知自己上發生了什麼事,猶猶豫豫,最終還是挑了個最不沾邊的話題,他問:「你怎麼今天回來,不是再過幾天才到嗎?」
聞延搖頭,說計劃有變,幾個景因為氣候原因不再被允許進,達不到最初想要效果,最後決定選在本城取景,再不就棚拍做後期。今天才到,剛好問問他是否在家,誰知宴禹電話裡醉得言語顛三倒四,於是只好親自來接。
宴禹點點頭,忽地憶起剛剛那聲重擊,他猛地睜大眼:「你對我車子幹了什麼!」聞延好笑地將空啤酒瓶得扁扁,再空投進垃圾簍,金屬挾著力道將簍子撞的晃了圈,又悠悠地立穩了。聞延左手托腮,毫無誠意地道了個歉:「我陪你修理費。」
宴禹更驚了,聞延對他車子做什麼,拿托車去撞了?還到修理費的程度?他想了又想,還是不放心,於是下樓看車。直到瞧見那拳頭凹陷,宴禹無言了。重回聞延家,他手去夠對方一直沒拿出來的右手,果不其然,紅腫青紫,留了傷。
蠢又笨,衝還野蠻。以去冰冷金屬,還傷到自己。聞延這是越活越年輕了嗎,衝的和個青春期男孩似的。宴禹冷笑地嘲諷一通,而後小心翼翼地往聞延手背上吹了吹:「我看著都疼。」
他轉找聞延家的醫藥箱,小心翼翼理傷口樣子逗樂了聞延。將人包紮好,反被聞延恩將仇報地掐了臉,力氣頗大,疼得宴禹表都變了。聞延邊邊笑,說他現在酒醒,總算不是糊塗模樣。等人撒手,他明顯到被掐那邊,腫高了許多。宴禹捂著臉盯了聞延好一會,心裡冷哼:裝腔作勢,口是心非,頭烏!
嫉妒又不願獨佔,想擁有又不願再次涉足。不給準話又讓人陷其中,撞得心淋漓再給你包紮好,笑看你不死心撞多一次。其心惡劣,套路之多,手幾次就如探戈,曖昧相擁相離,激烈你進我退,不著,夠不到,又放不下。可怎麼辦呢,就是不死心。
宴禹心頓時不佳,他起準備歸家,穿著聞延的服子。聞延打量手上扎出的蝴蝶結,聽到他的話,抬眼看他:「在我這睡吧。」宴禹不願:「我家有狗等我。」如果能被這話敷衍了事,聞延就不聞爺了。五分鐘後,蠢狗連狗帶窩,被聞延端了上來。
小司還一臉興,狂聞延腳踝。宴禹瞇眼看小司微笑狗臉,只抬腳用腳趾頭狗腦袋,不讓狗繼續,誰知道小司轉頭他腳趾頭,得他忙躲。聞延將床鋪得,喊他去睡。兩人一狗,全臥在那張床上。
聞延要手攬他,宴禹就翻。想他背,就平躺,翻來覆去好幾回,聞延先笑了。聲音在黑暗裡盪開,低沉讓他別鬧。宴禹心道:吃聞爬爬蝦傷手了還不能歇會再吃?這種況別再來撥他,不約。
不知是飽後嗜睡,還是那杯牛作祟,宴禹睡得快又沉,直接導致第二天曠工。幸好如今他也算工作室合夥人,電話中請了假,就在床上翻了好一會。聞延不在床上,桌有包子豆漿,雖然冷了,餡也膩了。宴禹還是一口包子配豆漿,吃得一個不剩。
他微信上聯繫高姓律師,約人見面,不在酒吧在飯店。他說有關於律法相關問題要咨詢一番,那邊很快回好,定在一個半小時後見面,於是宴禹扔了手機,起床去浴室。幾次留宿,聞延就心給他備一副牙刷口杯,兩個立在一塊,一藍一橙,還款。
宴禹笑笑洗漱,他臉功夫,就聽聞延開鎖聲,對方牽著小司回來,。宴禹問早上怎麼不他起床,聞延說了,他自己醒不過來,加之他有心讓他多睡一會。宴禹從浴室走出,好笑道:「扣了工資你給我補?我窮的很。」
聞延攤手:「錢沒有,可以償。」宴禹回想痛又爽,一步到胃的事,覺得這種償不如不要,總歸是他損失大些,做完不能說下不來床,畢竟他每週三天健房,不時夜跑攀巖登山,算是力充沛,軀強健。但招架聞延一場,還是會元氣大傷。
見他收拾自己抓弄頭髮,還不問自取套上聞延的襯衫加牛仔,偏大頭約能看到邊緣。聞延皺眉取來一條腰帶,為他套上扣好,將子提高,問他:「準備出門?」宴禹點頭,說去見個朋友。聞延說送他,他的車子已經被聞延開去修理廠,修補那塊凹陷。
宴禹無所謂點頭,等到了地,那高姓律師也剛到,給宴禹打招呼時,正好從停車位走出。宴禹從聞延車上下來,就被聞延住。宴禹回頭,就見聞延言又止。他沒多想,道謝後匆匆往高律師那走。
誰知道對方見到他,再看到聞延,有些驚訝:「那不是聞爺嗎。」宴禹揚眉看高律師,只見對方朝聞延那曖昧一笑,眼裡暗示味道濃厚,那是一種心照不宣,大家都懂的笑。
猜你喜歡
-
完結87 章
懷了敵國皇帝的崽後我跑了
沈眠一朝穿書,穿成了正在亡國的炮灰小皇帝。皇位剛剛坐了半天的那種。書裡的主角暴君拿著劍向他走來,笑眼盈盈,然後……挑了他的衣帶。士可殺不可辱!楚遲硯:“陛下長得真是不錯。”“是做我的人,還是……去死呢?”所謂君子報仇十年不晚,沈眠忍辱負重,成了暴君的男寵。不過男寵真不是好做的,沈眠每天都想著逃跑。前兩次都被抓了,後果慘烈。終於,沈眠逃跑了第三次。這回冇被抓,可他也發現自己的肚子竟然慢慢大了起來。他麼的這竟然是生子文嗎?!所以冇過多久,他便被暴君找到了。暴君看著這個自己快找瘋了的人,笑起來的時候陰風陣陣,他輕撫上那人的腹部,像是誘哄般輕聲道:“這野種,是誰的?”沈眠:“???”是你的狗渣男!排雷:1.有修改,重新開始。2.受盛世美顏,身嬌肉貴,有點萬人迷體質。3.暴君真心狠手辣和狗。4.攻受性格都有缺陷。5.好聚好散,小學生文筆,拒絕指導。6.有副CP★★★★★預收文《當死對頭變成小人魚後》宋祁星和沈戾天生不對盤。沈戾優秀又是天之驕子,剛出生就擁有家族一半的資產。所有人見了都得尊稱一聲:沈少。宋祁星處處針對他,見縫插針給他使壞。然後有一天,宋祁星莫名其妙出現在沈戾家的浴缸裡,下半身變成了一條藍色的魚尾,而且記憶全失。沈戾回來見此場景,冷笑一聲:“宋祁星,你特麼又在搞什麼名堂?”宋祁星覺得這人好兇,他很怕,但又莫名地想接近,被吼得可憐兮兮的,眨巴眨巴眼睛掉下幾顆小珍珠,小聲的:“你罵我乾什麼……”沈戾皺眉,這人搞什麼?總算冇有兇他,宋祁星擦乾眼淚,懵懵懂懂地朝沈戾伸出雙手,粉白的臉蛋兒紅撲撲,糯糯的:“要抱抱。”沈戾:“!!”常年處於食物鏈頂端的沈少坐懷不亂,嗬,靠這點兒手段就想勾引自己?十幾分鐘後,沈少的領帶到了宋祁星纖細潔白的手腕上。然後宋祁星哭了一晚上。第二天,宋祁星全身痠痛,轉頭一看沈戾這狗比竟然躺自己邊上?!WTF?!一巴掌揮過去:“姓沈的,你這狗比對老子乾了什麼?!”沈戾被打醒,卻也不生氣,將人摟進懷裡:“乖,彆鬨。”宋祁星:去die!我的其他預收也看一看呀~
34.3萬字8 10688 -
完結263 章

完了,少將彎了[星際]
當少年發現自己來到未來星際世界的時候,他是有點小懵逼的。 嗯,懵逼程度請參考原始人穿越到現代社會。 現在他成了這個原始人。 還好抱上一個超級粗的金大腿,膚白貌美大長腿的高冷星際少將閣下帶你裝逼帶你飛。 可是大腿想要把你丟在領地星球裏混吃等死做紈絝,還得履行為家族開枝散葉的義務做種豬怎麼辦? “不、用、了……我,喜歡男人。” 絕對是純直的少年挖了一個坑,然後用了自己一輩子去埋。 嗯,這其實就是一個披著星際皮的霸道元帥(少將一路晉級)愛上我的狗血文。 又名《全宇宙都認為是我這個被掰彎的直男掰彎了他們的男神閣下》 每天上班都要在戰艦上被少將閣下強行塞狗糧的部下們一邊強勢圍觀一邊冷笑。 撩了少將大人你還想跑?呵呵。
107.6萬字8 7224 -
完結12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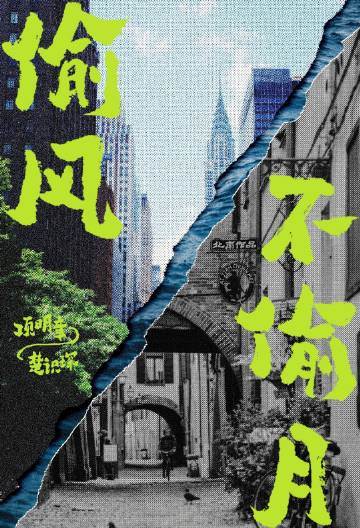
偷風不偷月
穿越(身穿),he,1v11945年春,沈若臻秘密送出最后一批抗幣,關閉復華銀行,卻在進行安全轉移時遭遇海難在徹底失去意識之前,他以為自己必死無疑……后來他聽見有人在身邊說話,貌似念了一對挽聯。沈若臻睜開眼躺在21世紀的高級病房,床邊立著一…
39.3萬字8 612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