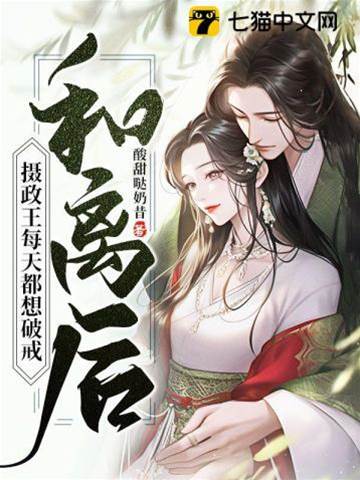《重生之庶女歸來》 第765章 誰是你的夫君
帳外的人,究竟是誰?孟瑄的朦朧睡當即一掃而空。
呼啦!
堆滿奏報的桌案被撞倒,東西滾落一地,有些撞到了火盆,燃起零零星星的火苗。但無論是孟瑄,還是熠迢,此刻都無心滅火。
他們的心神,完完全全被帳外的那個聲音給奪走了。
紫霄驚問,「你是人是鬼?」然後,對方含笑答道:「朗朗乾坤,只要心裡沒鬼的人,肯定就看不見鬼。喏,我的影子和你一樣,也踩在腳底下呢,我是人。」
世上最妙的仙樂,也比不上那一句話的分量,因為那道聲音屬於何當歸。
帳外,紫霄不可置信地說:「可是,可是他們都說你死了,為什麼,不可能……夫君為了你的死連吐幾盆,都垮了,前日剛見起,你就又來氣他,太過分了!」
何當歸奇怪地反問:「既然他很為我的死訊而難過,那我平平安安回來了,怎麼算是氣他呢?」
「你……」紫霄有點切齒的意味,「好個伶牙俐齒的妮子,真不能小瞧你!」
頓了頓,何當歸問:「你是何人?」
帳,孟瑄和熠迢的心一。熠迢要衝出去幫腔,孟瑄拉住他的袖子。
紫霄單手叉腰,一層甲胄包裹下的姿依然玲瓏窈窕,驕傲地說:「我是孟將軍的妾室,將軍是我的夫君。紫霄,這是我的名字。我是奉了公婆之命,來營里服侍將軍的。」
帳外長久的沉默。
熠迢低咒一聲,待要衝出去,孟瑄卻不鬆手。這算不算隔岸觀火?
最後,何當歸居然笑了,笑聲如銀鈴般悅耳聽,道:「巧了,我何當歸是孟將軍的正室,比你大一級。在家裡,你可以喚我一聲『姐姐』;外人面前,禮不可廢,你還是恭恭敬敬喊『公主』才能彰顯咱孟家對天恩浩的激之,紫姨娘。」
「公、公主?你做夢呢!」
何當歸悠然道:「皇上認我為妹,不是公主是什麼?注意你的口吻和態度,這裡是騎兵營,別給將軍丟臉。哦,順便說一句,我是奉了天子之命,來營里服侍將軍的。」
紫霄被堵得說不出話來,一雙烏溜溜的眼珠上下轉悠,閃著驚疑的。
「哎呀!」
何當歸一聲,把一帳之隔的孟瑄得口一。
何當歸單手扣住紫霄的巧下,淡若花瓣的指甲輕刮紫霄的臉蛋,引得一陣戰慄,「你……你……」
「要『姐姐』,不能這麼沒規矩。」何當歸更正,笑意更濃了,「多水靈的人,我見猶憐的,何況男人乎。不過湊近了看,竟有點照鏡子的詭異,你覺得呢,紫姨娘?」
「我……我……」
帳中傳出一個聲音,為紫霄解圍:「本將軍給你的事辦妥了麼,紫霄?如果你懶的話,會讓我很為難呢。」
是孟瑄。
瞬間弄懂了,他是在幫解圍,紫霄也瞬間變回了驕傲的孔雀王,鮮亮的羽抖擻起來。輕哼一聲,闊步離去。就算何當歸大難不死又如何?孟瑄,再也不是一個人的了。
素手掀簾,簾后的那張容,那眉,那眼,正是孟瑄午夜夢回的小樓里,反覆出現,又一次次消散的那張臉。
可現在不是夢裡,的臉也是實實在在,只要靠近就可以的到。
他沒有做夢,而且再也不用勉強睡去,只為夢裡能多看一眼了。可為什麼站得那樣遠,笑容淡淡疏離,這樣遠的距離覺不到的溫度,他怎知是不是真的毫髮無損?
熠迢滿臉激地問:「小姐,真的是您嗎?為什麼您沒死?」
「啊呀,難道你也著我一去不回?」
「不不、屬、屬下絕無此意!」熠迢一著急,口齒都磕了。
何當歸一笑:「逗你玩的,熠迢,好歹你也是六品軍階的副將一名了,怎麼一點兒不逗?」
「我……小姐你被敕封公主了?這是怎回事?」熠迢剛從何當歸之死的悲痛中平復,突然見到活生生的何當歸,又興,又衝擊,還很想弄明白,「你是如何逃出虎口的?我聽說人選定的獵,是必然要拆骨腹的,從無例外!」
其實,段曉樓那邊的錦衛幾天前就從齊玄余那裡知道,何當歸很大可能還活著,但段曉樓還固執地認定孟瑄負心,對何當歸下落不明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於是,這個不算喜訊的喜訊,沒有傳來騎兵營這邊。
何當歸笑笑,簡單一句「運氣好而已,我命太,連閻王爺也不收」,戲謔著一語帶過。
熠迢又看向孟瑄,更加疑了。為了防著紫霄對公子做些什麼不好的事,自己日日夜夜都守著公子,沒離開過半刻,而公子就是睡睡睡,沒出中軍帳半步。可公子竟然早就知道何當歸沒死?
熠迢還想打聽更多,孟瑄掃他一眼,目好似兩道冰錐,叉、叉、叉!
「熠迢,王副將投訴你缺勤,有沒有這回事?熠迢,別以為你是我的人,我就能寬放你的懶惰。軍中不收留懶漢,給我一個你為副將而缺勤不練的理由?」孟瑄板著面孔,大公無私地審問著。
熠迢差點沒吐,自己為什麼缺勤,公子不是最清楚的嗎?連著五日五夜,自己生怕公子一個想不開而做出什麼傻事,拋開所有一切,只守著公子。現在何當歸回來了,公子滿復活,滿面紅,卻揣著明白裝糊塗地審問自己。這算不算過河拆橋?
何當歸走過去,輕推熠迢一把,提醒他:「騎兵營是三日一點卯,你缺勤五日,也才誤了一次點卯,最多罰罰餉銀。還不快去校場補練,爭取個寬大理?」
熠迢「哦」一聲跑出去,跑了老遠才醒悟過來,公子是故意要支開自己的吧?
「清兒,你走近些,讓我看看你。」孟瑄語調平淡,帶著點音。
何當歸乖巧垂頭,聽話地走過去,依偎在那片結實的膛上。輕如羽的重量,重逾千鈞的錮,孟瑄的手臂一瞬間收,得不可思議。彷彿攢了幾輩子的力氣,全花在這一次擁抱上了。
蓄勢待發的捕籠,扣住了一隻心甘願的小白兔。這是此時此刻最恰如其分的描述。
「再也不放你出去了,再也沒有第二次了。」孟瑄的下抵著的頭頂,每一個字都是咬牙切齒說出來的。
何當歸悶悶道:「喂,你的鎧甲硌到我鼻子了,你的肩傷都還沒好,熠迢怎麼不給你卸甲?」
孟瑄閉眼,夢囈般喃喃:「昨晚,夢裡頭的你,我也能抱得到,但覺一點都不實在。我還以為今生今世,只能在夢裡看見你了。」
何當歸莞爾:「獃子你裝什麼傻,那是柏煬柏名產,『幻夢』耳。咱們又不是第一次用這種方式見面,你還沒習慣過來?快,先卸了這套邦邦的鎧甲,讓我瞧瞧你的傷,對了,我夢裡拿給你的葯,按時按量的吃了嗎?——喂,你先鬆開我!」
孟瑄不肯鬆手,反而愈抱愈了。眼裡的寒冰化水,一滴滴打在懷中人雪白纖細的後頸上。
「孟瑄!孟瑄?孟沈適!」
「相公!」
「人!請放手!」
孟瑄默默搖頭,不放,不放,任何人都休想再讓他放手。
大帳里的兩人糾纏著,帳外也傳來了類似的對話——
「放手!」
「你才放手!」
孟瑄與何當歸同時一愣,聽到帳外的爭吵聲是兩個人的聲音,其中一人是紫霄。孟瑄到奇怪的原因是,整個營中除了他懷裡的,還有外面的紫霄,不應該出現第三個人聲音。
「啊!」陌生聲尖,「你扯疼我了,瘋人!」
紫霄怒道:「呸,你是從哪兒冒出的俗村姑,連軍營也敢闖,你嫌命太長了?」
對方頓了頓,大概有點招架不住紫霄的氣勢洶洶,帶著委屈說:「你又是什麼人,憑什麼罵我是村姑?我是揚州城人氏,有孟將軍贈我的信,連外面的軍爺都放我進來了,你是什麼人,又兇又霸道,得我好疼!」
孟將軍的信?何當歸秀微挑,用眼神詢問孟瑄,孟瑄回以無辜的眼神,並開始皺眉回思。
揚州來的年輕人,到底是哪一個?可真的想不起來。
外面,紫霄冷笑道:「揚州村姑,你口中的孟將軍,不巧就是我的夫君。你一個年紀輕輕的村姑,打扮這樣來軍營找我夫君,我都替你臊得慌,當然得多問一句,你找我夫君有什麼事?」
何當歸略垂著頭,扯一笑。夫君,夫君,喊得真順溜。
這時,孟瑄湊過來,在領口嗅到清淡花香,頓時陶醉閉眼,張大了鼻孔想嗅到更多。
緻俊,卻是一副豬哥相,惹來何當歸的嫌棄,一把推開那顆頭。
彷彿還嫌不夠,外面兩個人一言不合,竟然打起來了!清晰的耳聲,推搡聲,一個哭:「誰是村姑,我爹是油商,我是城裡人家的兒!」另一個:「你推我?你敢推我?我夫君是將軍!」
猜你喜歡
-
完結433 章

農女為商:撿個王爺來致富
「無事」青年柳小小機緣際會到了古代,卻成了一個還沒進門就死了丈夫的「掃把星」。爹不疼娘不愛就算了,還要繼續把她嫁給「公公」沖喜!行吧,既然你們要這樣做,那就別怪我不客氣了,柳小小開啟了實力虐渣爹,懟渣孃的狀態。之後,本想手握靈泉發家致富奔向小康,偏偏有那不長眼睛的鄰居和親戚湊過來非要「借光!」光,沒有。懟,管夠!當日你們對我百般刁難,如今我讓你們高攀不起。隻是,我後麵那個尾巴,雖然你長的是高大帥,可現如今的我隻想發家不喜歡男人,你為什麼要一直跟著我!!!尾巴在身後委屈巴巴的看著她:「我賬房鑰匙在你那呀,我沒錢,所以隻能跟著你了呀。」柳小小:「……」誰特麼想要這玩意,如果不是你硬塞給我我會接?
74.2萬字6.4 76406 -
完結105 章

盲妾如她
俞姝眼盲那幾年,與哥哥走散,被賣進定國公府給詹五爺做妾。詹司柏詹五爺只有一妻,伉儷情深,因而十分排斥妾室。但他夫妻久無子嗣,只能讓俞姝這個盲妾生子。他極為嚴厲,令俞姝謹守身份,不可逾越半分。連每晚事后,都讓俞姝當即離去,不可停留。這樣也沒什…
49.6萬字8 28916 -
連載205 章

食全食美
餐飲大王師雁行穿越了。破屋漏雨,破窗透風,老的老,小的小,全部家產共計18個銅板。咋辦?重操舊業吧!從大祿朝的第一份盒飯開始,到第一百家連鎖客棧,師雁行再次創造了餐飲神話!無心戀愛只想賺錢的事業型直女VS外表粗獷豪放,實則對上喜歡的女人內心…
75.2萬字8 15259 -
完結56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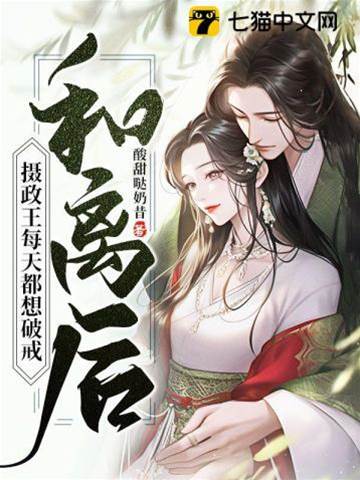
和離後攝政王每天都想破戒
葉芳一朝穿越,竟然穿成了一個醜得不能再醜的小可憐?無才,無貌,無權,無勢。新婚之夜,更是被夫君聯合郡主逼著喝下絕子藥,自降為妾?笑話,她葉芳菲是什麼都沒有,可是偏偏有錢,你能奈我如何?渣男貪圖她嫁妝,不肯和離,那她不介意讓渣男身敗名裂!郡主仗著身份欺辱她,高高在上,那她就把她拉下神壇!眾人恥笑她麵容醜陋,然而等她再次露麵的時候,眾人皆驚!開醫館,揚美名,葉芳菲活的風生水起,隻是再回頭的時候,身邊竟然不知道何時多了一個拉著她手非要娶她的攝政王。
99.6萬字8 920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