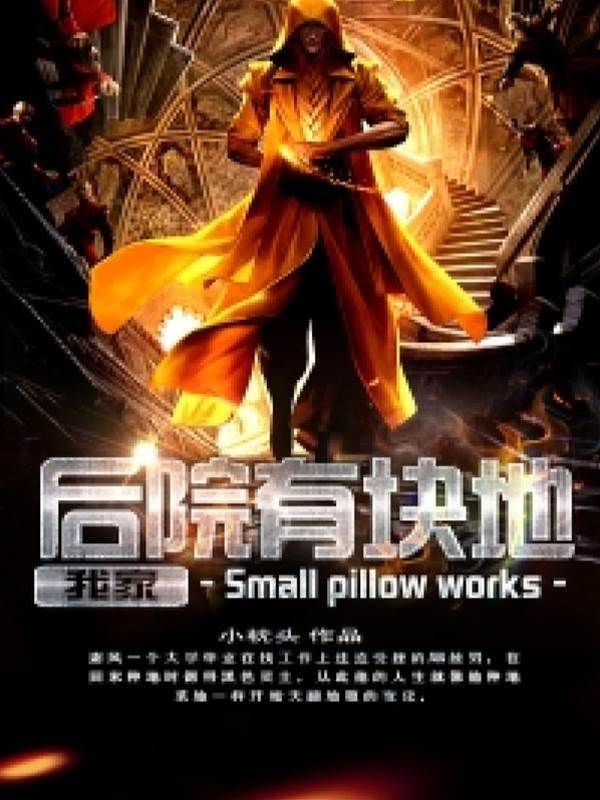《悍農:情蕩狼洼嶺》 第1章 脫下黃綢褲
一九七五年,夏天。
郁郁蔥蔥連綿不絕橫亙百里的狼洼山下是一片一眼不到邊的黃土地。
太如同一個大火球一樣烘烤著正在土地上辛苦勞作的狼洼嶺村民。男人們著黝黑的脊背,揮著鋤頭,豆粒大的汗珠劈劈啪啪掉在已經打了蔫的玉米苗上。在這群男人的前面是一群嘰嘰嘎嘎的人,們穿著布小褂,袖口高高挽起,蹲在地上費力的拔著草,黑油油的胳膊上滿是泥土。
生產隊的隊長李巧艷站在田頭指手畫腳的,不時發出一兩聲大聲的吆喝,催促著正在勞作的社員們。伴隨著的吆喝,坐在田頭一個三兩歲的娃哇哇的哭起來。李巧艷看一眼娃,可能是良心發現,大聲嚷一句,
“大家歇歇吧!”
聽到隊長的命令,男人,人幾乎同時放下手里的工,三三兩兩的回到田頭蹲坐下來。
一個二十多歲,長的面目清秀,臉上黑燦燦,前高高隆起的人快步走到那娃邊,蹲下,把娃攬在懷里,起襟,,碩大的黑乃子馬上跳了出來。人把乃頭迅速塞娃的里,那娃馬上停止了哭泣。
下午不上學,也和大人們在一起勞的十五歲年張一寶就站在離人不遠。這一幕被張一寶看的一覽無余,真真切切。張一寶就想,“玉蘭嬸兒的乃子真大啊!”
張一寶目不轉睛的看著,人突然抬起頭,看到張一寶那眼神,臉上慍怒道,
“看啥呢?才半大個小子,咋就這麼不學好呢?”
男人們聽到吳玉蘭的聲音,對著張一寶嘎嘎的笑笑,
“小子,還沒長全呢吧,咋就不像你爹呢,看你爹是多老實的一個人,跟你爹好好學學。”
張一寶臉上一紅,急忙移開目,怯的躲到一邊去。
張一寶的父親名李滿囤,是厚道的一個莊稼漢,老農民,平日里沒有一句話,是那種一碌碡碾不出個屁的主兒,大家給他送一個外號“老蔫”。正因為這樣,李滿囤在四十多歲的時候還沒有娶上婆娘。
那是在一個寒冷的冬天,大雪下了足足有一尺厚,嶺上來了一個要飯的人,那人二十來歲,長的面目白皙,雖說衫破爛,但也掩飾不住婀娜的條。人已經得奄奄一息,沒有走路的力氣。是李滿囤給了點吃食,使人活了過來。就這樣,人就留下了,人名張花朵,也就是張一寶的親娘。
在這個貧窮落后的村落,上至大隊長,下至生產隊長,都是人。人統治這個龐大的村落不知道有了多年,男人的地位是很卑微的。李滿囤滿盼著張花朵能給自己生下一個娃,也自己在村子里揚眉吐氣一回。可是張花朵的肚子偏偏不爭氣,生下來一個帶把的。李滿囤懊惱幾天之后,終于還是歡喜了,自己老來得子,也算是一個有福氣的人了。
在這個村子里,孩子都是隨母姓。張一寶就在這麼一個貧窮的家里茁壯長。雖然說村窮廟破,家貧狗瘦,但是張一寶一家也算是苦中作樂,日子過得還算說得過去。
在大人們的笑罵聲中,張一寶扎了人堆。歇下來的男人們吧嗒吧嗒的著旱煙,村子里老季云開眨眨眼皮,臉上帶著壞壞的笑,
“老爺們們,我給大家出個謎語,誰要是猜上來,今兒個的晚飯我請了!”
季云開四十多歲,一只腳有點瘸,是一個自詡肚子里有點墨水說笑,想人有點瘋狂的漢。大家一聽他要出謎語,就知道狗里不會吐出象牙來,急忙攛掇,
“說啊!說啊!”
季云開故作深沉,清清嗓子,說道,
“小奴家,一掐腰,五個摟著腰,一把下那黃綢,出烏黑一撮!”
人群立即躁起來,嘎嘎的笑個不停,就是連那人堆都發出了陣陣的竊笑。季云開一本正經的說,
“大家都說說,是啥子呀?”
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誰也說不上是什麼來。
張一寶隨口說,
“筆!”
季云開臉上帶了笑,
“嗯!還是這小子聰明!得了,今晚上到叔那兒,叔請你了!”
正在這個時候,大隊長陪著一個矮胖的男人走了過來,大家不約而同齊刷刷站起來,低著頭,不敢看大隊長。
大隊長楊玉珍,才三十多歲,長的那是嶺上的一朵花,要多就有多。嘟嘟的臉蛋,白皙的脖頸子,滿堅的大,翹。楊玉珍給人一種不怒自威的覺,任何人看到,就覺得自己矮半截。楊玉珍這個大隊長下面管著狼洼嶺上二十一個生產隊,那權力大了去了,儼然就是狼洼嶺的皇帝。平日里,大家本輕易看不到,不知道今天來到這里是要干什麼?
猜你喜歡
-
完結76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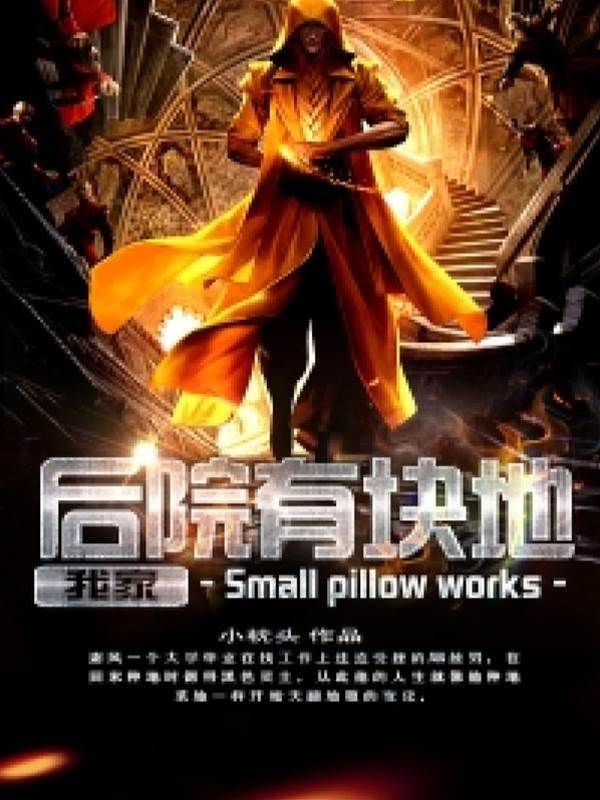
我家后院有塊地
謝風回家種地時偶得黑色靈土,從此他的人生開始天翻地覆的變化,種菜種花種一切。 一路的逆襲,一路走上人生巔峰。
131.2萬字8 41201 -
完結665 章

鄉艷:狂野美人溝
山村青年周二狗胸無大志,他青春萌動時就滿村子的調戲女人,終于在山上的茅草叢推倒了留守活寡王香妹,付出了自己的第一次………… 野性難羈的山里妹子,美艷的鄉村小寡婦,支教年輕美女教師,大學生美女村官,通通撲面而來……花色撩人,幸福的生活……
164.8萬字8 66847 -
完結1268 章

鄉村如此多妖
一個大學畢業生畢業後陰差陽錯的來到了偏遠的鄉鎮,樸實的鄉村,“妖怪”眾多,美女環繞,看他如何降妖。
228.2萬字8 20411 -
連載751 章

村野小神醫
學成回村,原本只想安靜賺錢,治病救人,奈何鶯鶯燕燕主動上門。…
128.5萬字8 51157 -
完結71 章

離開豪門后回村養老火了
云舒穿成一本小說里的豪門養女。女主即將回歸,云舒會從豪門千金變成鄉下村姑,從此成為襯托女主的對照組。上輩子云舒忙著賺錢,還沒享受就死了,實在虧這輩子她只想過悠閑養老生活。…
38.4萬字8.18 1013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