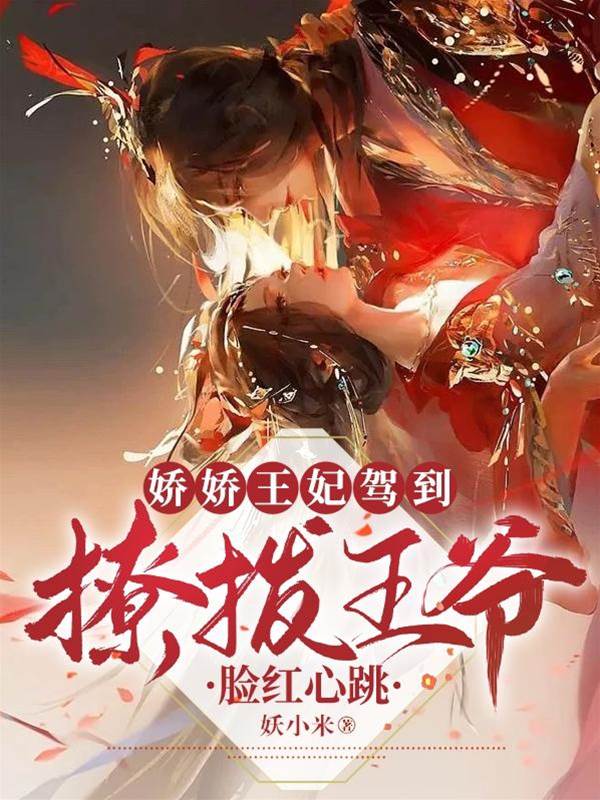《小千歲》 番外【太子哥哥】(2)
沈忠康坐在對面,看著新帝一改往常模樣連哄帶騙地將戶部尚書糊弄走,等人走了之后就自個兒愁眉苦臉的一聲接著一聲的嘆氣,他開口說道:“陛下可是缺銀子?”
贏元煜瞬間看他:“元輔有?”
沈忠康頓笑:“老臣可沒有,沈家什麼況陛下也知曉,若只是萬八千兩的還行,可多了就是賣了老臣也拿不出來。”
贏元煜眼中瞬間失了神采:“您都沒有,問朕缺不缺做什麼?”
他缺錢都快缺瘋了!
沈忠康說道:“老臣沒有銀子,可其他人有啊。”
贏元煜愣了下:“其他人?”
“陛下可是忘記了,前些時候白家送來的折子?”
沈忠康說道,“白家這兩年沒朝著朔州運送糧草,早前您給了他們皇商的牌子,又賜了白小公子縣爵的封號,如今的白家在整個朔康以及江南一帶,就沒有比他們更富的……”
贏元煜聽著時眼睛再度閃亮,忍不住就想起白家的事。
那白老爺子行商厲害,沒想到出了個白錦元更是青出于藍。
這兩年朝中銀錢不支之時,白家數次朝著朔州運送糧草支援軍需,還曾主捐贈過一大批銀子在去歲旱災時幫著賑災,他為此特意賜了白錦元爵位,還一度心想要將他招攬進戶部。
可那小子有些乖僻,不喜京,百般推辭不肯只說要守著白老爺子養老,暗地里卻幾乎領著白家商隊跑遍了整個大業。
這滿大業里上至皇室宗親,下至黎民百姓,貴如金銀玉,廉價如草席麻繩,那就沒有他不做的生意。
今歲年前,白錦元更是將生意瞄準了海外。
前些時候白家那頭就上了封折子,想要請求朝中開海,允許白家造船出海。
只那折子一直著,朝中也有不人為著開不開海吵得不可開。
沈忠康坐在對面,手撿著棋盤上的棋子扔進一旁棋盒里:
“陛下早前就有意想要重開海,只是朝中有些大臣固守舊念一直攔著,他們所擔心無非是海一開既不見利益又會讓沿海生出子,既如此,倒不如先允了白家所請,以朝廷之名讓白家先行造船出海。”
贏元煜若有所思:“元輔是想跟白家以利換利?”
沈忠康點點頭:“朔州重建需要銀子,今年秋收又還有數月,國庫銀錢捉襟見肘。”
“白家想嘗頭鮮,讓朝中開海,那讓他們以銀錢換出海機會他們想必也是愿意的。”
“到時陛下給白家一個方的份,他們以大業特使份出海,再派遣沿海員隨行,這樣既能安朝中,試探開海之后的況,也能讓白家心甘愿的掏銀子,也算是兩全其。”
贏元煜沉了片刻,倒覺得沈忠康所說的未必不是辦法。
他本就有意開海,只是一直沒有好的人選。
白錦元那小子他是放心的,畢竟雖然改了姓可到底還有阿窈鎮著呢。
那小子敢來,阿窈第一個打斷他的。
至于別的……
贏元煜也不在意,朝中那些個老古板愿不愿意干他什麼事,他們要再囂,行啊,那倒是了家底兒給朝廷解燃眉之急,只要他們能拿得出白家給的銀子,他也樂意將就著它們的意愿。
等下次缺銀子了,再開海。
兩人商議了一會兒,贏元煜就決定照著沈忠康所說的去做,除了允白家造船出海之外,他還決定再賜白錦元一個位,將那小子捆進朝廷里,其次只要白家愿意以錢財支援朝中,便允白錦元以大業朝特使的份出使海外,八百差隨行護他周全。
心事放下之后,贏元煜臉上瞬間明朗起來。
他代著潘青傳旨讓禮部和工部的人進宮,一邊重開了棋局跟沈忠康對弈起來。
二人說著閑話,沈忠康問:“聽說袁家之人不日就要押解京?”
贏元煜點點頭:“阿窈說與信件同時啟程,算一算應當就這幾日了。”
說起這個,他就腦袋疼,
“袁家的人也就罷了,送回來就送回來,該怎麼判就怎麼判,可您知道嗎,阿窈居然又送回來個子。”
沈忠康愣了下,隨即就忍不住笑起來。
薛諾他們剛離京時,手里握著區區五萬兵力,本就打不過西陵王府。
那會兒北狄正是最的時候,那狡猾兒就沒打算跟袁家杠,只讓姜和邱長青領著當初抓到的袁晟,帶了兩萬人前往朔州附近滋擾,加之早前就派去的探子,用一些上不得臺面的手段牽制袁家兵力,而和沈卻腳下一轉領著另外三萬人直奔江。
大業是有藩王的,各地藩王手中也都有屬軍。
那江是王的地盤,王圓膽小,兩人去了之后二話沒說直接開打,先將人打了個措手不及險些搶了藩地,接著曉之以之以利,半強半脅迫的讓王上了他們的賊船。
可王也怕薛諾他們事后翻臉,更怕朝廷將來追究。
薛諾的作就來了,直接以新帝的名義征選了王家的人進宮。
薛諾得了江四萬兵,軍備、武無數,與此同時,王的外甥就了薛諾第一個送回京城的人。
那時候贏元煜雖然驚愕,可也諒薛諾手中什麼都缺,且覺得后宮多上一個妃子就能換得王歸心,早日得了朔州大捷也值得,所以將人收進后宮,為表寬厚還給了個不錯的位分。
可萬萬沒想到,那只是開始!
那之后每隔一段時間,薛諾都會讓人送些貌如花的子回京,有時是一兩個,有時三、四個,那些子或是藩王親眷,或是各地強族、武軍的兒。
人進京了,贏元煜總不可能晾著。
再加上有王的事在前,拒收了其他子只會讓那些人心有不安。
怕會鬧出子,贏元煜只能將人統統放進了后宮里,以至于短短兩年多時間,他原本只有一個皇后兩個妃子的后宮充盈的讓他都記不住那些妃嬪的臉。
沈忠康看著新帝一臉的煩悶,忍不住問道:“長公主這次送回來的又是誰?”
“聽說是朔雍關駐軍統領魯常存的妹妹。”
贏元煜見沈忠康笑起來,直接扶著腦袋就抱怨道,
“以前要打朔州也就罷了,如今朔州都已經打下來了,還拿朕賣人。”
知道的,是他恤下臣,想以納妃安各地。
不知道的還以為他在賣,搞得他跟小倌兒似的……
“您說說,一小姑娘家家的,怎麼就能那麼記仇。”
“當初皇后不過是提了一句讓秦家跟長垣生米煮飯,可那事兒不是沒嗎,怎麼就能一直記到現在,隔三差五就送人回京,皇后每次都氣得臉青,連對朕也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
他跟皇后年夫妻,又共患難過,深不壽談不上,可他對皇后終究是不同的。
若只是尋常選妃也就算了,偶爾充盈幾個應付一下朝中那些人,皇后也不會有什麼不樂意。
可薛諾隔三差五就來這麼一回,送回來的那些子更是一個比一個厲害,偏偏家背景沒一個輸給皇后的,這就讓得皇后氣的紅了眼睛。
贏元煜近來很回后宮,怕得就是一去就瞧見皇后滿是幽怨的眼神,還有那一屋子鶯鶯燕燕。
與其對著那八百只鴨子似的嘰嘰喳喳吵個不停人,或耍心眼,或使手段,不是送湯就是跳舞,大冷天都能穿個薄紗跟鬼似的幽幽唱著小曲跟他“偶遇”,他倒不如留在書房批折子。
他愿意為著大業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沈忠康知道這會兒要是笑起來有些不厚道,可實在沒忍住。
薛諾那丫頭是真的損得沒邊兒了。
贏元煜惱怒道:“還有長垣,朕好歹跟他多年好友吧,他也不攔著阿窈一些,居然還寫信怪氣。”
“等回頭朕就給阿窈賜幾個俊俏年,再找幾個模樣標志的送后院里,看不氣死他!”
沈忠康聞言笑意更深,倒沒把新帝的話當真,只是忍著笑說道:“陛下是不是誤會了?如今朔州戰事已平,長公主不需要再收攏人心,又怎會再送人給您。”
贏元煜瞪大了眼:“那干嘛還送人回來?”
沈忠康說道:“長公主大抵不是將人送給陛下的。”
“前些時候長垣給老臣寫了信回來,說魯將軍父母早亡,他那妹妹與他相差近二十歲,一直如珠如寶的寵著,現在到了說親的年紀,可朔州邊地剛經戰事,且也沒什麼合適結親的對象。”
“魯將軍就托了長垣和長公主將他妹妹送進京城予他姨母手中,既是來京中暫住一段時間,也是趁機看能否替妹妹尋個佳婿。”
猜你喜歡
-
完結1055 章

侯府小啞女
燕云歌自末世而來,重生侯府,她給自己定了個小目標:每天吃好喝好樂無憂!然而……她爹一門心思造反,她哥一門心思造反,她嫁個男人,還是一門心思造反。燕云歌掀桌子,這日子沒發過了!
272.1萬字8 16625 -
完結10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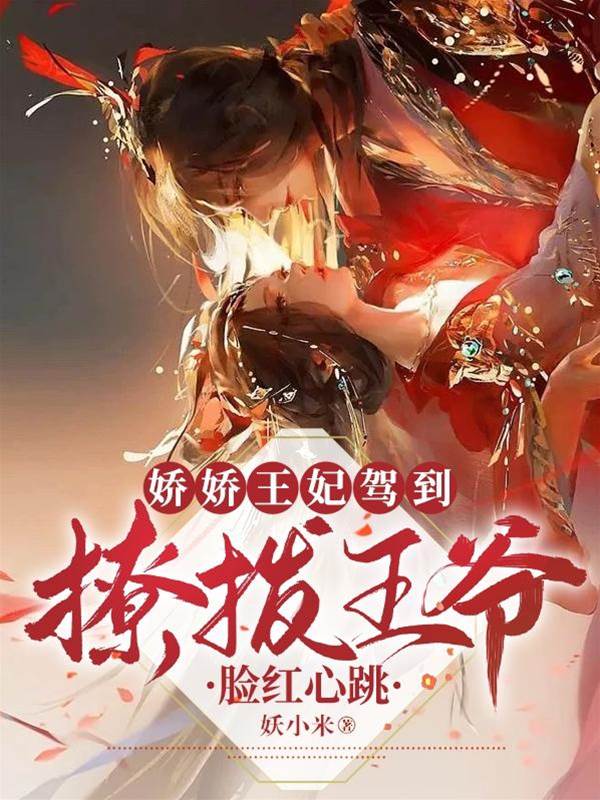
嬌嬌王妃駕到,撩撥王爺臉紅心跳
水洛藍,開局被迫嫁給廢柴王爺! 王爺生活不能自理? 不怕,洛藍為他端屎端尿。 王爺癱瘓在床? 不怕,洛藍帶著手術室穿越,可以為他醫治。 在廢柴王爺臉恢復容貌的那一刻,洛藍被他那張舉世無雙,俊朗冷俏的臉徹底吸引,從此後她開始過上了整日親親/摸摸/抱抱,沒羞沒臊的寵夫生活。 畫面一轉 男人站起來那一刻,直接將她按倒在床,唇齒相遇的瞬間,附在她耳邊輕聲細語:小丫頭,你撩撥本王半年了,該換本王寵你了。 看著他那張完美無瑕,讓她百看不厭的臉,洛藍微閉雙眼,靜等著那動人心魄時刻的到來……
183.7萬字8.18 101640 -
完結372 章

穿成短命白月光后,和反派HE了
桑遠遠穿進一本古早玄幻虐戀小說裏,成了男主那個紅顏薄命的早逝白月光。男主愛她,男配們也愛她。女主因爲長了一張酷似她的臉,被衆男又愛又虐又踩,傷身又傷心。和男主的感情更是波折重重狗血不斷,虐得死去活來,結局還能幸福HE。桑遠遠:“不好意思本人一不想死二受不得虐,所以我選擇跟反派走。打擾,告辭。”反派長眸微眯,姿態慵懶,脣角笑意如春風般和煦——“我的身邊……可是地獄呢。”她沉思三秒。“地獄有土嗎?”“……有腐地。”“有水嗎?”“……只有血。”他想看她驚惶失措,想等她尖叫逃離,不料女子呆滯三秒之後,雙眼竟然隱隱放光——“正好試試新品種!”“……”他在最深沉的黑暗中苟延殘喘,從來也沒想到,竟有一個人,能把花草種滿一片荒蕪。
57.1萬字7.92 9525 -
完結313 章
亡國后成了反賊的寵婢
姜嶠女扮男裝當了幾年暴君。叛軍攻入皇城時,她麻溜地收拾行李,縱火死遁,可陰差陽錯,她竟被當成樂伎,獻給了叛軍首領霍奚舟。姜嶠捂緊馬甲,計劃著再次逃跑。誰料傳聞中陰煞狠厲、不近女色的霍大將軍竟為她破了例。紅燭帳暖,男人摩挲著她眼角的淚痣,眸色暗沉,微有醉意,“今夜留下。”*姜嶠知道,霍奚舟待她特殊,只是因為她那雙眼睛肖似故人。無妨,他拿她當替身,她利用他逃命。兩人各有所圖,也是樁不虧的買賣。直到霍奚舟看她的眼神越來越深情,還鄭重其事地為允諾要娶她為妻,姜嶠才意識到,自己好像是在作繭自縛——
49.2萬字8 685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