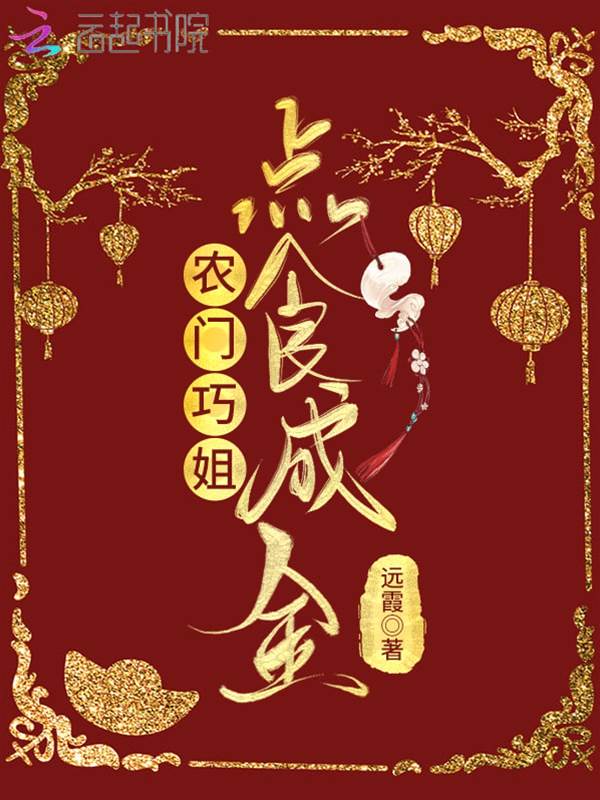《漁家小農女》 第 42 章
姐妹兩昨晚上悄悄說的這事兒,誰也沒有告訴玉玲。怕知道了會多想,也是因為談婚論嫁什麼的還早,現在說那些也無用。
玉竹想著和二約好的今日要帶去弄好東西便沒有帶竹簍子,而是找長姐要了一個撬海蠣的石鎬還有一個小陶罐用麻繩套起來提走了。
二還不足十歲,力有限,天天讓撬了海蠣回去再剝出來熬蠔油是不現實的。所以打算就直接帶二在海邊把海蠣剝出來。
其實退就三個時辰左右,劃算的還是把海蠣連殼帶的先弄回去。這樣可以弄很多,等晚上家裏人還可以一起幫忙撬海蠣。但二家裏現在就一個神不好的,也只能這樣了。是點兒,卻也比彎著三個時辰的腰去耙蛤蜊好。
玉竹和姐姐們打了招呼便準備出門去尋二,只是走到門口又想到了什麼,轉頭回去確認自己沒有看錯。
「誒?二哥?你怎麼還在家裏?」
平日裏這個時間,二哥早就上船了……
「今天咱們船不出海,我要去陶嬸嬸家幫忙。你不知道,陶嬸嬸自打見了咱家這灶,念叨了好多天了,也想要砌一個。對了,等下長姐也要過去幫忙,咱們午飯是在陶嬸嬸家吃,你等下回來直接過去,聽到沒?」
「好嘞!」
中午在陶嬸嬸家吃飯的話,那自己就要早點回來了。陶嬸嬸家吃飯都吃的比較早。
玉竹一路小跑到了二家,喊了好一會兒才看到二開門出來。臉上頂著一個大大的掌印,眼睛又紅又腫。
「二!誰打你了?!你?」
「不是……是我娘。」
二了自己的臉,不甚在意。那個人從晚上起,就不再是自己的娘了。
從來沒有見過一個人改嫁還要帶了自家死去丈夫的服走。那些都是爹的東西,就算不燒掉也該是留給阿。自己不過是想留幾件爹的裳,便手打了自己。
那一掌打掉了最後的一眷,以後再也不會為了那個人難過!
「昨天你說我帶陶罐,我都帶了,咱們走吧。」
玉竹見不想說,也不追問,拿出自己帶的蛋跟一人一個。一邊往海邊走一邊給講家裏小黑鯊的趣事兒。快到海邊的時候,二的心已經好很多了。
「玉竹妹妹!二!」
陶寶兒是跟著他娘出來的,隔著老遠就認出了人,喊著人便跑了過去。他娘只是稍稍猶豫了下,出去的手又收了回來。
魏春對二的不喜歡,一直都是因為那個娘。如今二爹沒了,娘聽說也要改嫁了,當真是個可憐的,自己一個大人還不至於跟個孩子計較。
隨們去玩兒吧,這不還有玉竹在一起麼,寶兒一向很聽話,也沒什麼不放心的。
…………
「二!你怎麼找玉竹也不我呀,好久了都。」
陶寶兒彷彿一點兒都不記得兩家的隔閡,還是和從前一樣。二的心卻很是複雜。
這還是把陶寶兒弄摔倒後頭一次正經的見他。之前他娘還來家裏大吵大鬧了一場,今日卻肯讓陶寶兒過來找自己玩兒,真是人看不懂。而且,他居然一點兒都不討厭自己,還是那樣嬉皮笑臉的。
他都忘了是誰害得他臉上差點兒留疤的麼……
二想到便問。
「上次我把你弄摔到地上,臉都壞了,你還敢來找我玩兒啊?」
「為什麼不敢吶,你又不是故意的。再說了,我爹說了,人活一生磕磕絆絆傷的時候兒多著呢,我那只是小傷。」
陶寶兒話音剛落,玉容便忍不住嘲笑出聲道:「既然知道是小傷,那躲在屋子裏不肯出來的是誰呀?還害的你娘跟你擔心了好幾日。」
「嘿嘿……」
「傻樣兒。」
二沒有排斥陶寶兒跟著一路,於是二人行便了三人行。
不過撬海蠣的地方海蠣眾多,對的小孩子來說算是危險的。於是陶寶兒被安排在了們旁邊較石頭的地方,負責去砸那些低矮礁石上的海蠣。
玉竹和二則是在礁石群里穿梭著,一個一個將石頭上的海蠣撬開取其。兩個人帶的陶罐都不是很大,只裝卻能夠裝上很多。撬了近一個時辰,兩個陶罐都還沒有滿。
而陶寶兒,早就沒了耐心,砸了一些便跑去玩兒沙扣蛤蜊去了。等他覺得無聊了,回頭一看,發現玉竹妹妹跟二還在礁石群里撬海蠣,那認真的模樣,難得的他心裏升出一慚愧。
為什麼二跟玉竹妹妹都那麼厲害,一點兒都不貪玩兒呢?
他想接著去幫忙,可惜沒有機會了。水已經漲了上來,所有村民都在開始往後退。
玉竹知道漲水時若不及時撤退後果有多嚴重,自然是拉著不捨的二跟陶寶兒直接往回走。走到沒幾步,看到沙灘上有塊灰白的東西。
海灘邊總是會被海浪推上來各種各樣的東西,枯樹樁更是長見,本來也沒當回事兒。只是陶寶兒一腳踢上去,那東西出了全貌,竟然有些像龍的模樣。
玉竹現代時是肖龍,在這裏也是肖龍,跟龍的緣分可以說是很深了。對龍的飾品,裝飾一向都偏的很。看到這塊類似龍的木頭,只覺得很合眼緣,便順手抱了起來,想著拿回家放家裏當個裝飾。
結果抱進懷裏才發現這東西並不是什麼木頭,外頭瞧著有些像蠟一樣的質,也不知道是個什麼東西。
管它呢,先抱回去再說。
三個人先去了二家,把玉竹陶罐里的海蠣都倒騰過去。又幫著一起餵了鴨狗狗。確切的說,是玉竹幫著二一起餵了鴨狗,本就沒有陶寶兒的什麼事兒。
也不是,陶寶兒他,幫忙讓了下路。
毫無存在的陶寶兒回去路上委屈極了。
「玉竹妹妹,你怎麼什麼都會啊?這樣顯得我好沒用,二會不喜歡我的。」
玉竹:「……」
只想著快點幫二做完活回家去,免得陶嬸嬸一家又全都等著自己一個人吃飯。哪裏有注意到陶寶兒是什麼心。
「你要是擔心二為這個不喜歡你,那你就去學呀。爹才剛沒了,娘也走了,咱們是的好朋友,難道不應該幫一起做點事嗎?」
自然是應該的。
陶寶兒聽完覺得很有道理。決定回家就讓阿教自己餵餵鴨。對了,他還要學生火,學掃地,學……好多好多東西!
兩人走了一段兒路就在岔路口分開了。
玉竹直接抱著懷裏的『龍』先回了自家。剛撬了那麼久的海蠣上都是腥味兒,聞著這味兒,等下吃飯都吃不下去。要先去換裳。
正換著呢,就聽到長姐在院子外頭問是不是回來了。玉竹一邊系著腰帶一邊應聲跑了出去。
姐妹三在隔壁呆了整整一下午,陶二叔家的灶臺也砌好了。晚飯便是用新灶新鍋來煮的。
看著一炊煙順著煙囪飄向天空,陶嬸嬸居然哭了起來。
玉容姐妹三倒是很能理解陶嬸嬸此刻的心,畢竟這麼多年來一直飽煙熏火燎的大多都是。
有了這個土灶,日後就再不用那樣的罪了。
這頓晚飯陶嬸嬸做的極為用心,有魚有蝦有。但專心吃飯的大概也就玉竹和陶木兩個人。陶二叔隨便拉了兩口飯,說出了他一個重要的決定。
「我想暫停出海捕魚。」
漁船是兩家共有的,要不要出海當然是要兩家一起商量。陶二叔解釋了下自己想暫停出海的原因。
「你們也知道這土灶到底有多好用。你們嬸兒跟我這麼多年,我一共也才瞧見哭過三回。這土灶能掉眼淚,可見是砌在了的心坎兒上。都這樣了,那村裏人就更別說了。」
說到這兒,大家都聽出來了,陶二叔是想改行去做這砌土灶的活兒。玉玲下意識的看了眼長姐,發現長姐已然面欣喜,顯然是贊的。
也不是就玉容一個人贊,陶嬸嬸和玉竹那也是打心眼兒里舉雙手贊的。
出海捕魚和蹲人屋子裏砌土灶,用腳想也知道還是出海捕魚更危險。尤其是村裏前幾日剛翻船沒了一個人。陶嬸嬸跟玉容每每一聽他們要出海,心裏都要跟著揪起來,一直到人平安回來才能放下。
玉容更是一晚上做好幾次噩夢,總是會夢到二妹掉進海里喊救命的場景。所以一聽到陶二叔說暫停出海捕魚,第一個便同意了。
一瞧玉容同意了,陶二叔便知道這事兒了。玉家能做主的,還是要看玉容才行。至於自家,他可是知道自家婆子早就念叨著不想他跟兒子們出海。
陶二叔眼亮的驚人。
「今天咱們砌灶的時候,後頭的今合過來瞧見了,一聽用便找了我想讓我們去給他家裏也砌一個,說是願意給工錢。不過我們家這泥磚是提前好幾天就出來準備好的,他家一點兒準備都沒有,暫時不能弄。再說我也沒還跟你們商量,就沒應。既然你們都答應了,那我明兒個過去跟他商量下的事。」
猜你喜歡
-
完結220 章
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
一個消極怠工的古代庶女,生活如此艱難,何必賣力奮鬥.古代貴族女子的人生基調是由家族決定的,還流行株連,一個飛來橫禍就會徹底遭殃,要活好活順活出尊嚴,明蘭表示,鴨梨很大.古代太危險了,咱們還是睡死算了.
116.9萬字8 27005 -
完結274 章

帶著超市回五零
華國五百強女企業家曾尛穿越了,還帶著自己旗下的超級市場穿回了平行空間困難艱苦的五十年代。望著家徒四壁,麵黃肌瘦的寡母幼弟妹,剛剛十歲,大字不識一個的‘曾尛’,不得不扛起家庭重擔,帶領全家勤勞致富奔小康!本文曆史背景架空,平行空間年代文,深究黨慎入!
66.6萬字8 44851 -
完結279 章

被太子嫌棄的小可憐後來成了首富
渾渾噩噩過了十四年的唐婉月一覺醒來,撥算盤,開鋪子,手撕偽善養父母,一躍成為京城女首富。那位曾經拒絕她的男人成了當今皇帝,竟日日粘著她。唐婉月氣,“當皇帝這麼閒嗎?”“不閒。朕來解決國家大事。朕後繼無人,缺個太子。你可願和我生?”唐婉月怒指自己,“我……生。”某男人堵了她的嘴,將人扛上了肩,直奔皇宮。“既然你同意了,其餘的話不用多說。”——————當女主不想談戀愛,隻想發展事業後,那個狗男人居然開始耍流氓!超級超級富的女主在線求助:“皇帝綁架良家好姑娘去哪裡狀告有用?我有錢。很多錢。超級多的錢。”
49.5萬字8.18 35817 -
完結4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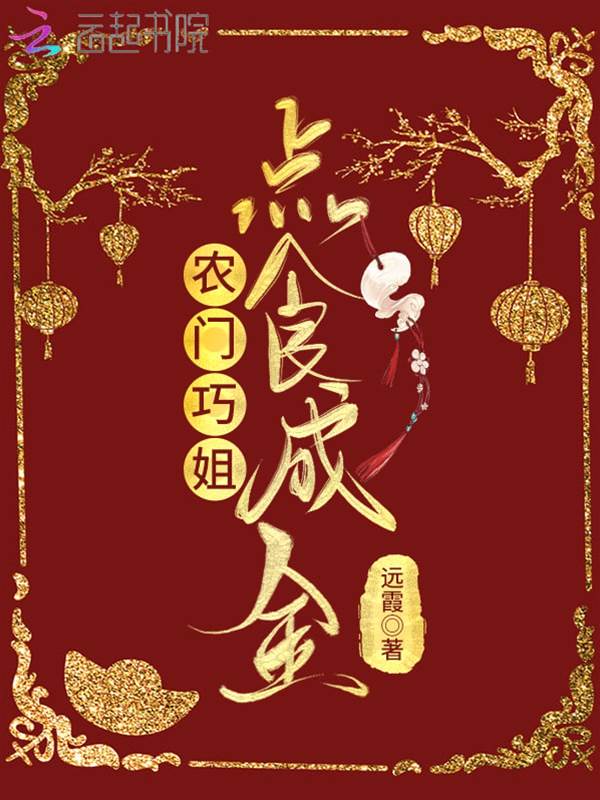
農門巧姐點食成金
高級點心師意外穿成13歲彪悍小農女-包蓉。後奶惡毒,親爺成了後爺。,爹娘軟弱可欺,弟弟幼小,包蓉擼起袖子,極品欺上門,一個字:虐!家裏窮,一個字:幹!爹娘軟弱慢慢調教,終有一天會變肉餡大包,弟弟聰明,那就好好讀書考科舉,以後給姐當靠山,至於經常帶著禮物上門的貴公子,嗯,這條粗大腿當然得抱緊了,她想要把事業做強做大,沒有靠山可不行,沒有銀子,她有做點心的手藝,無論是粗糧、雜糧、還是精糧,隻要經過她的手,那就都是寶。從此,包蓉銀子、鋪子全都有,外加一個自己送上門的親王夫君,氣得後奶一概極品直跳腳,卻拿她無可奈何。
77.6萬字8 34256 -
完結861 章

穿到荒年後,我成了極品惡婆婆
程彎彎睡醒一睜眼,成了古代大河村33歲的農婦。 四個兒子跪在床前喊娘,兒媳肚子裏還揣著一個孫子。 母胎單身33年的她,一躍成為了奶奶婆婆級別的人物。 調教四個兒子已經夠難了,沒想到天降災禍,蝗災、旱災、雪災… 唯一慶幸的是,她有一個交易商城。 叮!天然野菜10個銅板! 叮!野生肥魚200個銅板!
165.3萬字8 23939 -
連載1569 章

首輔大人夜夜翻牆:餓餓! 飯飯!
一朝穿成農家女,娘親是喪夫新寡,幼弟是瘸腿癱兒。前有村賊吃絕戶,后有奸人縱災火,一夜之間,覃家滿目瘡痍。覃宛揉著含淚擤涕的妹寶頭發揪:“哭啥,有阿姐在呢。”一個月后,寧遠縣縣北支起一家食攤。月上柳梢的西街夜市,酸辣螺螄粉,香酥臭豆腐,鴨血粉絲湯……飄香十里。縣北食肆老板揮手趕客:“快!今兒早些閉門歇業,覃娘子要收攤了!”人前只吃魚翅燕窩的李府夫人托自家丫鬟:“覃家食攤的螺螄粉,多買些來,悄悄的。”云州知府設宴款待京城來的陸宰執:“大人請用,這便是遠近聞名的覃家香酥臭豆腐。”矜貴清冷,食性挑剔的陸修淡淡瞥了案桌一眼,拂衣離去。月末傍晚,人聲鼎沸的西街夜市,刺啦一聲,覃家食肆新雇的幫廚將黑色豆腐下了油鍋。覃宛順手遞上套袖:“係上,別濺了油。”“嗯。”碎玉擊石般清明冷冽。知府大人遠遠望見這一幕,冷汗津津。那頭戴冠帽,頂著一張人神共憤的清貴容顏,站在油鍋前行雲流水炸起臭豆腐的,不是陸宰執是誰!
142.6萬字8 2900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