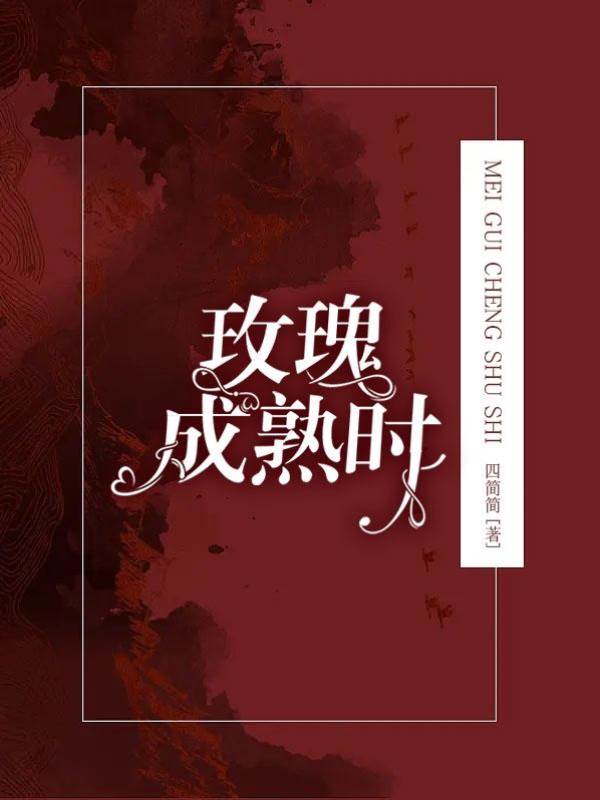《風繼續吹》 第17章 第 17 章
關門聲響起,盛悉風緩緩睜開眼睛,發了會呆,腦袋換個方向,再度閉眼。
現實讓不痛快,決定去夢里避會世。
約莫睡了半小時,江開把提溜起來,腦子還沒醒人先被迫醒了,直到坐上擺渡車,他仍然沒有就候雪怡出現在這里的事給出任何解釋。
車發之際,盛悉風放棄最后的僥幸,貓腰想下車。
江開把拉回來坐下,吩咐司機:“師傅,開吧。”
“干嘛啊?”盛悉風臉不佳。
江開說:“吃中飯。”
擺渡車啟步,穿梭在狹窄的石板路上。
盛悉風不看他,也吩咐司機:“師傅,停車。”
夫妻倆一個開一個停,司機不知道聽誰的,車速降下來,但并未徹底停下。
盛悉風打開車門就要往下跳。
擺渡車急剎車,好在車速慢,沒傷,只踉蹌一下。
江開追下去,扣住的手臂,扭頭低聲音,好言相勸:“你不去吃,家里人要以為我們吵架了。”
“誰以為誰以為唄。”現在陪他演夫妻恩,門都沒有。
江開看一會,老生常談:“我又怎麼你了?”
他的語氣那麼無奈,著忍讓。
盛悉風鼻尖一酸,忽然有點委屈。
他跟別的生牽扯不清,對方舞到和家人面前,打攪還算平靜安穩的婚后生活。
謹記自己聯姻妻子的份,知道自己沒有資格管他什麼,也時刻提醒自己以大局為重,所以沒有鬧,甚至沒有說他們兩個一句不好,只是想一個人待一會。
是他糾纏不休。
結果到頭來,卻弄得像是在無理取鬧。
不敢開口,因為開口一定是哭腔,該死的淚失質每次都在關鍵時刻掉鏈子。
兩人沉默地對峙片刻,盛悉風再走,江開沒有攔,聽到他重新上車,重重關上車門,車輛在后漸漸開遠。
別看坐車只一小會,但步行還遠,又是上坡路,費不勁,后背都出了汗,等走到他們那棟小屋,早就火冒三丈。
新仇舊賬一起數算,這時也不管什麼面不面了,沖進他的臥室,胡把他的東西往他行李箱里砸,闔都沒闔嚴實就豎了起來,里頭的和一些雜噼里啪啦沿路掉。
全然不管,來到門邊就一個大甩手,直接往廊下扔。
“轟隆。”
扔完拍拍手,解氣了一點。
手還沒拍完,人先僵住了。
本該狼心狗肺丟下一個人去用午飯的江開,不知道何時去而復返,正抱臂倚在秋千架旁,角上翹,好整以暇的模樣,見證了發飆的全過程。
“盛公主。”他慢條斯理一遍的外號,“你是不是忘了,這房間登記在我名下。”他沖微微一笑,循循善的口吻,“所以要走該是誰走啊?”
盛悉風既然扔都扔了,這個時候怎麼可能犯慫,小屋建在五級臺階之上,海拔比他高,這會居高臨下、冷冷睥睨他:“那你報警啊。”
言下之意很明顯:這潑姑我撒定了。
學著他的樣子,也抄起手臂,面無表等待他走近。
他一步步走上臺階,盛悉風看他的角度也從俯視,變平視,最后變仰視。
但這并不影響的氣勢輸出。
心里有劍,就能當個合格的刺客。
江開在離兩步遠的距離外停下來,目越過肩頭,看到里頭一片狼藉的他的東西,只一眼,又渾不在意地看向:“最后問你一遍,去不去吃飯?”
“不、去。”盛悉風一字一頓說完,扭頭就進屋。
門沒能關上,從外面被他抵住了,剛要罵人,已經被他打橫抱起來。
江開抬腳把門的品踢進去,然后反腳勾上門,走向前院柵欄外等候的擺渡車。
盛悉風發脾氣的時候才不管有沒有外人在場,既然他搞違背婦意愿這套,休怪不給他面子,罵罵咧咧,又踢又撓地掙扎上了。
跟條大魚似的在他懷里撲騰,他還得防著摔下來,一時顧不過來,抱著真有點費勁了。
“盛悉風。”他。
盛悉風小氣起來沒下限,怒極了一掌重重打在他肩頭:“我不要你。”
“名字都不給我了?”他好笑道。
他又想用經典的渣男笑蠱人,盛悉風堅決不上當。
江開嘆氣,假意伏低做小:“打不來罵不來,背后二十幾個親戚撐腰,確實了不起。”
“你知道就好。”揚起下,干脆也不掙扎了,沖他囂,“江開我告訴你,待會吃飯我就這張臉,一點點都不會收斂,你有種就帶我去。”
江開面猶疑,腳步也慢下來。
“怕了就放我下來。”見這招奏效,盛悉風對他出個譏誚的笑。
原來他也會怕。
誰知下一秒,他角牽出抹意味不明的弧度,接著將往肩上一扛,大步流星繼續走,語氣泰然。
方才的遲疑儼然不過虛晃一槍。
“那走啊,毀滅世界去。”
盛悉風腦袋朝下,倒沖,臉漲得通紅。
江開個子高特長,幾步就將扛至擺渡車旁,將塞了進去,自己則繞到另一側開門上車。
擺渡車司機從后視鏡觀察到兩人之間劍拔弩張的氣氛,識趣沒多,只默默啟車輛下山。
盛悉風不再反抗,瞇眼注視窗外景倒退,車廂被正午的曬得暖烘烘的,手心和背脊卻一個勁冒冷汗。
和江開的事鬧到家人面前,必然引起軒然大波,不知道事態會發展到什麼地步,甚至不知道還能不能收場——如果他和侯雪怡真的有點什麼的話。
這兩年來,快刀斬麻的念頭時不時飄過的腦海,但不該以這種自殺式的襲擊方式,更不該是那麼難堪的場面。
只是話放出去了,他也迎戰了,已經沒有回頭箭,又到了最討厭的正面沖突環節。
戰斗的號角吹響,面對即將到來的修羅場,大腦皮層下,極度的興和極度的恐懼矛盾并存,脈搏劇烈跳,到了沸點,在管里一片嘩然,的四肢都有明顯的麻意。
他們一路都沒有說話,除了車胎軋過地面的輕響,車里安靜得幾乎沒有一聲音。
司機的尷尬癌可能比較嚴重,夫妻倆的對峙令他一個外人如坐針氈,只盼著快點把這兩尊瘟神送走,所以他把油門踩到了底,即便擺渡車撐死也只能加速到30碼,他還是開出了秋名山車神的。
換擋,加速,點踩剎車,拐彎,一系列作行云流水,最后一個漂亮的甩尾,堪堪急剎在酒店主樓的臺階前。
盛悉風一路都在顱演習接下來可能出現的狀況,車忽然猝不及防的一下漂移,整個人也往旁邊撲去,險些結結實實撲到江開上。
江開扶,手搭在肩頭穩住形。
大戰在即,接敵方的幫助就是破壞己方士氣,盛悉風手腳并用把他推開,急后退兩步,開門跳車。
他看著避他如蛇蝎的樣子,忽然輕笑著搖搖頭。
這種輕描淡寫的態度像一針,猛然刺痛了怒脹的緒。
他甚至都不害怕嗎?
“你等這一天很久了吧?”瞪他,“正好,我也是!”
這句話一出來,就知道今天肯定別想漂漂亮亮贏他了,他們甚至還沒有正式開戰,鼻腔就已經泛起酸,說到最后的時候忍不住帶了一細微的哽咽,不知道他有沒有聽出來。
“我等哪一天?”江開好笑地問著,也邁下車來,因為個子太高,腰彎得很低,但高度預估不到位,下車之際,他的額頭還是結結實實撞上了車門門框。
“咚”的一聲,靜很大。
他悶哼一聲,手去捂。
看他倒霉,盛悉風有點想笑,只是想到如今跟他這個關系,別開臉去,生生把上揚的角下去,間哽的那口氣稍有舒緩。
他不長記的,記憶里,他好幾次腦袋撞車門了,而且每次都剛好發生在跟他鬧得很兇、真格的時候。
哭點低,相對應的,笑點也低,他這麼來一下,總忍不住破防。
一笑就容易崩盤。
輕咳一下下笑意,拾起支離破碎的緒,胡拼湊一堆當做武裝,率先往里頭走。
江開職業病發作,沒著急走,還有心思就司機方才的表現給出評價:“師傅,技很不錯啊。”
“哪里哪里。”熱心腸的司機真服了這年輕人的心大,指指盛悉風的背影示意他趕追,還小聲給他傳授籍,“孩子嘛,要哄的,很好哄的,快去啊。”
酒店二樓除了自助早餐廳,其余都是大大小小的設宴包廂,供同行的來賓擁有私的用餐空間。
著旗袍的迎賓小姐娉婷迎上來,江開遠遠就沖擺手,表示不需要引路。
夫妻倆都是一張生人勿進的臉,一路無人敢叨擾。
盛悉風跟著江開七彎八拐,像出自家房子那般練。
他的識路本領從小就極其驚人,只消走過一遍或者看過一遍地圖,幾年都不會忘,有時候甚至不需要地圖的指引,僅靠本能,他就能找到對的路。
真就是老天賞飯吃,正是靠著近乎蠻不講理的空間思維,才能準記住賽場上那復雜到足以讓普通人大腦宕機的剎車點與行車路線。
倆人停在一間掛牌“靜雪軒”的雙開包廂門前,里頭的聲響過厚重的木門約傳來,說笑聲和觥籌錯的杯聲織在一起,像定時炸-彈的倒計時讀秒。
盛悉風的心跳已經快要跳出嗓子眼,可反觀江開一秒的猶豫都不曾有,下手就推門。
行,這日子他真不想過了是吧?眼一閉心一橫,凝起殺氣,跟了進去。
猜你喜歡
-
完結80 章

我終于失去了你
十歲那年,許諾撞見父親出軌,父母失敗的婚姻讓她變得像只刺猬,拒絕任何人親近。高考完的一天,她遇見了莫鋮,這個玩世不恭的少年對她一見傾心。莫鋮與許諾完全是兩個世界的人,一個熱情如火,一個患得患失,卻在不知不覺中,許諾慢慢動了心。不料,一次生日聚會上的酒後放縱,莫鋮讓許諾失去了所有,包括心中至愛的親人。剛烈的許諾選擇了一條讓所有人都無法回頭的路,她親手把莫鋮送進監獄。多年後,兩人在下雪的街頭相遇,忽然明白了,這世間有一種愛情就是:遠遠地看著我吧,就像你深愛卻再也觸摸不到的戀人。 一場來不及好好相愛的青春傷痛絕戀。十歲那年,許諾撞見父親出軌,父母失敗的婚姻讓她變得像只刺猬,拒絕任何人親近。高考完的一天,她遇見了莫鋮,這個玩世不恭的少年對許諾一見傾心。莫鋮:你向我說后會無期,我卻想再見你一面。許諾:全忘了,我還這麼喜歡你,喜歡到跟你私奔。洛裊裊:我永遠忘不了十七歲的夏天,我遇見一個叫趙亦樹的少年,他冷漠自私,也沒多帥得多驚天動地,可怎麼辦,我就是喜歡他,喜歡得不得了……趙亦樹:我不知道要去哪里,什麼時候去,我只知道,我想見她,見到她會很開心。
33.3萬字8 6890 -
完結320 章

總裁娶妻套路深
原本只想給家人治病錢,沒想到這個男人不認賬,除非重新簽訂契約,黎晴沒得選擇,只能乖乖簽字,事成之后……黎晴:我們的契約到期了,放我走。傅廷辰:老婆,結婚證上可沒有到期這一說。--情節虛構,請勿模仿
86.9萬字8 37855 -
完結476 章

偏要
楚意沒名沒分跟了晏北傾八年,為他生了兩個孩子。 病得快死的時候,問晏北傾,能不能為她做一次手術。 卻只得到一句,你配嗎? 而他轉頭,為白月光安排了床位。 這個男人的心是冷的,是硬的。 瀕死的痛苦,讓她徹底覺悟。 身無分文離開晏家,原以為要走投無路,結果—— 影帝帶她回家,豪門公子倒貼,還有富豪親爹找上門要她繼承千億家業。 再相見,晏北傾牽著兩個孩子,雙眼猩紅:楚意,求你,回來。 楚意笑笑,將當年那句話送回: 晏北傾,你不配。
66萬字8 58640 -
完結14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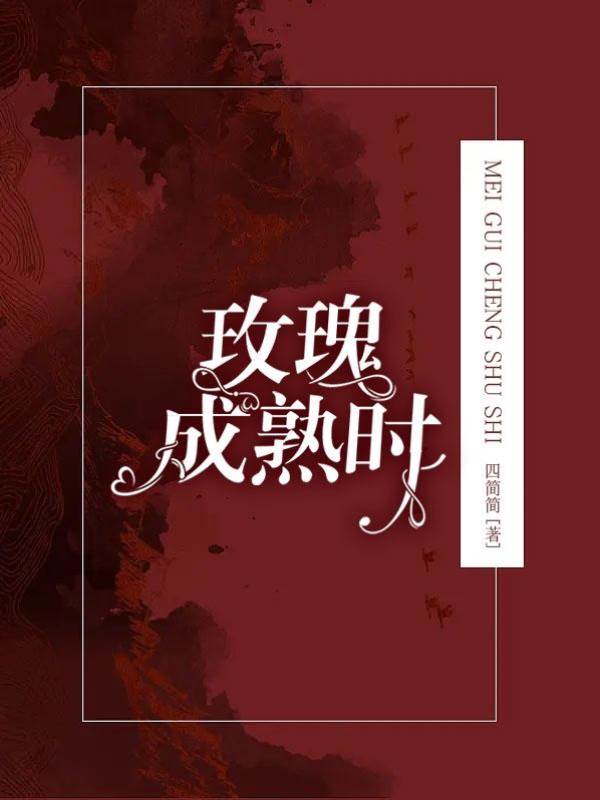
玫瑰成熟時
蘇落胭是京北出了名的美人,祖籍南江,一顰一笑,眼波流轉間有著江南女子的溫婉與嫵媚。傅家是京北世家,無人不知傅城深是傅家下一任家主,行事狠辣,不擇手段,還不近女色,所有人都好奇會被什麼樣的女人拿下。蘇落胭出國留學多年,狐朋狗友在酒吧為她舉辦接風宴,有不長眼的端著酒杯上前。“不喝就是不給我麵子?我一句話就能讓你消失在京北。”酒吧中有人認了出來,“那個是蘇落胭呀。”有人說道:“是那個被傅城深捧在手心裏小公主,蘇落胭。”所有人都知道傅城深對蘇落胭,比自己的親妹妹還寵,從未覺得兩個人能走到一起。傅老爺子拿著京北的青年才俊的照片給蘇落胭介紹,“胭胭,你看一下有哪些合適的,我讓他們到家裏麵來跟你吃飯。”殊不知上樓後,蘇落胭被人摁在門口,挑著她的下巴,“準備跟哪家的青年才俊吃飯呢?”蘇落胭剛想解釋,就被吻住了。雙潔雙初戀,年齡差6歲
23.5萬字8 17099 -
完結166 章

頂不住了,傅總天天按住我不放
[頂級豪門 男主冷傲會撩 女主嬌軟美人 後續男主強勢寵 雙潔]時憶最後悔的事情,就是招惹渣男未婚妻的小叔子。本來吃完就散夥,誰知請神容易送神難。一場意外,兩相糾纏。“傅先生,這事不能怪我。”傅霆洲步步緊逼,“ 所以你必須,我想你就得願。”傳聞中桀驁不馴的傅霆洲步步為營想偷心,其實最先入心的是他!
61.1萬字8.18 4028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