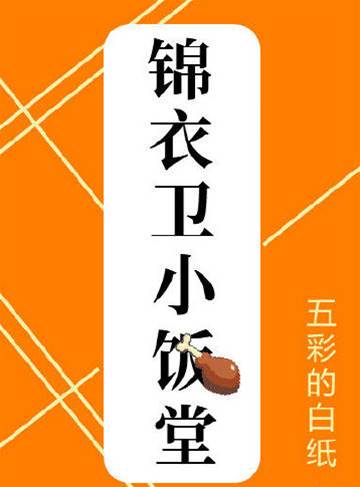《玉殿嬌》 第92章 剖心
雪霧濛濛,天地浩茫茫間,只余下了雪地里這一對新人。
拜完天地,危眉趕拉謝灼起來,他還生病,不能在雪地里久跪,“快起來,我們進屋。”
謝灼卻又飲下了幾杯雪水。
一杯敬他的父親,一杯敬他的母妃。
他心極好,是真的將這雪水當作酒在喝了。
危眉上去阻攔他,到最后竟被他拉著喝了幾杯,敬了他父皇母妃,又敬了危眉的父母。
二人一同往屋走。
窗外風雪加,這間狹小的木屋,二人相互依偎臥在一起,沒有暖盆,沒有布衾,竟也覺一片溫暖。
謝灼輕的面容,拭去他臉上的雪珠,道:“還欠你一個房夜,只能回去給你了。”
危眉霎時臉頰一紅,淡淡的紅暈,一直蔓延到耳后,與他指尖相扣,“可我們已經同過房了。”
謝灼道:“但到底是不一樣的。你和我第一次同房,就是為了要一個孩子,那時可沒有半點的溫。”
回想他初回京,竟已過去兩年。
危眉道:“其實你最初為何冷漠對我,我都能明白。”
支撐起子,趴在他上,手上他的面容,“你一個人在邊關經歷了這麼多,踏足回到京城后,我是君妻,是你的侄媳,你覺得我們之間再無可能,所以才有意避我,對我格外冷漠,對嗎?”
危眉他的眼尾,他的面頰褪去了年時青,染上了許多男人的氣質,一派的深沉。
還記得他初回京的歸京宴,滿堂觥籌錯、歡聲笑語,他一人獨自坐在案幾后,一清冷,四周的歡鬧好像都與他無關,能切切實實他上的冷傲與孤寂。
昔日他是肆意張揚的年郎,對誰如春風一般,如今卻在塞外閱遍世態炎涼,被霜雪打磨得一凌厲。
這樣的人,都是冷的,又從何去說?
謝灼道:“可是后來你冒雪來求我,我還是無法看著你去求別的男人,看著與他生下孩子。”
危眉張了張口,謝灼輕握住的手笑道:“我在北疆,什麼都沒有了,一個人看著浩瀚雪地,心中空空,孤獨無依,戒斷了一切,以為如此就不會再被事態所傷,心中無無念,直到那夜看到你冒雪而來,好像里凝滯的重新流。”
危眉忽然問道:“你以前喜歡我嗎?”
謝灼想到從前和去放花燈,那一日穿著一灑金的紅,牽著他的袖子,與他穿行在人間煙火中,看著明眸善睞,笑意繾綣,如春夜里溫的清泉。
世間沒有哪個男兒會不心的。
自然也包括他。
危眉等著他的一個答復。
謝灼道:“是喜歡的。”
“我利用了那個危家郎接近危月,可也在一次次相中,傾心于。帶去見母妃說要娶,是想這輩子都與在一起,用余下一生好好補償。”
可惜后來隔了太多的事,他到那麼晚才徹底明白自己的心意。
后來千方百計想要離開他,說上了一個虛妄,一個不存在的幻象,而謝灼的確不再是的故
人了。
他淡淡垂下眼睫,知曉應當極其在乎這一點。
危眉聽得眼眶發酸。
這是埋在心深最在意的事,聽到他這樣說,最后一怨念也煙消云散。
危眉將頭埋在他懷里,聽著他膛平穩的心跳,淚水再次沾了他的襟,聲道:“我從十一歲那年遇到你便喜歡你,后來深宮之中仍在掛念你,不管你變什麼樣子,我都喜歡你。你待我這樣好,是這世間最好的郎君。”
謝灼道:“可我雙手沾滿鮮,半只腳踏了深淵,早就不是你的舊人。”
“謝灼,你曉得我此生最后悔的事是什麼嗎?”
危眉眼里閃爍淚:“我最后悔沒有和你一同來北疆,你若是手上沾滿鮮,那我便在你殺人后,為你掉手上所有的!你若是要步那深淵,那我便拉你一把,救你出那地獄,又或者和你一同墜深淵!你所有經歷的磨難,我都愿意陪你一同經歷一遍。”
謝灼靜靜著片刻,笑道:“眉眉,我真的很開心。”
他的下來,吻住了的瓣,那灼熱的溫度淌過的,如同暖流淌過的心尖。
一切過往隔閡留下的瘡疤,都被慢慢地填滿了。
他含去眼角的細淚:“能娶你是我此生的幸事。”
從今以后,我的每一次心跳,都是因為你而起。
謝灼道:“等回京后,我們再辦一次婚典吧。”
危眉眉眼輕彎,“好啊。”
晨曦的灑向了大地,驅散了無盡的黑夜,新的一日即將到來。
外面的世界雪濃風驟,而在木屋,他們地依偎,相互取暖,藉這些年來對方上的傷口。
這一刻歲月雋永,仿佛地老天荒。
**
謝灼還在發低燒,手抵著輕輕咳嗽。
危眉讓他躺在床上好好歇息,準備自己去外面撿一些木柴,謝灼聽罷,執意下床與一起出去。
冬日冰寒,萬都在休眠,林子沒什麼野,二人獵了半刻,才獵到了一只小野兔。
回來后,危眉坐在暖爐旁,抱著他取暖,有一搭沒一搭與他聊著天。
謝灼將暖盆上烤著的野兔翻了一個面,問危眉:“我昏迷的這幾日,都未曾有人來?”
危眉搖搖頭:“沒有。”
謝灼微微蹙起眉梢,“我昏迷了三天三夜,按理說,大祁的士兵應該收到消息,雪原來找到我們了。”
危眉遲疑:“你的意思是……”
“怕是消息沒有功傳出去。”
危眉握他的手臂:“雪原遼闊,他們在來的路上一時耽擱,迷失方向也有可能。”
謝灼道:“不至于這麼久,我在北疆時,多次帶士兵雪原歷練,他們中有人認得路。”
他怕多想,摟道:“別擔心,再等個兩三日,或許那時他們便到了。”
危眉靠在他懷里,點了點頭。他雖如此安,但心里仍有擔憂,若是兩日之后,還沒有來,那到時候與謝灼該怎麼出去呢?
廊下結起了冰棱,天一日比一日冰寒。
一夜過去,救
兵仍沒有到來。
到了第二天夜里,危眉睡夢中,被謝灼拍了拍臉頰,“眉眉、眉眉?”
下意識往他懷里鉆了鉆,眼睛都沒睜開抱住他問:“是祁兵來了嗎?”
“不是,起來吧,我帶你出雪原。”
這一句話讓危眉立馬清醒,睜開雙眼,“我們現在就走?”
謝灼穿好了服,因為傷口還沒痊愈,作顯得有些遲緩。
他點了點頭:“外面是四更天,我們現在出發,過兩三個時辰天就亮了,還能走一個白日。”
危眉連忙下床,一邊穿襖一邊問:“可你子還沒好,能撐得住嗎?”
謝灼道:“可以。你放心吧。”
二人出了小木屋,謝灼牽來了馬,扶著危眉上馬。
臨走之前,謝灼檢查了一下的包袱,確保箭弩短箭都帶上了,方才離開。
危眉轉首看了一眼離開的方向,那間木屋孤零零地佇立在雪地之中,木門搖晃,“啪”的一聲,重重一聲闔上。
危眉轉而看向前方,“要走多久才能出去?”
謝灼握著韁繩,往山坡上走,“一日一夜,需要翻過這座雪山。大概明日這個時辰能出去了。”
危眉抬起頭,遠方巍峨雪山高聳,連綿仿若看不到盡頭。
一只手臂從后出攬住,他道:“別害怕,我與你一同走。”
狂風驟雪之中,行路極其艱難。二人一點點往雪山行進,等到了山林,紛紛落下的雪被林間高大的樹冠蓋住,雪方才小了下去。
謝灼在耳邊道:“此時野都在林深冬眠,不會輕易出來。”
危眉輕點點頭,然而四周靜悄悄的,猶如不可踏足的地,靜謐之下仿佛伏著危機,不由輕輕屏住了呼吸。
行了兩個時辰,危眉才慢慢適應。
握住謝灼的手,“你若是覺得累,就靠在我上歇息一會,我來策馬。”
謝灼笑了笑:“無事。”
一路上都是單調的灌木與雪景,二人一邊行路一邊談,談到遠在京中的孩兒,謝灼道:“不知道回去后,阿忱還認不認得我們?”
危眉道:“怎麼會不認識,我離京數月回去,他見到我還是很黏我,我抱他他也不哭不鬧。”
謝灼輕笑道:“那是他膽
子大,不怕生。”
危眉想起阿忱,就想起將他抱在懷里乎乎的樣子,角浮起微笑,“等我們回去,他也快周歲了呀,正是牙牙學語的時候,我們也該教他說話了。你說會先喊阿爹還是阿娘呢。”
猜你喜歡
-
完結272 章

重生之女將星
古語雲:關西出將,關東出相。 禾晏是天生的將星。 她是兄長的替代品,征戰沙場多年,平西羌,定南蠻,卻在同族兄長病好之時功成身退,嫁人成親。 成親之後,不得夫君寵愛,更身患奇疾,雙目失明,貌美小妾站在她麵前溫柔而語:你那毒瞎雙眼的湯藥,可是你族中長輩親自吩咐送來。隻有死人纔不會泄露秘密,你活著——就是對他們天大的威脅! 一代名將,巾幗英雄,死於後宅爭風吃醋的無知婦人手中,何其荒唐! 再醒來,她竟成操練場上校尉的女兒,柔弱驕縱,青春爛漫。 領我的功勳,要我的命,帶我的兵馬,欺我的情!重來一世,她定要將所失去的一件件奪回來。召天下,紅顏封侯,威震九州! 一如軍營深似海,這不,一開始就遇到了她前世的死對頭,那個“兵鋒所指,威驚絕域”的少年將軍。
110.6萬字8.38 44496 -
完結23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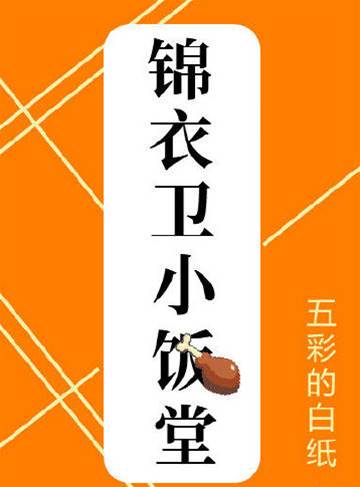
錦衣衛小飯堂(美食)
自從董舒甜到錦衣衛小飯堂后,最熱門的話題,就是#指揮使最近吃了什麼#錦衣衛1:“我看到夜嶼大人吃烤鴨了,皮脆肉嫩,油滋滋的,嚼起來嘎吱響!”錦衣衛2:“我看到夜嶼大人吃麻婆豆腐了,一勺澆在米飯上,嘖嘖,鮮嫩香滑,滋溜一下就吞了!”錦衣衛3:…
77.3萬字8.09 39237 -
完結678 章

快穿:在偏執男配心尖肆意撒嬌
【嬌軟撩系主神+瘋批病嬌男配+一見鐘情+甜寵1V1】都說:男主是女主的,男配是大家的。手拿虐文女主劇本的溫欣毫不猶豫撲進深情男配的懷里,“那邊的男主,你不要過來啊!”甜甜的愛情不要,傻子才去找虐!*霸道忠犬少爺拽著她的手腕,眸光猩紅:“不許去找他,你到底什麼時候才能回頭來看看老子?”君奪臣妻,狠厲暴君將她禁錮在龍椅上,癡迷地摸著她的臉:“天下都是朕的,夫人自然也是。
72.2萬字8 18678 -
完結282 章

國公夫人嬌養手冊/國公夫人嬌寵日常
小家碧玉、貌美身嬌的阿秀,嫁給魏瀾做了世子夫人。 魏瀾冷冰冰的,阿秀以爲她這輩子都要當個擺設,世子爺卻越來越喜歡來她的房裏,隨皇上去行宮也要帶上她一起去泡湯池。 國公府裏好吃好喝,還有世子爺百般寵着,阿秀過得像神仙一樣快活,順風順水當上了一品國公夫人,兒女也個個有出息。 直到最後,阿秀才發現魏瀾還藏了一個天大的祕密!
45.1萬字8 38864 -
完結206 章

賠罪
施綿九歲那年,小疊池來了個桀驁不馴的少年,第一次碰面就把她的救命藥打翻了。 爲了賠罪,少年成了施綿的跟班,做牛做馬。 一賠六年,兩人成了親。 施綿在小疊池養病到十六歲,時值宮中皇子選妃,被接回了家。 中秋宮宴,施綿跟在最後面,低着頭努力做個最不起眼的姑娘,可偏偏有人朝她撞了過來,扯掉了她腰間的白玉銀環禁步。 祖母面色大變,推着她跪下賠禮。 施綿踉蹌了一下,被人扶住,頭頂有人道:“你這小姑娘,怎麼弱不禁風的?” 施綿愕然,這聲音,怎麼這樣像那個與她拜堂第二日就不見蹤影的夫婿?
33.9萬字8.18 410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