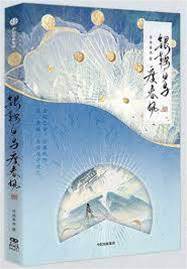《云鬢楚腰》 第147章 第 147 章
147
本來秋后年前,就是刑部最忙的時候,刑部院子里連小廝都是一路小跑的,更別提員了,陸則進宮出宮,一來一去便是兩個時辰,等他前腳剛回刑部,便立即有主事抱了卷宗來尋他拿主意,進進出出,門檻險些都被踩平了去。
直到傍晚時分,下了一整日的雨漸漸停了,才終于無人敲門了。
刑部郎中齊直進來,將上一旬的贖銀冊子給他過目。這筆銀子雖是刑部在收,但刑部實則是不管銀錢的,每旬都會朝戶部送一次銀。這也算是一貫的老規矩了。
陸則翻看了會兒,挑出幾問了問,齊直倒是一一答了,這事便也算過去了。齊直拿了蓋了刑部公印的冊子,準備要出去,想了想,又問了一聲上司,“大人還不走麽?這會兒雨停了,路上也好走,看這天,今晚夜里怕還要下一遭。”
陸則看了眼案上的公牘文書,隨口道,“理完了再說。”
齊直便應了聲,道,“那下灶房提前備了晚膳和宵食。”
陸則頷首,“多謝。”
齊直關門出去,陸則便了常寧進來,讓他回府傳個話,自己便繼續忙了,等忙得差不多了,早過了晚膳的時辰了。好在刑部灶房是習慣了有員忙得廢寢忘食的,這邊一膳,那邊便趕忙派人送來了。
菜倒也不好不差,半只剁燒鵝、一份鱸魚羹、一碟子清炒瓠瓜。跟府里自然沒法比,但陸則也不是挑三揀四的人,有些菜,他只是不喜歡吃,并不是不能吃,畢竟只是用來果腹的。趁著用膳的時辰,陸則了常寧進來,問他,“方才你回去傳話,可還順利?”
常寧前陣子挨了罰,好險沒被世子厭棄,如今做事倒是得了訣竅了。世子最看重的,自是世子夫人,只要跟夫人有關的,他多長個心眼,準不會有錯。他也只琢磨了一下世子的話,便試著開口道,“倒是順利的。是惠媽媽出來聽的話,還賞了屬下一小袋煨板栗,說是夫人要吃,結果膳房送多了些,們又都煨了。”
常寧揣著顆心說了堆“廢話”,鼓起勇氣抬頭看世子的神,卻見他聽了后,不知想到什麼,竟笑了一下,顯然是心很愉悅。
自在宮門外被明安公主的人攔下,世子可一直冷著臉。可見還是夫人最頂用,雖沒面,但不過一袋煨板栗,都不值幾個銅板,也能世子高興。這本事,旁人大抵是怎麼也學不來的。
“東西呢?”陸則收起笑,看了眼常寧,叩指在桌上敲了敲。
常寧自然是沒敢吃的,拿出那藍布小袋來,遞過去。陸則接了,倒了幾個在手里,放得太久,已經冷了。阿芙倒確實這些,他每次回去,總能見跟惠娘幾個搗鼓些新鮮吃食。惠娘幾個也哄著,只要大夫說能吃,便二話不說想法子弄來。不過,雖吃這些,但一日三餐還是胃口很好的,他看了后,便也由著了。
陸則自己留了幾個,將剩下的丟給常寧,“既是賞你的,留著吧。”
常寧接住了,樂呵呵地道,“那屬下拿去跟兄弟們分一分。”
用過晚膳,時辰已經不早了,陸則將剩下的一氣做完了,已經快子時了。果然如齊直所言,夜里還有一場雨,且下得不小,院里秋后逐漸干涸的池塘,此時都積滿了小半的水了。看雨勢,大約也不會停。陸則便還是留在刑部歇了,他現在回去,又要驚阿芙睡得不好。
陸則不大在刑部宿,但還是給他留了專門的房間,每日有人收拾整理,還算整潔,只是秋雨綿綿,被褥有些許的氣。
陸則閉上眼,睡得很快。
窗外劃過一道閃電,劃破雨幕,雷聲轟隆,有半夜被驚醒的老人了眼睛,看了眼被吹得哐啷響的窗戶,起去關,就看見一陣電閃雷鳴,雷電擊中河邊的老柳樹,頓時起了一簇火,好在傾盆而下的雨水,很快澆滅了火苗,老爺子忍不住嘟囔。
“都十月了,怎麼還打雷啊?十月雷,閻王不得閑噢,可不是什麼好兆頭……”
……
陸則從一片混沌中睜開眼,暴雨傾盆,雨水如注,冰冷,幾乎得他睜不開眼睛。他下意識地揮出手里的刀,伴隨著一聲慘,穿著甲胄的士兵應聲倒下,濺了他一臉。
接著又是一刀,從脖子劈下,那人骨盡裂,只一層皮黏連著。
又是一刀……
他不知自己揮了多下,也不知有多人死在自己手里,只是很麻木地揮刀、斬敵。他沿著廡廊朝前,心里仿佛有什麼在催促他一樣,他越走越快,手里的刀也越砍越快,他幾乎沒有防的作,只是一味的進攻,上的傷口越來越多,堆在他腳下的尸首,也越來越多。
終于,他走到一宮宇。
很陌生,他很小就在宮里念書,按理說,他對宮中很悉,但這里,他卻只覺得很陌生,像是從未踏足過。庭院中荒草叢生,幾乎蓋過他的鞋面,陸則一步一步朝前走,覺得步子越來越重,越來越沉。
直到他手,推開那扇朱紅的大門,那門很沉很舊,像是年久失修一樣,朱紅的漆已經開始落了,螭銅環銹跡斑斑,沉重的嘎吱聲中,門打開了。
陸則忽覺得子一輕,腳下的步子也不再像先前那樣沉得他邁不開,他心中有個聲音,急切沙啞,一遍遍地催促他進去。他顧不得其他,被那聲音催得心慌不已,下意識邁了進去。
院子里也很陳舊,大抵很久無人居住了,石桌石凳胡倒在地上,屋檐下掛滿了蛛網,被疾風驟雨吹得一晃一晃的。
陸則的眼睛,下意識地凝聚在其中一扇門上,那是一扇很普通的格扇門,他手去推,卻仿佛一個踉蹌一般,踏了進去。
屋里很黑,大抵是沒人住的緣故,連燭火也沒有,暗沉得厲害。他站在那里,忽的聽見一個悉的聲音,很輕,他卻猛地一,快步朝聲音傳來的方向走去。
穿過一扇門,他竟看見了阿芙。
他的阿芙,躺在一張落滿了灰的床榻上,帳子上打著補丁,甚至還掛著蛛網。平躺在那里,渾都是的,頭發上不斷有雨水低落,臉慘白,眼睛閉著,烏黑的睫一不,除了無意識的□□,幾乎是失去意識的。瘦得厲害,幾乎到了令人看了覺得可憐的地步,除去那高高隆起的腹部,四肢皆瘦削,幾乎只是一層皮,裹著底下那層骨。
陸則看得心頭驚懼,下意識想要上前,卻被一無形的力量,牢牢束縛在原地,他看見惠娘從次間匆匆跑過來,他大聲喊,惠娘只是直直地穿過他,奔到床榻邊,哽咽著道,“娘子,奴婢尋不到更好的了,只有這個了。”
抖開臂彎那條毯子,盡可能地撣去那上面的灰,卻也是徒勞。哆嗦著,手卻穩穩地,將那毯子蓋在主子上。仿佛想盡力讓床榻上即將生產的主子,稍微暖和一點。
陸則看著這一幕,渾發,他已經知道這是夢了,但他依然沒辦法接,他的阿芙那麼的潔,他上帶了酒氣去抱,都要哄他去洗漱的。怎麼躺在這種地方,蓋著那樣一條破破爛爛的毯子,還懷著孩子,誰膽敢這樣怠慢?
誰敢這樣待……他要殺了那個人,他要殺了他!
殺了他!
陸則用盡全力氣,想掙開那束縛著他的力量,卻無論如何都只是徒勞,他看著阿芙睜開眼,緩緩手去握惠娘的手,聲音虛弱地幾乎聽不見,說,“惠娘,你幫幫我,幫我保下這孩子,幫幫我,好不好?”
惠娘哭著答應下來。
這里太簡陋了,什麼都沒有,縱使惠娘進進出出,翻箱倒柜,也只找到寥寥幾樣能用的東西。一燒了一半的蠟燭、一把銅制的繡花剪子、一塊疊起來的藍布……就只有這些。
哪怕陸則是男子,他也知道,婦人分娩時要什麼,開水、棉紗布,還有讓產婦恢復力氣的參片湯藥,大夫、產婆。從得知阿芙有孕起,他不止一次想過那一天,他肯定會守著,會有最好的大夫和產婆,會有最好的藥和補品,但實際上,這里什麼都沒有,連最基本的熱水都沒有。
他什麼都給不了,只能站在這里,眼睜睜地看著。
陸則生平第一次這麼痛恨自己的無能。
榻上的小娘子痛苦□□著,聲音從虛弱到沙啞,的手抓著床榻的邊沿,指甲在那梨花木上幾乎留下了深深的印子。窗戶被風猛地吹開了,但主仆倆一個無力,一個無心,誰都沒有去管那窗戶,任由冷風朝里灌。
猜你喜歡
-
完結1979 章

萌寶在上:邪魅王爺追妻忙
穿越成廢物如何?咱未婚先孕有個天才萌寶罩!不知道孩子他爹是誰又如何?咱母子聲名鵲起還怕冇人倒插門?萌寶:孃親,神獸給你牽來了!天材地寶給你搶來了!漂亮的男人給你帶來了!某女嫌棄:無錢無勢無實力,不要!某隻妖孽邪笑:錢財任你揮霍,大陸任你橫走,夠冇?母子兩人對視:美男在手,天下我有!成交!
177.5萬字8 130419 -
完結5533 章

冷王邪妃太逆天
救人一世,儘落個滿門抄斬,再世為人,她要逆天改命,毒禍天下!獲神劍,契神獸,修神訣,煉天下神器!欺我者亡!虐我者死!誅我全家之人,讓你連活都冇有可能!再活一世,就是這樣猖狂!他是世上最冷漠的九爺,戰場見到他的人,都已經死了,人送“活閻王”。本以為他是最無情的九王爺,卻變成了自己夜夜變狼的大師兄!“小師妹,我可以罩你一生!”“大師兄,我可以毒你全家!”“太好了!小師妹,我們一起雙修禍害全天下!”雙煞合併,天下誰人不抖!
363.3萬字8 119781 -
完結37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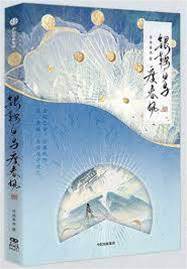
銀鞍白馬度春風
君主剛愎自用,昏庸無能,掩蓋在長安錦繡繁華之下的,是外戚當權,蟻蛀堤穴。 賢仁的太子備受猜忌,腐蠹之輩禍亂朝綱。身爲一國公主,受萬民奉養,亦可濟世救民,也當整頓朝綱。 世人只掃門前雪,我顧他人瓦上霜。這是一個公主奮鬥的故事,也是一羣少年奮鬥的故事。 ** 你該知道,她若掌皇權,與你便再無可能。 我知道。 你就不會,心有不甘嗎? 無妨,待我助她成一世功業,他日史書之上,我們的名字必相去不遠。如此,也算相守了。
55.4萬字8 187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