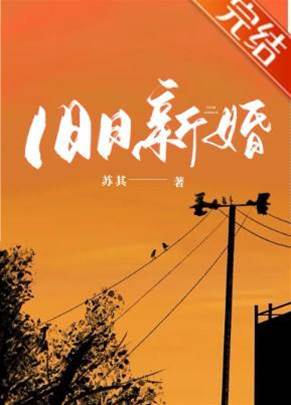《小情竇》 第16章 第十六章
沒人料到事會是這個走向。
在祁岸發飆的那刻, 幾乎所有人都屏息凝神地朝事發中心地去。
各目在周圍來回掃,掃得宋枝蒽一口飯都吃不下去,著筷子, 覺呼吸都滯幾分。
是樂樂義憤填膺又勇敢地起, 當著所有人的面, 斥責那個男生,“我知道我丑,不用你提醒, 但你又是什麼貨?”
“背后給班上生評十大丑的事你以為大家都不知道?”
“你這種人也就在學校能嘚瑟, 等到了社會你試試?看有沒有人收拾你!”
“而且我夸宋枝蒽漂亮怎麼了, 不過長了個胎記, 沒有那個胎記比學校任何生都漂亮, 你的評價算個屁!”
說這些話時,那個男生就呆若木地坐在那里,連都不敢轉。
剛剛一同嘲笑的其他幾個人也都面訕訕地低著頭, 抓耳撓腮,完全沒了剛才的嬉皮笑臉和作威作福。
唯一八風不的人是祁岸。
他始終保持剛剛那副姿態,面卻比之前冷上百倍千倍, 就這麼目不轉睛地盯著眼前的鄭威。
在樂樂怒氣沖天的指責后,他沉啞開腔,“去。”
“……”
“道歉。”
清清朗朗的幾個字, 如雨滴落在青石板, 又像甘霖潤澤燥郁干涸的心田。
眼眶那潤的一滴終究被宋枝蒽忍住, 抬起頭,看到鄭威遲鈍兩三秒后, 不不愿地站起。
五金椅和大理石底面出刺耳的滋嘎一聲。
他頂著一張如喪考妣的臉, 來到宋枝蒽和樂樂的飯桌前, 含糊著嗓音說了句對不起。
樂樂冷嗤一聲,一屁在旁邊坐下。
本以為這事就這麼息事寧人。
不料在鄭威轉離開的前一秒,宋枝蒽拿起旁邊裝著水的玻璃杯,毫無預兆地起,朝鄭威臉上潑去。
水是溫水,也本沒多。
可潑在臉上激起的恥心,完全不亞于一掌當眾扇在鄭威臉上。
那是宋枝蒽第一次當眾做這樣的反擊。
甚至連自己,都拿不準自己當時怎麼就腦子一熱,做出這樣的舉。
或許是后知后覺的恐懼心作祟,宋枝蒽拉起樂樂轉就走。
卻不知道,坐在斜前方朝這邊一直看著的祁岸,角勾起的一抹戲謔又玩味的笑。
就是那個晚上,洗過澡一沐浴香氣的祁岸再次來到閣樓。
年穿著寬大的白衛短,雙手抄兜閑閑進來,毫不客氣地霸占著宋枝蒽那張小小的舊轉椅,像那麼回事兒地告訴,得罪人了。
“鄭威那家伙很記仇。”
“你今天讓他當眾丟臉,小心他報復。”
最后幾個字被他抑揚頓挫得煞有介事。
說完祁岸吊起眼梢,由下至上地覷著,像在故意看什麼反應。
宋枝蒽輕抿著,默不作聲地站在桌旁收拾雜,好一會兒才開口,“那就讓他報復。”
說完像賭氣似的。
一轉,把書本文一腦放進書包里。
哪里還像平時那個糯糯的小綿羊。
祁岸角一扯,似是覺得新鮮,吊兒郎當地笑,“看不出來,還有骨氣。”
被他這麼諷刺,宋枝蒽作一頓。
十七八歲的嬰兒還未完全褪去,本就有些圓潤的兩頰這會兒更有些鼓,角略微耷著,目不轉睛地看著祁岸,還沒想好說什麼,就見年漫不經心地起。
修長如玉的手撐在桌面上,另只手習慣地抄著兜。
祁岸略微彎,一瞬不瞬地著宋枝蒽,調子慵懶輕佻,“怕了?”
“……”
被他上好聞的氣息侵襲到心跳加速,宋枝蒽下意識往后退了半步。
偏偏祁岸好整以暇,毫不退讓。
宋枝蒽被他目灼得不自在,不得已別開視線,出眼尾后如蝴蝶振翅飛的暗紅胎記。
祁岸盯著那塊胎記,目有很短的一瞬凝滯。
但很快,就恢復那副慵懶桀驁的模樣,語氣難掩凌厲鋒芒,“放心,有爺在。”
宋枝蒽抬眸看他。
年隨意倚著桌沿斜睨著,薄潤的邪邪一勾——
“我看誰敢欺負你。”
那時那刻的那番話,像年時不文的約定,不摻半點虛假意。
只是后來發生太多不可預測的事。
宋枝蒽還是渡過了一段非常難熬的高中時,祁岸也終究沒能為那個一直保護在邊的人。
-
大雨初霽。
翌日的北川市碧空如洗,惠風和暢。
昨夜宋枝蒽睡得不太安穩,又了風寒,臨近中午才醒。
這個時間,舅舅和舅媽都在家,屋里飄著香味四溢的飯菜香,勾得饞蟲作祟。
宋枝蒽本想繼續在床上賴會兒,手機卻不省心,像個電馬達似的不停震。
昨晚手機幾乎沒電,一直仍在桌上充著電沒管,后來睡過去,更是什麼都聽不到。
也是這會兒,才發現手機堆積了好多條短信以及未接電話。
其中大多數都來自同一個陌生號碼,打眼一看就知道是何愷。
見不接電話,何愷發了好多信息解釋昨天的事:
+:【枝蒽,我對天發誓,我是真不知道應雪給你發了信息,什麼時候拿我手機我都不知道】
+:【聚會我也不是不想帶你去,當時咱倆不是在冷戰嗎,我沒想好怎麼理,應雪從國外回來說沒意思,就磨著我非要我帶去】
+:【不過后來我也反省了,是我不對,我跟只是普通朋友,不能這麼越界,我當時也不應該為了保護面子,承認是我發的】
+:【枝蒽,對不起,真的對不起,是我不好讓你委屈】
+:【我真的知道錯了枝蒽,咱倆別分手行不行?】
宋枝蒽波瀾不驚地看著屏幕上這些俯首帖的短信,心里沒覺得半分爽快,只覺得很諷刺。
何愷似乎從來就沒搞懂,為什麼要和他分手。
并不是因為應雪,抑或是聚會這件事,而是從本上,他就沒有好好對待過這段。
而這種話,和他說再多也沒有用。
他總會嫻地找出各種理由周旋,再用富的口舌經驗打敗拙的宋枝蒽。
靜默須臾。
宋枝蒽到底什麼都沒回,熄滅屏幕把手機放到一邊,起下床出去洗漱。
收拾好出來時,午飯已經準備好,熱騰騰地擺滿一小張桌子。
舅媽和舅舅難得出門晚些,一家四口其樂融融地坐在一起吃飯。
趙淑梅生怕宋枝蒽吃不飽,一個勁兒地給夾菜,連帶著平時心大意的舅舅都跟著注意起來,“枝蒽這是怎麼了,怎麼覺臉這麼差。”
宋枝蒽筷子尖一頓,口而出,“昨晚淋了雨,有點不舒服。”
聽這麼說,楊春芝這才想起什麼,“哎”了聲撂下筷子,“你這要是不說,我都忘了——”
起快步走到廚房,不知搗鼓什麼,沒多久就端著一份剛用微波爐熱好的煎餃回來。
煎餃金燦燦的,上面灑了黑芝麻和蔥花,熱氣騰騰勾人食,是宋枝蒽從小到大最吃的食。
楊春芝特意放到宋枝蒽面前,“喏,你的。”
宋枝蒽愣住。
楊春芝揚了揚下,“就你那個朋友,上次給你捧場的男孩,昨晚又去我那兒吃燒烤了,帶著一堆小男生。”
舅舅接話,“就他們啊,一頓飯吃了一千多,不要命的點。”
趙淑梅笑起來,“我說呢,你們倆今天怎麼看起來這麼喜氣,原來昨晚上接了大單。”
楊春芝憨厚地笑,“哎呀,都是枝蒽的小同學給捧場,什麼貴點什麼,那酒后來都喝不完……哎,我還沒說完呢。”
看向宋枝蒽,“就他,昨天臨走前,讓我把冒藥和這份玉米鮮煎餃給你帶回去,說你晚上淋了雨,也沒怎麼吃東西。”
“藥就在電視柜底下放著,的塑料袋。”
“也怪我們回來太晚,你都睡了,就忘記跟你說。”
宋枝蒽猝不及防地怔住。
趙淑梅也意外起來,“什麼小同學,什麼來歷,怎麼這麼有錢,對你還這麼上心。”
楊春芝心直口快,“是對象的朋友——”
后面的話還沒來得及說,宋枝蒽就自己開了口,“是祁岸。”
趙淑梅神若有所悟那般,又有些微妙的訝然,“小岸啊。”
宋枝蒽輕嗯了聲,沒再答話,只顧低頭吃飯。
飯后,宋枝蒽照例陪楊春芝一起收拾碗筷。
楊春芝問,“你跟舅媽說實話,你是不是跟何愷鬧矛盾了?”
宋枝蒽洗碗的手一頓,神不大自在。
“你看看,我就說沒錯。”
楊春芝眼向來毒辣,“不然昨天那男孩也不至于那麼明目張膽的給你送東西。”
宋枝蒽用鋼球機械地挫著瓷碗,半猶半豫地打聽,“他昨天怎麼說的。”
猜你喜歡
-
連載1471 章
盛少,情深不晚
年輕幼稚的周沫被爸爸算計,稀裡糊塗睡了高冷男神盛南平,陰差陽錯生了兒子。 盛南平恨透周沫 三年後,為了救兒子,他必須和周沫再生一個孩子。 周沫是有些怕盛南平的,婚後,她發現盛南平更可怕。 “你,你要乾什麼?” “乾該乾的事兒,當年你費儘心機爬上我的床,為的不就是今天?” “……” 傳聞,京都財神爺盛南平是禁慾係男神,周沫表示,騙人滴! 終於熬到協議到期,周沫爆發:“我要離婚!我要翻身!” 但盛南平是什麼人,他能把你寵上天,也能殺你不眨眼......
357.7萬字8 15379 -
完結1203 章

五年後,龍鳳雙寶攜她炸了大佬集團
夏梵音被繼妹陷害懷孕,被迫假死逃出國。 五年後,她帶著萌寶們回國複仇,竟意外收穫了個模範老公。 安城裡的人都知道紀三爺性情殘暴冷血,可卻日日苦纏全城知名的“狐貍精”。 夏梵音掙紮:“三爺,麻煩你自重!” 紀爵寒抱起龍鳳胎:“孩子都生了,你說什麼自重?”
214萬字8.18 86711 -
完結17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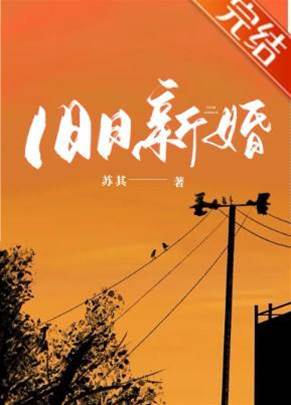
立冬/舊日新婚
秦南山是聞依最不喜歡的男人類型之一,刻板嚴肅,沒有喜好,沒有激情,像密林深處一潭死水,石頭扔進去,波瀾不驚。 一夜混亂,聞依更新認知,不全無可取之處。 一個月後,聞依看着試紙上兩道鮮明的紅槓,陷入沉思。 從懂事起,她從未想過結婚生子。 - 秦南山二十八歲,A大數學系副教授,完美主義,討厭意外,包括數學公式和人生。 聞依找上門時他一夜沒睡,逼着自己接受這個意外。 領證、辦婚禮、同居,他們被迫進入一段婚姻。 某個冬日深夜,聞依忽然想吃點酸的,換好衣服準備出門。 客廳裏穿着整齊加班的秦南山看向玄關被她踢亂的鞋子,眉心緊擰,耐着性子問:“去哪?” “想吃酸的。” “非吃不可?” “嗯。” 男人垂眸看錶,十二點零七分。 他心底輕嘆一聲,站起來,無奈道:“我去給你買。”
31萬字8.18 19274 -
連載959 章

賀總夫人又來蹭氣運了
姜糖天生缺錢命,被師父哄下山找有緣人。 本以為是個騙局,沒想到一下山就遇到了個金大腿,站他旁邊功德就蹭蹭漲,拉一下手功德翻倍,能花的錢也越來越多,姜糖立馬決定,賴上他不走了! 眾人發現,冷漠無情的賀三爺身邊忽然出現了一個軟乎乎的小姑娘,會算命畫符看風水,最重要的是,總是對賀三爺動手動腳,誰不知道賀三爺不近女色啊,正當眾人等著她手被折斷的時候,卻見賀三爺溫柔地牽住她的手。 “嫁給我,讓你蹭一輩子氣運。”
174.2萬字8.18 12962 -
連載317 章

避孕失敗!沈小姐帶崽獨美,厲總慌了
十年深愛,四年婚姻,沈瀟瀟畫地為牢,將自己困死其中,哪怕他恨她,她也甘之如飴。直到一場綁架案中,他在白月光和懷孕的她之間選擇放棄她,間接害得父親離世。她終於心死,起訴離婚,遠走國外。三年後再見,她攜夫帶子歸國。厲行淵將她困在身下,“沈瀟瀟,誰準你嫁給別人的?”沈瀟瀟嬌笑,“厲先生,一個合格的前夫應該像死了一樣,嗯?”男人眼眶猩紅,嗓音顫抖,“瀟瀟,我錯了,求你,你再看看我……”
53.8萬字8.18 5010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