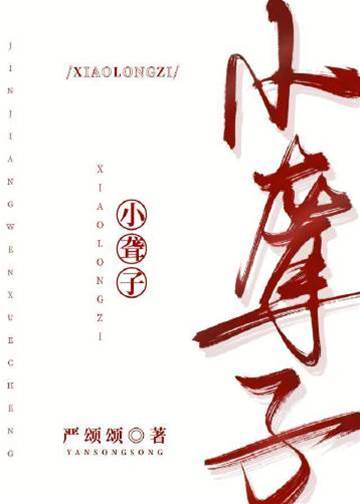《夢河夜航》 第55章 第 55 章
這些人不論男,居然都在問聞雪時,在干嘛,睡了嗎。
婁語無語。
他仿佛察覺到異樣的沉默,直接道:“你在意的話就問,不要憋著。”
:“倒也沒有……”
畢竟的微信也經常有人噓寒問暖,那麼聞雪時也不可能無人問津,招蜂引蝶程度和不相上下。
但還是不爽。
他平淡道:“都是圈人,我不方便刪,但我也不會搭理。但如果你想讓我刪掉他們的話我也無所謂。就說被盜號了。”
“……虧你想得出來。”被他逗笑,點開丁文山的消息,念出來,“他在問你明天晚上的線上采訪提綱你確認沒有,你看了嗎?”
“你直接跟他回說我睡了吧。”
“好。”
按照他剛才的話潤了下回復過去:我準備睡了,有事明天再說
收到消息的丁文山卻眉頭一皺。
怎麼回事,居然沒打句號……
嘶,事好像有點不對勁。
婁語還沒察覺到自己有點出馬腳,下意識點退微信準備鎖屏把手機放回,手指不經意往右一,iphone自帶的照片回憶冷不丁顯現。
看見那張照片,完全愣住。
——金碧輝煌的頒獎大廳,黑的座位,高筑的舞臺,穿著拖地黑的人站在其中,眼含熱淚,
手里攥著沉甸的視后獎杯。
那是三年前登頂的那一刻。
照片上沒有任何工作室或者的水印,是用手機親自拍的。
就在這時,明明已經停滯的歌曲在三分鐘之后,居然再度響起歌聲——
這才意識到,這首歌本不止三分鐘,剛才的停頓也并不是結束,而是歌曲的留白。
它狡猾地留白,漫長到讓人以為不會再有后續時,突然毫無征兆地響起了空靈的聲唱,曲風截然不同,像遙遠的唱詩班在慶賀新生。
它恰好響在手的瞬間,兩種不同程度的震撼敲擊著的耳和心臟,以致于不自地渾戰栗,怔怔地側過頭去看聞雪時。被手機背叛的主人還毫無所覺,看著路段前方,注意到的視線,笑著瞥一眼,騰出手的耳朵。
“怎麼了,困了?”
聲音得像一片云。
的心臟被這片薄云絞殺,掩飾地把手機摁滅,故作平靜地放回扶手盒。
“我知道你為什麼喜歡這首歌了。”無所適從地調整著表,“因為這三分鐘的留白對不對。”
他點頭,輕描淡寫地說:“在這首歌里能聽到希。”
無論是對于人生,對于夢想,還是對于他們之間的,似乎都在唱著絕逢生的可能。
這五年來,他每次覺得自己快沒辦法支撐下去的時候,這首歌某種程度上像是一粒藥片,告訴他現在所經歷的只是留白,而不是終點。
終點的盡頭,是婁語。
如果從前有人對他說,一個人的存在會那麼重要,他一定會嗤笑。
很多年前,那會兒還是大學的時候,老師教表演課,回去讓他們多看經典影片,多學習演員的表演方法,重要的還是會故事背后的人生哲學。只有真正懂了人世故,才能真正詮釋出好的作品。
他便經常在打工完后的深夜專門繞遠路去錄像店租碟來看。大城市如今那樣的店鋪已經很了,他找了很久才找到的一家,開到凌晨兩點,坐夜8路從他打工的地點開始七站,再坐夜26路經過漫長的43分鐘到達學校。
宿舍常常很空,一個常年拍戲,一個本不住校,還有一個混跡夜店,這個點正是最high的時候,如果釣到妹,整夜都不會回宿舍。
比起舍友們富多彩的娛樂活,獨自坐長長的夜路公去租碟就是他唯一的樂趣了。他總是喜歡看窗外,路上會經過一條河。他怕看見河,尤其是夜下的河。但他總是會不由自主地盯著它瞧,腦子里想的是父親那一晚看見的河面,是不是也和他一樣。
那確實無聊的,無聊得讓人想要慢慢走進去。
這個念頭一出來,他看見車窗上映出的影子在笑,他盯了他一會兒,才意識到,哦,原來這個在笑的人是我自己。
晴好的夜晚,會有在河邊接吻散步,也會有三兩個中年人結伴在這里夜釣,大多數時候,那條河邊的路還是空的,只有蚊蠅在路燈下飛,清白的燈和月混在一起,分不清哪種白看上去更寂寞一些。
又或者只是他的眼睛看什麼都寂寞。
電影是唯一看上去能讓他覺不太寂寞的東西。里面有各種各樣的死亡,也有各種各樣的,雖然他也并不是完全明白,但他看完一場電影,就會在和死里穿梭一遍,那種覺很好。不過大多數時候他只能很痛徹地明白死亡,不太能明白。
他還記得有個晚上他在宿舍里看了通宵的電影,主要是打工完到宿舍都凌晨兩點了,而那部電影有四個小時,《國往事》。
他便看看
看,一直往下看,沒剎住。
天邊曙出時,自己了滿地煙頭,只有他一人的宿舍煙霧繚繞。他吸著自己制造出來的二手煙,嚨很,腦海中反復滾著某段臺詞——
「當我對世事厭倦的時候,我就會想到你。
想到你在世界的某個地方生活著,存在著,
我就愿意忍這一切。
你的存在對我來說,很重要。」
當時的他念著這段臺詞,仰頭輕笑著向空中吐出一層煙圈。
而若干年后的現在,他終于知道,這世界上的確是有這麼一個人的。以致于想到,無論是看燈還是月,無論是不是再獨自路過那條夜河,都好像不會再寂寞了。
車子終于駛進市區,駛進他們悉的街道,七拐八拐,停在了小區的偏僻一角。為了安全起見,婁語先下了車,再過幾分鐘,聞雪時才下,兩人一前一后上樓。
婁語轉開大門,沒開燈,黑漆漆地踏進這間房子。
自從把手單在那張海報之后,這間房子就像被蓋了黃土的棺木,再也沒來過。站在空的客廳中央,總覺得像是上輩子的事。
后突然傳來輕輕的開門關門聲,接著有人把燈打開了。
婁語回過頭,看著后的聞雪時,收起緒,對他笑笑。
“你看,我都和你說了,這里面空空的,沒什麼好看。”
他環視了一圈,最后落在上。
“最重要的已經在這兒了。”他說。
他頭頂懸掛著陳舊的鎢燈,泛著低瓦數的黃,他站在下,整個人被昏黃浸染著,就好像是多年前他站在便利店的櫥窗外頭,路燈的昏黃染著他一樣。
怔怔地看著他,說:“是的,在這里了。”
“怎麼表呆呆的。”聞雪時走過來笑著掐了把的臉,隨即往唯一的臥室走去,邊念叨,“想看看那張海報的,現在都看不到實了。”
婁語跟在他后進屋,海報之前被用手單蓋上,之前被丁文山摘下來,現在又暴出來,泛黃地掛在那兒,從門口去,就像是一間老式錄像廳的址。
聞雪時走到海報跟前,手了上面的兩個背影。
“你們好。”
他笑著和海報上的他們打招呼。
他話音剛落,就聽到后傳來手機快門的咔嚓聲。
“怎麼突然拍我?”他回過頭,婁語揮了揮手機,回答他:“禮尚往來。”
“禮尚往來?”
“以前你也拍過我和海報的合影不是嗎?”
他一愣神,反應過來:“啊,你說首映那天?”
“對,就是我們把這張海報從電影院帶回來那天。”
他了鼻子:“……你怎麼知道的?”
“我看到了你的微博小號……”婁語有些好笑地說,“你那個號的頭像就是我做的表包,我認不出來才怪,所以不小心看到了你的微博……順便看見你發了一條這張照片的相關微博。”
——「你永遠是我無人知曉的主角」
是在當時,特別震撼的一條微博。
婁語故作輕松地聳聳肩:“雖然我知道它現在已經被刪啦。”
聞雪時沉默片刻,忽然對說:“給你看看我換的新頭像。”
他把手機遞過來,微博的賬號頭像頁上依然是一只熊貓。
只不過不再是制作的表包了,而是一張網圖,熊貓胖墩墩的黑白背影,置
在一片雪地中。
被雪包圍的大熊貓。
婁語嘟囔:“……犯規啊,換這麼可的頭像。”
他道:“嗯,都是我們小樓喜歡的,熊貓,還有雪。包括名字里帶雪的男人。”
語氣卻一本正經,十足自信又臭屁。
角忍不住翹起,掩飾地沖他翻個白眼,想把手機遞還給他,他卻沒接。
猜你喜歡
-
完結47 章

離婚成為富婆后
影視頂流顧宣烈,劍眉星目,矜貴高冷。 身為顧氏企業的大少,是粉絲們嘴里不努力就得回家繼承家業的“人間富貴花”。 他從不與人傳緋聞,對外宣稱不婚主義。 但心底埋藏一個不為人知的秘密—— 他想要的女人,是別人的老婆。 才剛離婚,季開開頂著亞姐的頭銜重回娛樂圈,上綜藝,演電視,錢多人美,一炮而紅。 娛記樂于報道她的豪車上,又載了哪個小鮮肉來博取新聞版面。 黑粉群嘲:不過是拿錢泡“真愛”,坐等富婆人財兩空。 后來,眼尖的粉絲發現,從季開開車上下來的是娛樂圈的頂流影帝顧宣烈! 認為她一定會后悔的前夫:“……” 嗯?不對!一定是哪里出了問題。 前夫緊急公關,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太太有些頑皮,過幾天就會回家!” 一天后,影帝曬出八億的藍鉆戒指和一張幼時的合影,[顧太,快來認領我!] 他想要的女人,這次一定得是他的。 **雙C卯足了力氣開屏吸引人的影帝VS我只喜歡你的臉真的不想再結婚的小富婆
13.3萬字8.33 7588 -
完結7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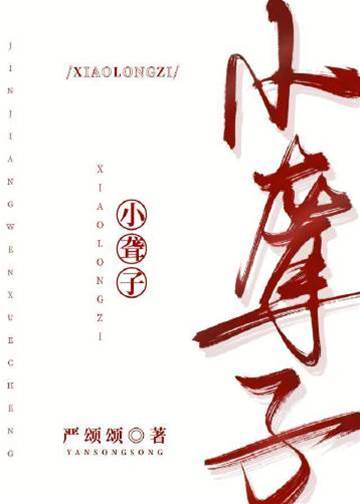
小聾子受決定擺爛任寵
憑一己之力把狗血虐文走成瑪麗蘇甜寵的霸總攻X聽不見就當沒發生活一天算一天小聾子受紀阮穿進一本古早狗血虐文里,成了和攻協議結婚被虐身虐心八百遍的小可憐受。他檢查了下自己——聽障,體弱多病,還無家可歸。很好,紀阮靠回病床,不舒服,躺會兒再說。一…
30萬字8.18 17628 -
完結207 章

不浪漫罪名
簡介: 周一總是很怕陸聿。他強勢霸道,還要夜夜與她縱歡。他貪戀她的柔軟,想要她的愛。世人都以為他在這段感情裏占據了絕對的主動權。可他說:“一一,我才是你卑微的囚徒。”~也許,你我都應該認下這從一開始就不浪漫罪名。
33.3萬字8.25 762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