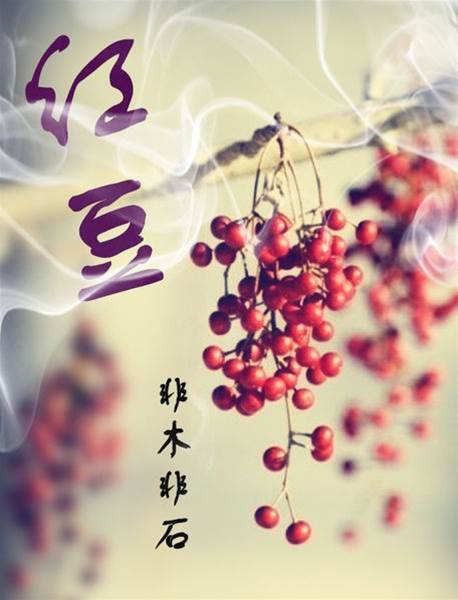《七十年代漂亮女配》 第94章 第094章
于是阮紅兵接上道:“就是,稚鬼!”
阮溪在旁邊笑。
本來阮溪還想帶他們去北海公園劃個船,但是因為時間不夠,所以就沒有去。在傍晚時間差不多的時候,帶著阮紅軍他們去到了教育局。
阮潔下班從大門里出來,看到他們還驚喜了一下。
阮溪對說:“走吧,我們來接你下班,今晚去你家蹭飯,去你家睡。”
阮潔笑起來道:“好啊,走,我們去買菜。”
既然不打算去外面飯館吃,于是五個人三輛自行車,先去副食店買,買好又去菜場買菜,然后拎著大包小包的東西回家做飯。
阮潔住在一個小區的樓房里,是單位分的房子,三室一廳。這年代住在這種小區的樓房里,可比住平房有面子且舒服多了。有這樣一套房子,能人羨慕死。
比起周老太太的四合院,阮紅軍三個人果然也更喜歡阮潔的這個房子。
阮秋月還說:“大姐你要是不辭職,結了婚也能分到這樣的房子。”
現在還沒有商品房這個東西,房子都靠單位分。
阮溪笑著說:“我更喜歡住平房。”
阮溪和阮潔去廚房里做飯,讓阮紅軍三個人在客廳自己玩。阮潔和陳衛東還買了電視機,三個人便在外面津津有味地看起電視來了。
阮潔知道阮溪一直想買城里的房子,而城里也就只有四合院的平房好買,剛才提到平房,便跟阮溪說:“陳衛東最近有點忙,等他閑下來讓他幫你找。”
阮溪笑笑道:“我自己找到了一套。”
阮潔站在灶臺邊摘芹菜,看阮溪一眼,“真的啊?好買嗎?要多錢啊?”
阮溪拿著刀切土豆:“我一個老顧客的房子,常給做服的,要出國去養老,剛好兒子需要用錢,所以就想賣房子,說是一萬二。”
阮潔想了想,“差不多就這價。”
阮溪道:“等陳衛東不忙了,你讓他繼續幫我看一看,最好是能再找兩套,到時候讓三姑他們都搬到城里來住,也不能一直住在鄉下,學校不好。”
阮潔點點頭,“行,我他幫你看著。”
兩個人在廚房里聊著天做飯,做好飯阮紅軍三個人洗手吃飯。
關了電視洗完手過來吃飯的時候,阮秋月問:“不等姐夫回來一起吃嗎?”
阮潔道:“他今晚值班住單位,不回來。”
阮秋月點點頭,“哦。”
于是他們便沒再管陳衛東,五個人坐下來吃飯,吃完飯又看電視吃水果嗑瓜子聊了會天,挨個洗完澡回到房間里睡覺。
雖然家里的房間夠,但阮潔還是把阮溪和阮秋月到了一起住。難得姐妹三人聚到一起,昨天晚上沒能好好說話,今天當然要睡在一起好好聊天。
于是三個人又聊到夜深才睡覺。
雖然睡得晚,但早上三個人也都很早就起來了。阮潔去上班,阮溪帶著阮紅軍三個人又去北海公園玩了半天,劃船吹湖風,中午仍然是下館子。
吃完午飯四個人找地方休息了一會,然后在差不多的時間去了教育部禮堂。
憑票進場后,發現禮堂里已經坐了很多人,當然基本都是十六七歲的中學生。前面位置被坐滿了,阮溪便帶著阮紅軍他們坐在了后面。
反正禮堂的椅子都是一排高過一排的,前后又都有喇叭,坐前面還是后面都不影響,該看到的都能看到,該聽到的也都能聽到。
中午吃飽飯了,午后天氣又熱得很,而且昨晚熬到夜深才睡,所以阮溪坐下來后沒多一會就覺眼皮有些發重,開始打哈欠想要睡覺。
雖然困,雖然這講座也不是為這種年齡的人準備的,但是來都來了,自然還是要看一看最高研究院里那些院士的風采的,所以就強打著神。
強打著神等到講座開始,主持人上臺說完開場白以后,邀請了一個鬢角花白的院士上臺開始發言。
阮溪靠在椅背上,撐著眼皮聽。
院士在講宇宙講星星,講黑白蟲這些東西,其實還有意思的,但阮溪還是越聽越困。抬手擋住打了幾遍哈欠,實在沒撐住,靠著椅背睡了過去。
阮秋月坐在旁邊聽得專注,倒是一點瞌睡都沒打。
阮溪睡著睡著,那腦袋就落下來靠阮秋月的肩膀上去了。
阮秋月轉頭看向笑笑,任靠著自己的肩膀繼續睡,而自己繼續認真聽講座。
這些院士講的東西都喜歡,越聽越有意思,一邊聽一邊覺自己已經置在宇宙,已經完暢游在絕的科學規律之中了。
然后臺上忽上來一個年輕的發言人,禮堂里瞬間起了一點小。
阮秋月能明白這種小的來源,因為這個年輕人長得很好看,而且不止是長得好看,主持人介紹的時候,頭銜也還多的,年紀輕輕居然有不研究果。
雖然都聽不太懂,但是一聽就是很厲害的人。
剛才上臺發言的都是爺爺輩的人,現在突然上來一個二十多歲的,長得好看又有這些高端頭銜加持,尤其是禮堂里的孩子們,不起點小才不正常。
大家都是青春活潑的年紀,這些反應純屬正常。
阮秋月因為自己旁邊沒有坐生,阮溪又睡著了,所以沒有人流兩句。
阮紅軍和阮紅兵甚至不明白這突然的小是怎麼回事,所以轉頭問阮秋月:“怎麼了?這個比之前的兩個都厲害?”
阮秋月笑一下,“那倒沒有,前兩個都是院士。”
能評選上院士那最小也得四五十歲,這年輕人二十多歲肯定不是院士。
阮紅軍和阮紅兵疑了一下,臺上的人開始發言,他們便認真聽講沒再說話了。
阮秋月骨架小人又瘦,阮溪靠在肩膀上睡得并不舒服。硌得腦袋瓜子疼,便在迷迷糊糊中抬起頭來,又靠回椅背上睡去了。
剛又沉夢中,忽有人在旁邊搖肩膀。
被搖得醒過來,驚得睜開眼,只見阮潔不知道什麼時候來了,就坐在旁邊的空座位上。還知道自己在哪里,于是小聲問了句:“怎麼了?”
阮潔指指臺上發言的人,小聲問道:“那是凌爻嗎?”
聽到這話,阮溪又清醒了幾分,轉頭看向臺上的發言人。看到的瞬間愣了一下,眨眨眼之后看向阮潔,又轉頭往臺上的發言人看過去。
阮潔再次小聲問:“是不是啊?”
阮溪轉過頭看向阮潔,說話還帶著點鼻音,著聲音道:“不是你們單位搞的活嗎?邀請了哪些人過來,你不知道,你來問我啊?”
阮潔小聲道:“不是我負責的,我哪知道啊,我就是個小嘍啰。我忙完手里的活跑過來的,來了就看到這個在臺上發言,我覺得有點像他,但是又覺得好像不是。”
阮溪聽完阮潔的話,又把目轉去臺上。
阮潔說的沒錯,這個人長得像凌爻,但是給的覺又好像不是。凌爻一臉氣,而這個年輕人面部和五廓都清晰很多,整張臉更加俊秀朗一些。
最重要的,說話談吐以及眼神氣質,一點都不像。
阮潔又在旁邊問:“你覺得是嗎?”
阮溪搖搖頭,“不知道。”
為了確認,又轉頭看向阮秋月,小聲問:“這位發言的老師,什麼啊?”
阮秋月想了一下,“沒注意聽。”
剛才全關注,還有這個老師的那張臉去了。
阮溪又往阮潔那邊靠過去,看著臺上的年輕人小聲說:“應該不是吧。”
阮潔又仔細看了一會,也說:“乍看覺得像,仔細看看確實覺應該不是他。”
畢竟人家在發言,學生們聽得認真,倆說到這便沒再說話了。
當然阮溪睡了一覺也沒有困意了,便坐在椅子上看著臺上的年輕人說話。因為沒有從頭開始聽,講了什麼都不知道,盯著他那張臉看了。
這個年輕人發言結束,這個講座也就結束了。
主持人說完結束語,禮堂里的學生也就慢慢站起來開始散了。
阮溪和阮潔一起站起來,問:“一起走嗎?”
阮潔道:“走啊,我還得回去上班呢。”
說完兩個人便跟在阮紅軍他們后出座位,直接從禮堂后門出去了。
禮堂座位的第一排,最后發言的那個年輕人和兩個院士起。他站著和其中一個院士說了兩句話,轉頭的空隙忽看到后排站著兩個悉的面孔。
他晃了一下神把目聚焦到左邊那個人的臉上,看著站著和右邊的人說了兩句話,然后跟在三個學生后出座位,從禮堂的后門出去。
院士看他說著話突然走神,好奇往后排看了一眼,問他:“怎麼了?”
年輕人回過神來,繃神眨兩下眼,忙對院士說:“褚老師,我有點事出去一下。”
禮堂里學生多走不過去,他自然沒有往后排去,而是直接從前門跟學生出去。出去后他繃著面到張,但并沒有看到剛才在禮堂后排看到的人。
心跳堵在嗓子眼里,心臟幾乎要從腔里蹦出來。
片刻后他又回頭進禮堂,上臺直接拿起話筒打開喊:“阮溪!我是凌爻!”
“溪溪!我是凌爻!”
“我是崽崽!”
阮溪和阮潔剛出禮堂走過拐角,正要加快步子的時候,忽聽到禮堂里的喇叭中傳出自己的名字。聽到聲音的瞬間,和阮潔同時愣住停住了步子。
好片刻,阮潔說:“是凌爻,他在你。”
阮溪回過神,和阮潔一起轉回去,剛從拐角轉出去,便見凌爻從禮堂的大門里急急出來了。他出來后四張,轉向這邊的時候,剛好和阮溪的目上。
兩個人隔了二十多米的距離看到彼此,瞬間整個世界都安靜下來了。
猜你喜歡
-
完結443 章
寵婚似火:嬌妻,好孕到!
黎淺是江城所有女人艷羨的對象,也是所有女人最不屑的存在。 她有著最艷麗精緻的容貌,卻是個作風豪放、人人不齒的私生女。 一場精心的設計,一次意亂情迷的放縱,一個多月後黎淺拿著妊娠四十天的檢查單與陸天擎在醫院
109.6萬字8 24711 -
完結12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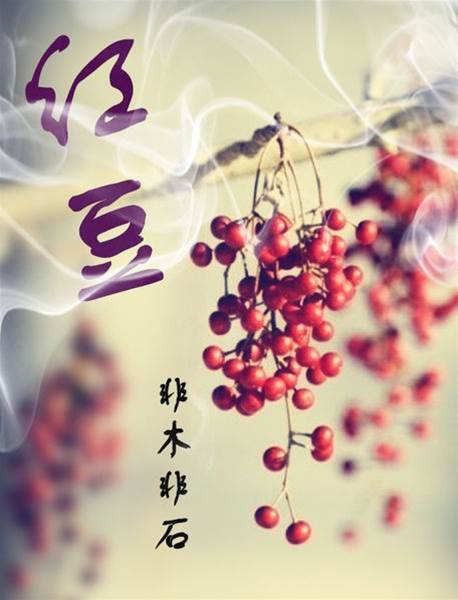
紅豆
他捏著手機慢慢把玩,似笑非笑說:“看,你守著我落兩滴淚,我心疼了,什麼不能給你?”
30.6萬字8 7305 -
完結179 章

嫁給財閥掌舵人後,頂奢戴到手軟
別名:前夫出軌以後,我睡了他兄弟【甜寵 追妻火葬場 直接把骨灰揚了 男二上位 潔 雙處】【排雷:前期女主商業聯姻結過婚,但有名無實】阮嫆跟淩也結婚兩年,淩也提出離婚時,她毫不猶豫答應。手握巨額財產,從此她放飛自我。阮家就她一個獨苗,需要傳宗接代?簡單,“幫我發一則重金求子消息。”就寫,“因丈夫車禍無法身孕,求一健康男性共孕,重金酬謝。”至於要求,“要帥,身材巨好,國外常青藤名校畢業,活兒好,價錢好商量。”她重金挖來的私人助理效率極高,第二天就將應聘者照片發來。完全符合她的要求,且超出預期,就是照片裏矜貴清冷的側影,有點眼熟。她立馬拍板,“就他了。”“這邊隨時可以安排,但對方有個條件。”阮嫆挑眉,“什麼條件?”“他比較害羞,要關燈。”後來她才知道她惹上什麼樣的麻煩,這人不光是千億奢侈品集團慕家獨子,還是她前夫最好的兄弟。——淩也沒有像往常等來阮嫆複合,而是她另有新歡的消息。他忍著心頭絕望窒息,對人道,“離了她老子還不活了,不許勸。”後來半夜酒醉打電話過去。“嫆嫆……”聲音微澀。另頭傳來一道男聲,清冷平靜,“請問半夜找我老婆有事嗎?”“……”
31.5萬字8 1539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