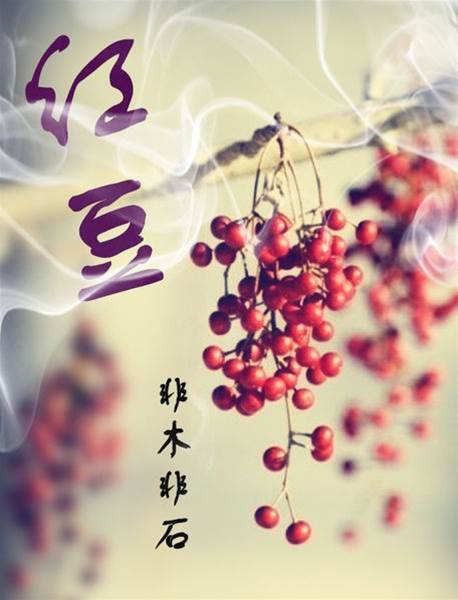《晨昏游戲》 第60章 第60章
落地窗外面是深沉難辨的夜,恰好映上郁承漆黑幽邃的眸,他近兩步,把抵在高腳凳旁,垂斂著眼盯著。
像是獵人看獵的眼神,十足侵略,饒是懷歆也不自覺做了個吞咽的作,下意識地想移開視線。
“你……”
瞠大黑眸迎著他,飛速轉腦子想講點什麼話:“你和付先生是怎麼認識的?”
一個不太高明的話題轉移,郁承居高臨下地看了片刻,還是縱容地收斂了氣息。
他低下眸子,回答:“我們原先一同在香港念初中。”
付庭宥和郁承是因馬球課結緣的。他轉學過去的那所貴族學校,潘雋令人排打他,導致了那次墜馬事件,是付庭宥當即遣人送他去的醫院,事后也站出來為他說話,這讓郁承在學校里的境不再那麼艱難。
懷歆倒是第一次聽聞此事,憤怒地瞠圓眼睛,著聲音道:“他們怎麼可以這樣!也太過分了!”
郁承意外于的聲討,怔了一下,很快勾著眼尾笑起來。
“都過去多久的事了。”
男人語氣無謂,了的腦袋,以示安,“我早就不在意了。”
懷歆卻還是顰著眉,張地看著他:“你當時傷到哪里了?”
圓漉漉的眼睛蘊著淺,像是有些潤,郁承對上眼睛,嗓音有些低沉:“比較嚴重的一是左手手臂,碎骨折。”
“留疤了嗎?”
懷歆問完就知道這話有點多余了,于是換了個說法:“我可以看看嗎?”
郁承撐著臺面靠近一些,深暗眸下來,掌心在肩頭挲。
“要服。”他的話讓的心輕微提起,懷歆張了張,見郁承笑了下,淡道,“回去給你看。”
懷歆線平直,沒再說話。
郁承靜靜凝視須臾,替將耳邊碎發挽到后面,溫地問:“吃飽了麼。”
懷歆低低嗯了聲。
他便垂下眸道:“我這邊還有點事,你先回房間去。”
抬睫,抿看著他,郁承嘆口氣,解釋道:“在這邊我會分神,可能顧不好你。”
道理是這麼個道理。懷歆無端有些累了,拉長語調應了一聲:“好吧,我這就回去。”
郁承在走之前叮囑道:“上去之后給我發個信息。”
“嗯。”
他眸沉靜地目送墨綠的窈窕影消失在拐角,肩膀突然被人攬了一下:“在這里啊,到找你。”
是付庭宥。
他順著郁承視線看過去,了然一笑:“送走你小友了?”
郁承不置可否,神散漫地看向他:“同他們都聊完了?”
“都打發走了。”付庭宥坐下來,注意力被臺面上的高腳杯吸引了去,葉鴻的名片倒在其中浸染酒漬,簡直可憐兮兮的。
他瞧了一會兒,樂了,向郁承求證:“是做的?”
郁承沒回話,付庭宥便嘖嘖稱道:“有意思的小姑娘,怪不得你喜歡了。”
郁承神不明地抬了下眉,出聲匡正:“可只說了是我的伴。”
“是,我一開始也以為沒什麼特別呢。”付庭宥意味深長地說,“后來瞧見你們之間的互,才知道不一樣。”
郁承淡淡勾了下,算是承認了這話。
“是我我也喜歡這種的。”
付庭宥笑笑,片晌好似想到什麼,嘆了聲,“可惜遇到了我們這樣的人,會吃苦頭的。”
郁承知道他在說什麼,招來侍者要了一瓶威士忌。
玻璃杯中斟滿了酒,氣泡上涌,兩人杯對飲。
付庭宥的胞弟付庭胥和初友便是如此,家族強制聯姻,拆散了這對苦命鴛鴦,友因不能接人與別人結婚而自殺,付庭胥則患上抑郁癥,終日郁郁寡歡。
郁承低垂睫羽:“所以你知道我為什麼一直不愿意回潘家了麼。”
他想要自由。
“合理。”付庭宥喝了一口酒,問郁承,“那你現在為什麼又要回去?”
因為他意識到逃避不能真正解決問題。
只有變得強大,才能保護自己所在乎的一切。
付庭宥從郁承的眼神中讀懂了他的想法,他沉默下來,好久才說:“阿承,這條路并不好走。”
又想要自由又想要權柄,世上哪有這麼容易的事。
“我知道。”郁承頷首,平靜地說,“置之死地而后生。總要去試試。”
許琮可以遣人為侯素馨換藥,日后也可以作手段毀了懷歆的前途。只要郁承有肋,這便是一個死局。
侯素馨的事只是一個引子,郁承卻可以通過它預見將來。
他拼盡全力也許能夠保住郁家夫婦,可假以時日若天平這端再多了誰,郁承沒有十足把握護所有人周全。
但是他知道自己貪心,想要的很多,既割舍不下,便只有全力一搏。
付庭宥知道他心意已決,沒再說什麼,只是與他了杯,寬道:“大好日子,不說這些了。”
懷歆剛給他發了信息,說回到房間了,郁承收起手機,重新為付庭宥滿上了酒,后者道:“這里的人也基本上都介紹與你認識了。來香港記得找我,我帶人和你吃飯。”
“好。”郁承拍拍他的肩膀,“你有什麼事也同我講。”
“那是自然。”
付庭宥回憶起上學時發生的事,樁樁件件猶在眼前,他不住嘆道:“一晃眼十幾年了。”
時間是最不仁慈的東西,但卻能夠讓很多事變得雋永深刻。
比如兩肋刀、肝膽相照的義,任歲月再怎麼磋磨,還是一如往昔。
一瓶威士忌所剩無幾,兩人都有了些醉意,這時郁承擱在一旁的手機震,是懷歆來電。
付庭宥瞥了一眼,了然似的笑:“人家等急了,趕回去吧,明天再聊。”頓了下,“葉鴻那小子我替你教訓他。”
郁承似笑非笑地輕哼了聲,起與他作別,邊往回走邊接電話,聽到懷歆在那頭小聲詢問他什麼時候回來。
有些委屈的聲調,也許是故意,小貓似的撓人心。
“現在。”郁承嗓音低磁,紅酒一般的醇郁,“在房間里乖乖等著我。”
從宴會廳到酒店房間的路比較長,中間還要經過熱鬧的賭場,形形的男相擁著注,頹靡而奢華的金錢氣息泛濫,郁承屈肘系好西裝紐扣,面冷淡地穿過這片鬧區。
在等待電梯樓層逐漸上升的過程中,郁承不由得想到樓上那只小貓。
不知道現在在做什麼?簡直沒一刻安分。
他知道自己今晚喝醉了,溫比平常更高一點,有些燥熱。郁承閉上眼,按了按太。
沒有用太久時間就走到了行政套房門口,已近凌晨一點,遠離了地面上的喧囂,周圍很是安靜,郁承本想抬手敲敲門,最終還是掏出了房卡刷開門閘。
與他想象中不同,室昏昧一片,靜得連一針落下都能聽見。
臥室出些許線,郁承了外裳隨意搭在一,視野有點恍惚,他步伐緩慢地往里間走去。
待看清床上的景之后,男人腳步頓住。
——懷歆穿著一條淡紫的綢睡,趴在離門口稍遠的那一側睡著了。
的床頭開著一盞橘黃的臺燈,線不亮,剛剛好把姣好的廓勾勒出來。
懷歆側著頭,白皙的臉頰對著他,順的烏發鋪陳在的枕上,卷翹的眼睫隨綿長的呼吸輕輕,纖細的小肚在外面,凝脂般細。
全上下都在發,連頭發兒最外面一圈都瑩著暖融融的金橙。
郁承結微,走近了兩步。聞到上淡淡的梔子花香。
再一低眼,又看到懷歆手中攥著的手機。看樣子本來是準備等他,但實在太困倦所以睡著了。
郁承在上來之前,心里還有過別的設想,但如今卻覺得,沒有哪一幕比眼前的景更人了。
有人等待的覺是這樣的,很多年前,他也曾會過。
郁承在離懷歆近的那一側床沿坐下,垂下眸看著。
時間好像有那麼一刻短暫地停止流,他抬起手,緩慢挲散開的黑發,的,讓人心中熨帖。
懷歆輕緩地呼吸著,對此毫無知覺,睡得像只冬眠的可小。
郁承緒難辨地凝視半晌,輕輕走的手機,放在床頭。
頃俯下,在臉頰上吻了一下。
“晚安。”他喃喃出聲。
第二天早上懷歆醒來,窗外燦爛的早已撒進室。暖調線為周圍添上一抹油畫般的,迷茫地盯著天花板看了半晌,朝旁邊猛地一轉頭。
——沒人。
浴室傳來約約的水聲,懷歆支著坐起來,捂著腦袋了炸掉的呆。
啊啊啊啊啊啊那麼好的機會居然都錯過了!!!
猜你喜歡
-
完結443 章
寵婚似火:嬌妻,好孕到!
黎淺是江城所有女人艷羨的對象,也是所有女人最不屑的存在。 她有著最艷麗精緻的容貌,卻是個作風豪放、人人不齒的私生女。 一場精心的設計,一次意亂情迷的放縱,一個多月後黎淺拿著妊娠四十天的檢查單與陸天擎在醫院
109.6萬字8 24711 -
完結12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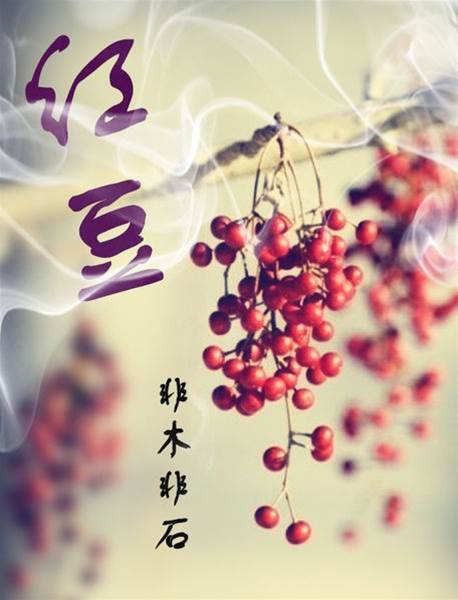
紅豆
他捏著手機慢慢把玩,似笑非笑說:“看,你守著我落兩滴淚,我心疼了,什麼不能給你?”
30.6萬字8 7305 -
完結179 章

嫁給財閥掌舵人後,頂奢戴到手軟
別名:前夫出軌以後,我睡了他兄弟【甜寵 追妻火葬場 直接把骨灰揚了 男二上位 潔 雙處】【排雷:前期女主商業聯姻結過婚,但有名無實】阮嫆跟淩也結婚兩年,淩也提出離婚時,她毫不猶豫答應。手握巨額財產,從此她放飛自我。阮家就她一個獨苗,需要傳宗接代?簡單,“幫我發一則重金求子消息。”就寫,“因丈夫車禍無法身孕,求一健康男性共孕,重金酬謝。”至於要求,“要帥,身材巨好,國外常青藤名校畢業,活兒好,價錢好商量。”她重金挖來的私人助理效率極高,第二天就將應聘者照片發來。完全符合她的要求,且超出預期,就是照片裏矜貴清冷的側影,有點眼熟。她立馬拍板,“就他了。”“這邊隨時可以安排,但對方有個條件。”阮嫆挑眉,“什麼條件?”“他比較害羞,要關燈。”後來她才知道她惹上什麼樣的麻煩,這人不光是千億奢侈品集團慕家獨子,還是她前夫最好的兄弟。——淩也沒有像往常等來阮嫆複合,而是她另有新歡的消息。他忍著心頭絕望窒息,對人道,“離了她老子還不活了,不許勸。”後來半夜酒醉打電話過去。“嫆嫆……”聲音微澀。另頭傳來一道男聲,清冷平靜,“請問半夜找我老婆有事嗎?”“……”
31.5萬字8 1539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