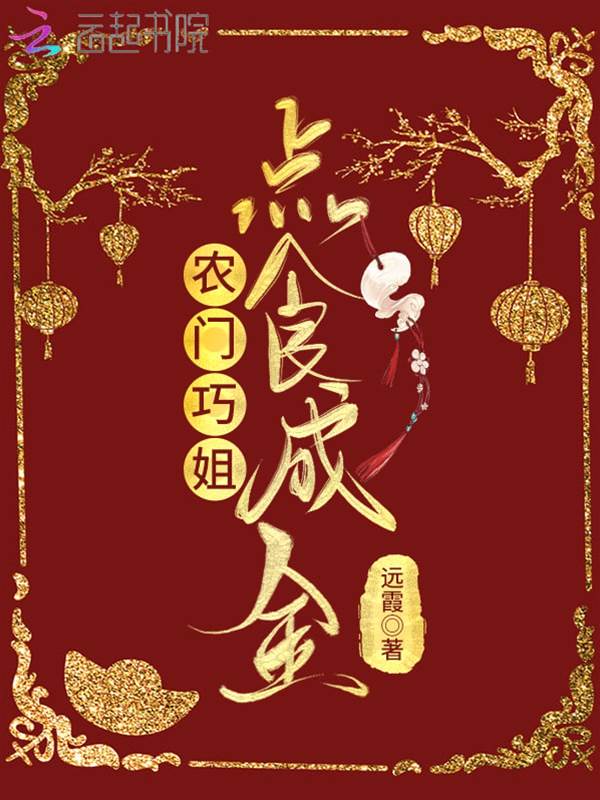《我力能扛鼎》 第45章 第 45 章
來吃酒的夫子們離開時, 已經快要黃昏了,差點午飯連上了晚飯。
唐老爺喝得四六不著的,義山酒量又差, 早早就回屋睡了,剩下的兩桌夫子們也各個東倒西搖,站也站不穩, 哪里還能瞧得出文人風儀?
唐夫人一個眷, 不好送這群醉鬼,只臉說了兩句客氣話, 之后全給葉三峰和管家,由他倆送著夫子們出門坐上了車。
唐老爺仰在椅子上昏頭大睡,醉得已經不像樣了, 下人費了好大勁兒才把他扶起來。唐老爺站都站不穩當,心卻不安分,抓著一個仆從笑哈哈道。
“我兒!神!”
那仆從哭笑不得:“知道啦,爺是神!”
“我兒,神!”唐老爺站在庭院里了一聲, 對著老樹了一聲, 走到回廊轉角,對著養魚的大花瓷缸還吆喝了一聲:“今年一舉中試!明年考上狀元!宗耀祖!”
滿缸錦鯉嚇得直往水缸深鉆。
唐夫人腦殼:“快把老爺扶回屋里睡覺去,酒不醒別讓他出來, 這麼嚷嚷,左鄰右舍都聽著呢,人家聽笑話。”
胡嬤嬤眼里含笑:“夫人這話說得不對, 誰會笑話?他們羨慕還來不及呢。”
“這倒是。”
幾桌杯盤狼藉收拾完,把夫子們借著酒興作的詩也都收好了,唐夫人又仔細問過管家今天都有哪家來送過禮, 送了什麼,把禮單記好,想清楚怎麼回禮……一應瑣事安排完,唐夫人直覺得頭暈腦脹,一個腦袋不夠用。
待月上中天,府里才都歇下來。
珠珠今天跟唐荼荼一張床睡的,自躺到床上,就沒安穩過,吃吃笑個不停。
唐荼荼的褥子薄,被笑得整張床板都在抖,只好把被子裹個團,自己鉆里頭,抗震,不一會兒又熱得不了了。
見姐姐翻來覆去的,珠珠握了一只手:“姐,你是不是也好高興?高興得睡不著?”
唐荼荼:“……還行。”
珠珠翻了個扭向,依舊吃吃地笑:“我以后就是神的妹妹啦!”
這孩子思路不連貫,總是一跳一跳的,隔了不多時,又高興拍掌道:“哥哥真的好厲害,華姨也好厲害,難怪人們都說‘龍生龍生,老鼠兒子會打呢’——爹爹他一般聰明,華姨特別聰明,生下的哥哥就聰明——爹爹讀書一般,娘不讀書,難怪我讀不好書。”
這都什麼跟什麼……難為還扯出了傳學。
唐荼荼困得不行,忽悠:“那你快點睡覺,晚睡就更傻了。你明天還得早點起,去看姥姥呢。”
話沒說完,枕旁已有輕輕的鼾聲,珠珠睡著了。
不嘰嘰喳喳地說話了,唐荼荼的睡意反倒飛走了一半,半天沒睡著。
夏天的夜晚是不安靜的,后窗臨著院兒,開著半扇窗,夜里總能聽到蟲鳴。
唐荼荼枕著手臂,把這幾天的事兒捋了捋,有點靜不下心,不論想什麼,思路總是要繞到天津府那小才子上。
——“天津府武清縣,蕭臨風”麼?
那張云錦作褙、金線繡云紋的神榜,供在了正廳里。唐荼荼下午去看過,把這行字背下來了。
中午聽葉先生的意思,中舉者只寫“某地某人”,中間不寫“家族”,而單單寫一個人名的,基本上可以確定是無族的人。
這實在怪異。
盛朝人把親族緣看得極重,但凡有家族的,誰會不往上加?除非是犯了錯事被逐出家族、辟門另過的;要麼是逃荒逃難、親族死絕的。
葉三峰晌午說起時,隨口說了句“這人來歷古怪”,唐荼荼立馬在此留了個心眼,腦子里冒出了葉先生沒想到的另一種可能,的心撲通直跳。
無家無族的,還有一種況。
——就是這個人,是憑空蹦出來的。
自己,死時損壞,大約是了野鬼,一縷魂兒飄進了這個“唐荼荼”的,頂了“唐荼荼”的名字而活,也就有了親族。
可如果,有人與魂魄沒分離,是隨著穿過來的呢?
改名易姓,無親無族,就能對上了。
唐荼荼滿腦子胡思想,心事重重地睡下了。第二天,比一家人起得都要早,早飯快吃完時,唐夫人才起來。
一大早的,唐夫人喜盈腮:“荼荼又起得這麼早?”
唐荼荼一宿沒睡踏實,不多講,含糊帶過:“天沒亮,我就了。”
一句話,把唐夫人多話都堵回去了。
這些日子禮部忙得腳不沾地,鄉試結束后,總算得了兩日休沐,唐老爺因為兒子中舉,又告了一天假,休完這三天,就要開始晝夜不歇地辦太后壽辰了。唐老爺要在這幾天里,趕把兒子中舉的一應瑣事都辦妥。
有父母親族的,實在是累,唐荼荼旁觀著爹娘和哥哥這幾日,先后拜訪了老宅、舅爺、族長家,拜完了這一圈,才顧上去丈母娘家。
今天要去的是唐夫人的娘家,因為是續娶,哥哥作為繼子,份多是有些尷尬的。好在華瓊和唐老爺和離早,哥哥兩頭來往,跟唐夫人母家那邊也沒斷了走。
進了一道門,就是半個孫兒了。十幾年下來,跟那邊也出了幾分親緣。
義山高中的事,總得讓老人家聽聽,高興高興。唐夫人心里也有揚眉吐氣的意思,想讓娘家人看看,以頭婚嫁給老爺,嫁進門來給倆孩子當后娘,那也是亮眼睛嫁的,不是閉著眼睛嫁。
“荼荼不去看姥姥麼?”唐夫人試探著問。
唐荼荼捧著一杯茶水漱了口,“母親,你們去吧,我今兒上街一趟,有點事兒。”
唐夫人勸了兩句,見荼荼沒有去的意思,也就作罷了。
心里邊卻有點酸:荼荼自華家太太那兒回來,這兩天,明顯心不在焉了,人回了家,心卻沒跟著回來。到底是親娘,自己再怎麼用心,也比不了人家。
吃罷早飯,唐荼荼就帶著福丫出了門,左右太沒大升起來,坐馬車熱,主仆倆索步行著,直奔學臺去了。
鄉試剛放榜,學臺衙門正是熱鬧的時候。
本朝科考有法,所有落了榜但覺得批卷不公的學生,都可以憑號書要回自己的卷子,請求考重新批閱;也可以去學臺查閱中舉考生的卷子,要是覺得哪個名不副實,覺得何批卷不公,都可以公然提出質疑。
自古文人多相輕,經義策還好,時務、方略這樣的主觀題,有不學生會覺得自己答得比中試者好。可絕大多數的學生,還是會心平氣和地接自己落榜的事實,他們一心求上進,更想知道“中舉的卷子好在哪里”,如此,便需要講釋疑。
歷來科舉結束后的那個月,天下講學之風興。
國子監和翰林講會多|人|替著,從早到晚不休,將前百名舉人的卷子一份一份挨著講過去,講學臺下座無虛席,每場都要聚集幾百人。還有學子專門記錄講的話,匯集冊,拿去坊間書館文社賣錢。
眼下,學臺衙門敞開大門,衙差只簡單看過戶籍,不拘份,都能進去聽講。
“小姐,好多差爺……”
福丫從來沒進過衙門,肚子直打擺子,攙著二小姐的小臂給自己壯膽。
唐荼荼把的爪子拍下去,“大方些,你又沒做虧心事,衙差還會抓住你打板子不?你這樣頭塌肩的,看著才像壞人——你看,衙差盯著你看了吧?”
福丫巍巍地直了直腰板。
唐荼荼帶著福丫一路走過哨房與理事院,看見好幾位富家小姐也如一般,來學臺聽講學,欣賞才子答卷。
腹有詩書的孩子真是極的,唐荼荼留神多看了幾眼,迎面走來的姑娘并不忌諱盯著看,淺淺一笑,沖福了一禮。
衙門東院正講學,已經講到第八名的卷子了。滿院子儒衫飄飄,書生們聽得神。
西院是公榜、重批試卷,還有展覽才子答卷的地方。前百名考生的卷子原稿,全都裱好掛在了墻上,滿院三堵墻都掛滿了卷子,供學子們閱覽。
讓唐荼荼心心念念的那個“蕭臨風”,一進門就跟衙差打聽過了。
那蕭臨風帖試問策排了八十多名,口問卻排到了第三,總名次一下提至第二十名,只比哥哥低一位,被制在了哥哥下邊。
這名次有種刻意為之的古怪,是“惜才之心”與“京城臉面”權衡之后給出的名次,確實如葉先生所說,是上頭的伎倆。
三堵墻邊圍著的學子多,最頂上的磚石上以朱筆寫著名次。唐荼荼一個一個數過去,數到“二十”時停下了腳步,抬頭一看。
——蕭臨風!
深呼一口氣,忍住咚咚跳的心跳,借著人矮力氣大,從人堆中隔開一人寬的隙了進去。
猜你喜歡
-
完結1620 章

神醫娘親她又美又颯
九千歲獨孤鶩因疾被迫娶退婚女鳳白泠,滿朝轟動。 皇子們紛紛前來「恭賀」 : 鳳白泠雖貌丑無能又家道中落,可她不懼你克妻不舉之名,還順帶讓你當了便宜爹, 可喜可賀。 獨孤鶩想想無才無貌無德的某女,冷冷一句:一年之後,必休妻。 一年後,獨孤鶩包下天下最大的酒樓,呼朋喚友,準備和離。 哪知酒樓老闆直接免費三天,說是要歡慶離婚, 正和各路豪強稱兄道弟的第一美女打了個酒嗝:「你們以為我圖他的身子,我是饞他的帝王氣運」 九千歲被休后, 第一月,滿城疫病橫行,醫佛現世,竟是鳳白泠。 第二月, 全國飢荒遍地,首富賑災,又是鳳白泠。 第三月,九朝聯軍圍城,萬獸禦敵,還是鳳白泠。 第某個月,九千歲追妻踏遍九州八荒:祖宗,求入贅。 兩小萌神齊聲:父王,你得排號!
284.6萬字8.18 32474 -
完結4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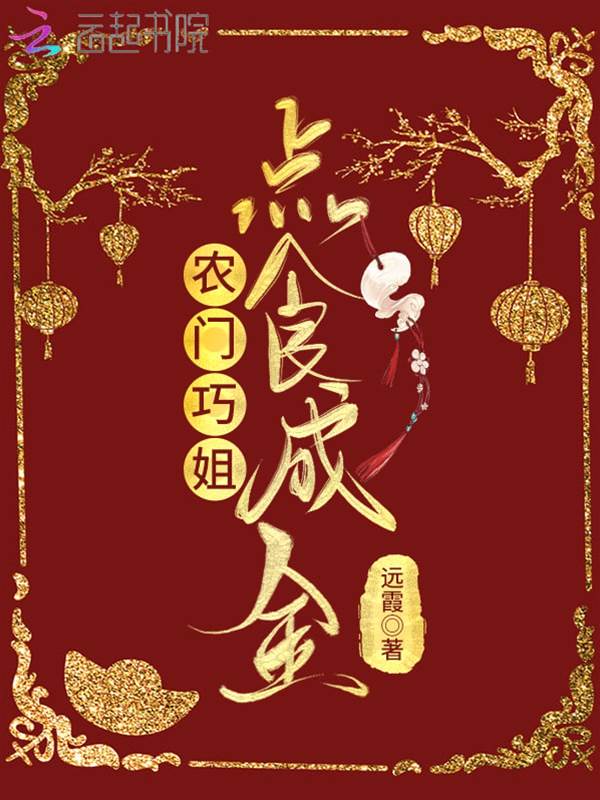
農門巧姐點食成金
高級點心師意外穿成13歲彪悍小農女-包蓉。後奶惡毒,親爺成了後爺。,爹娘軟弱可欺,弟弟幼小,包蓉擼起袖子,極品欺上門,一個字:虐!家裏窮,一個字:幹!爹娘軟弱慢慢調教,終有一天會變肉餡大包,弟弟聰明,那就好好讀書考科舉,以後給姐當靠山,至於經常帶著禮物上門的貴公子,嗯,這條粗大腿當然得抱緊了,她想要把事業做強做大,沒有靠山可不行,沒有銀子,她有做點心的手藝,無論是粗糧、雜糧、還是精糧,隻要經過她的手,那就都是寶。從此,包蓉銀子、鋪子全都有,外加一個自己送上門的親王夫君,氣得後奶一概極品直跳腳,卻拿她無可奈何。
77.6萬字8 33870 -
完結506 章

爺快跪下,夫人又來退親了
中醫世家的天才女醫生一朝穿越,成了左相府最不受寵的庶女。 她小娘早逝,嫡母苛待,受盡長姐欺負不說,還要和下人丫鬟同吃同住。 路只有一條,晏梨只能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鬥嫡母踹長姐,只是這個便宜未婚夫卻怎麼甩都甩不掉。 “你不是說我的臉每一處長得都讓你倒胃口?” 某人雲淡風輕,「胃口是會變的」。 “ ”我臉皮比城牆還厚?” 某人面不改色,「其實我說的是我自己,你若不信,不如親自量量? “ ”寧願娶條狗也不娶我?” 某人再也繃不住,將晏梨壓在牆上,湊近她,“當時有眼不識娘子,別記仇了行不行? 晏梨笑著眯眼,一腳踢過去。 抱歉,得罪過她的人,都拿小本記著呢,有仇必報!
90.4萬字8 2908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