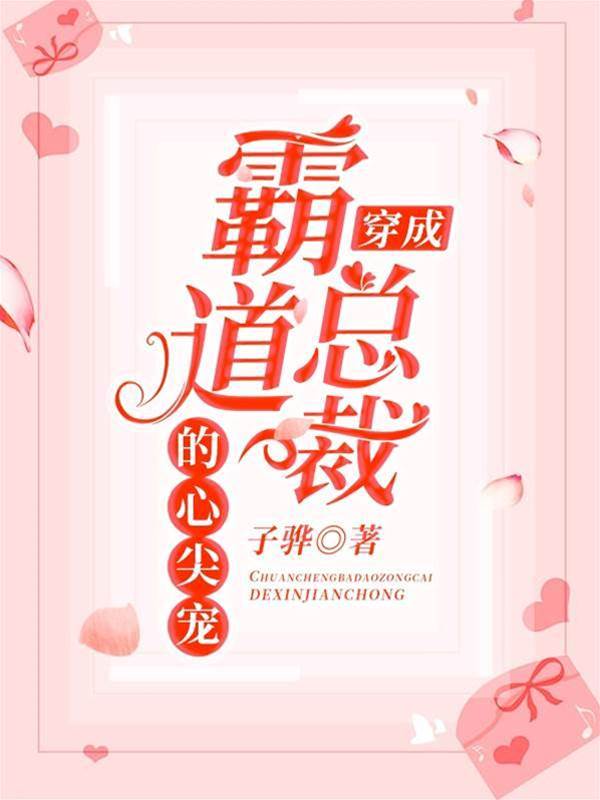《穿成亡國太子妃》 第150章 番外:他也不講理
***
轉眼便到了清明,秦笙從前因為阿姊的關系,同沈嬋走得極近,只可惜故人已逝。
秦笙因為沈嬋的遭遇哭過好幾回。
曾被送去北戎和親,知道那有多可怕,若不是阿姊想辦法救下,只怕現在也已赴黃泉了。
秦笙聽說逢年過節沒人燒供奉,在地府做鬼也是要被人欺負的,沈家已沒人了,怕沈嬋去了那邊也過不好,私下同秦夫人商量,逢年過節給沈嬋燒些冥紙。
秦夫人也心疼沈嬋是個苦命的孩子,自是同意的,只是擔心秦簡依舊過不去心里那關,讓秦笙莫在秦簡跟前提起。
清明這天,秦笙做賊似的溜去廢棄的后院準備給沈嬋燒供奉時,卻發現掃墓回來兄長也在這邊給誰燒冥紙。
秦簡鮮飲酒,此刻卻盤坐在地上,手里拿著掌大個土陶酒壺,自己喝一口,又給地上倒上些許,說:“我是楚臣,你活著的時候,我同你必是勢不兩立的,不過現在你死了,倒是能再同你喝場酒。”
秦笙屏住呼吸躲在未加修剪的花圃后,不敢發出半點聲響。
秦簡可能是醉了,絮絮叨叨說了很多:“當初說好的若得仕,必鋤攘兇,匡扶社稷,到頭來你卻忘了個干凈……”
秦笙咬住,大概猜到兄長是給誰燒的冥紙了。
秦簡再次痛飲一口后,將酒壺里的酒水盡數灑到了地上,在一片殘中離開了院落。
有一瞬,秦笙覺得兄長的形是有些孤獨的。
當然知道,死去的那人,曾是父親的學生、兄長最要好的朋友。
兄長肯在清明為那人燒一份供奉,大抵已是徹底放下心中的怨懟了吧。
一直到看不見秦簡的影,秦笙才從花圃后走出來,把籃子里的冥紙就著沒燃完的冥紙一并燒了,說:“這是給阿嬋的。”
火燎盡了冥紙,晚風一吹,絮狀的紙灰飛。
秦笙閉上眼這風,似和昔日的好友淺淺擁抱了一下。
秦笙突然覺得有些難過,但也知道,對好友來說,死亡帶來的終結,才是解。
那屬于人世的皮囊,困住太久了。
***
清明那場祭奠帶來的,讓秦笙看淡了很多事。
又有人上門來說親時,終于沒再一口回絕,表示一切聽秦夫人和秦簡的。
秦夫人見秦笙一下子變得比秦簡還老氣橫秋,倒是又憂心起來,說親事不急,怕一個人在家中悶壞了,讓去參加詩會散散心。
正好裴聞雁也被遞了帖子,秦笙同一起去,倒是有個伴兒。
二人乘馬車時,裴聞雁著秦笙一臉看破紅塵的神,想起自己聽到的風聲,問:“徐尚書家托人去你們府上說親了?”
秦笙點頭。
裴聞雁不知為何,神變得有些怪異:“你見過徐家長子?”
秦笙說:“并未。”
前來說的夫人倒是把對方夸得天上有地上無。
見裴聞雁言又止,不由問:“怎麼了?”
裴聞雁說:“你們家同意這門親事了?”
秦笙眉心一蹙:“這話從哪兒說起?”
裴聞雁在這些事上一貫明,當即就道:“徐家這事做得不地道,據聞是他們請的那人傳出去的,說先前來秦家說親的,都被你母親回絕了,這回徐家上門來,你母親沒把話說死,八是相中了徐家。”
裴聞雁是見過那位徐家公子的,對方樣貌雖和謝桓沒有半點相似,氣質上卻極像。
先前還當是秦笙見過那徐家公子后,才松的口。
現在看來,分明是徐家想攀秦家這門親,眼瞧著秦夫人那邊留了余地,怕還有旁人上門提親,索借人之口把話傳出去,這樣一來別人知道秦家有中意的婿人選了,就不會再上門自討沒趣。
哪怕秦家怪下來,徐家也能說是人的不牢,把責任推出去。
到時候秦夫人為保秦笙的面,只能矮子中間拔高個兒,認了徐家這門親。
秦笙眉心只蹙了一會兒,就舒展開了:“隨說去,只要我秦家不點這個頭,到時候鬧笑話的就是他們。”
裴聞雁原本還有些氣憤,聽秦笙這麼一說,頓時又笑開:“也對,明眼人都看得出來這是徐家急著攀高枝,換做旁的姑娘還怕損名節,你們秦家怕什麼?”
莫說皇后娘娘護短,便是秦簡逮著個徐尚書的錯彈劾一番,都夠徐家喝一壺的。
**
從裴聞雁那里聽到的消息并沒敗秦笙多興致,不過有了皇后胞妹這層份,出現在這樣的場合,難免被人奉承,秦笙不擅應付這些,見過主人家后,就趕往僻靜躲。
裴聞雁本是同一起的,不過遇見了幾個兒時好友,被拉著說話去了,秦笙在詩會上悶頭吃。
等裴聞雁回來時,秦笙抬起頭正想同說話,曲水流觴席邊的眾人都在拍手好,并且還有不人含笑朝自己看來,秦笙還當是自己吃相不雅,趕端坐好,又用手絹了角。
卻見裴聞雁著臉道:“方才作詩的便是徐家大公子。”
詩會上男席是分開的,中間隔著一片蓮花池。
秦笙往男子席那邊看去,著儒袍的男子姿俊如一桿修竹,正拱手向四方謝禮,見自己也抬頭去時,臉上分明劃過一抹局促,報赧一笑后坐下了。
秦笙卻有片刻失神,的確在他上,瞧見了一個人的影子。
裴聞雁用手肘拐了一記:“你給我清醒點啊!”
秦笙垂下頭,角翹起,但弧度分明多了幾分苦:“我知道。”
那些日子里刻意忘的,如今又被勾起來了,秦笙覺得心里悶得慌,道:“茶水喝多了,我去趟凈房。”
裴聞雁不太放心:“要我跟著嗎?”
秦笙搖頭:“我有婢子跟著,不妨事。”
裴聞雁也看出是想獨自待會兒,沒再堅持。
*
秦笙只是想出去走走,把心里的悶意散一散,府上有幾株梨樹花開得極晚。
秦笙瞧見了,仰著頭看了一陣,同隨行的婢子說:“怪不得都說雪落枯枝似梨花開,這滿樹梨花,也像下過一場大雪一般。”
后傳來一道清雅的嗓音:“像北庭的雪還是汴京的雪?”
秦笙渾一僵,不可置信般轉頭看去,瞧見不遠著一襲藏青儒袍的男子時,怔了半晌,才喚道:“大……大公子?”
面容還是記憶里悉的面容,只是他不再笑了。
謝桓說:“可否請秦姑娘借一步說話?”
若是旁人,秦笙自是不敢的,但眼前人,是個謙謙君子,同跟著自己的婢子道:“琥珀,你去路口等我。”
婢子是秦家的丫鬟,并不識得謝桓,有些猶豫:“可是小姐……”
秦笙說:“大公子一家曾有恩于我,不會害我。”
婢子瞧著謝桓的確是溫文爾雅的模樣,聽話退了下去。
梨花樹下只剩秦笙和謝桓,最初的驚訝過去了,秦笙心中升起一莫名的張。
努力平復緒,笑問:“大公子何時來的汴京?”
謝桓著:“剛到不久。”
他神冷淡,秦笙想著自己先前拒收謝家送來的禮,他心中有了芥也是應該的,只是心中還是有些難過,臉上的笑也跟著收了幾分,禮貌再問了句:“大公子回京是有急事?”
謝桓說:“是。”
秦笙猜測能讓他這般急著進京的應該是謝家的事:“若有秦府幫得上忙的地方,大公子盡管開口。”
謝桓突然問了句:“聽說你快定親了?”
定親是子虛烏有的事,不過這時候自己親口否定,倒像是想再同他藕斷連。
秦笙頷首道:“婚姻大事,由母親和兄長做主的。”
此言一出,便陷了一陣長久的沉默,只有起風的時候,滿樹梨花紛飛而落。
秦笙靜立了一會兒,向謝桓福道:“我出來有一陣了,裴郡主還在等我,便先行告辭了。”
同謝桓肩而過的剎那,秦笙手腕突然被大力攥住。
謝桓說:“你不嫁旁人,嫁我行麼?”
秦笙瞪大了眼。
謝桓已轉過來,黑沉的眸子一瞬不瞬盯著:“我已向陛下和娘娘遞了折子,奏請調回京城。”
“你喜歡汴京,我也可以留在汴京。”
這話一出口,秦笙突然就控制不住眼眶的意:“我不值得大公子為我做到這份上……”
謝桓攥著手腕的力道未松分毫:“值不值得,我說了算。”
他用另一只手幫掉眼淚:“旁人能為你做的,我可以做到,旁人做不到的,我也可以做到。你要不要嫁我?”
秦笙淚流不止,曾經讓止步這段的,就是這千里之遙,但他都已跋涉過這千里,走到了跟前,還有什麼不敢邁出這最后一步的。
秦笙含著淚點了頭。
謝桓一直抿的角這才松了幾分,看著眼前這張恰似梨花帶雨的面容,從抵達汴京聽到將要與旁人定親就升起的那焦躁卻并未消散。
等上到一片溫的時候,他才意識到自己吻了上去。
當真是瘋了。
可腦子里只有理智被轟然沖垮的麻痹快意。
幸好,他趕來了。
他奏請回京的折子還沒批下來,就收到了秦家把謝府送去的東西退回來的消息。
各府去秦家提親的事他也有所耳聞,秦家在這時候拒收他送去的東西,他怕秦家已經找到乘龍快婿了。
他一刻不敢耽擱,匆匆進京,稍一打探關于的消息,就聽說了即將和徐尚書之子定親的事,當時只覺心口似被油烹火燒過。
這個吻唐突到讓謝桓自己都錯愣不已,怕嚇到在秦笙,他只是一就退開,“我已經讓人去秦府了,你母親兄長若同意,我擇個吉日就去下聘。”
秦笙跟只呆頭鵝似的傻愣愣站在原地,謝桓說了什麼都沒聽清。
從前一直覺著謝桓溫雅隨和,今日才驚覺,他同謝馳不愧是兄弟,他強勢不講理的時候,半點不遜謝馳。
猜你喜歡
-
完結666 章

報告王爺,王妃出逃1001次
一朝穿越,要成為太子妃的葉芷蕓被大越的戰神當場搶親!傳聞這位戰神性情殘暴,不近女色!性情殘暴?不近女色?“王爺,王妃把您的軍符扔湖里了!”王爺頭也不抬:“派人多做幾個,讓王妃扔著玩。”“王爺,王妃要燒了太子府!”王爺興致盎然:“去幫王妃加把火。”“王爺!不好了,王妃要跟南清九王爺踏青!”王爺神色大變:“快備車,本王要同王妃一起迎接來使!”
96萬字8 251098 -
完結37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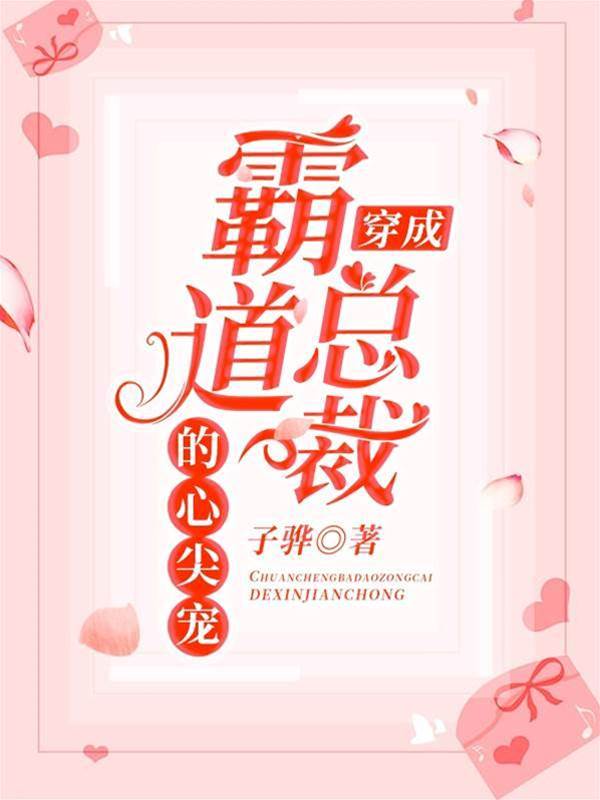
穿成霸道總裁的心尖寵
金尊玉貴的小公主一朝醒來發現自己穿越了? 身旁竟然躺著一個粗獷的野漢子?怎會被人捉奸在床? 丈夫英俊瀟灑,他怎會看得上這種胡子拉碴的臭男人? “老公,聽我解釋。” “離婚。” 程珍兒撲進男人的懷抱里,緊緊地環住他的腰,“老公,你這麼優秀,人家怎會看得上別人呢?” “老公,你的心跳得好快啊!” 男人一臉陰鷙,“離婚。” 此后,厲家那個懦弱成性、膽膽怯怯的少夫人不見了蹤影,變成了時而賣萌撒嬌時而任性善良的程珍兒。 冷若冰霜的霸道總裁好像變了一個人,不分場合的對她又摟又抱。 “老公,注意場合。” “不要!” 厲騰瀾送上深情一吻…
34.6萬字8 23505 -
完結2757 章

我家王妃很任性
鬼醫毒九一朝醒來,成了深崖底下被拋尸體的廢物,“哦?廢物?”她冷笑,丹爐開,金針出,服百藥,死人都能起死回生,這破病就不信治不了了。然而低頭一看,還是廢物。“……”…
499.8萬字8 40547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