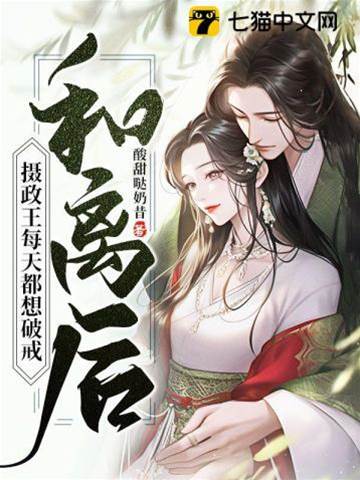《折君》 第36章 第36章
陳小妹的直覺不錯, 陳升前腳走,陳太太洗了把臉重新上了妝,后腳也出了門。
至于是往哪兒去的, 去做什麼的,陳小妹是半點不知,瞧著人走得不見影了,在院子里踱了半天步,想不出來,又疑心自己思慮太多,也是沒別的法子, 折轉回了院自己屋里去了。
又說柳家村,柳漁早上出門不久,王氏提著一大籃子裳去了河邊。每日里這個點, 正是婦人們浣時,也是這條河一天最熱鬧的時候。王氏與正洗的婦人們打了個招呼,尋了眼下還空著的位置,把籃子里的服都拿出來放在磊起的石塊上, 先把空籃洗凈,這才拎起服浣洗起來。
見王氏悶頭洗, 與挨得近的一個婦人挪了挪子,湊得離王氏近了些, 笑問:“你家漁兒, 好事是不是近了?”
王氏浣洗的作一頓,又繼續洗, 口中道:“這怎麼說的?還小呢, 還準備再留兩年。”
那婦人吃吃笑起來:“鎮里的大戶人家想娶, 你舍得留啊。”
王氏愣住:“什麼大戶人家?”
婦人見這神, 奇道:“你不知道?昨天陳槐花不是去你家了?”
陳槐花正是陳媽那妹子的名字。
王氏點頭,“找我家漁兒幫著打個絡子,這怎麼扯到婚事上頭去了?”
那婦人就笑:“我可是瞧得真真的,跟著一起去的是姐,就在你們家院子外瞧著呢,陳槐花恁鬼,想是帶著姐來相漁兒的。”
王氏這兩年沒見人探頭探腦的在外邊瞧閨,也不以為奇,“陳槐花娘家的算哪門子大戶人家。”淡定的又洗起裳來。
婦人撲哧笑了起來:“你想事可真簡單,那陳槐花姐姐家是不富裕,可做工的那家是鎮上陳家呀,開書齋那家,你家寶哥兒日常用的一應筆墨紙硯和書本都是那書齋買的吧,這不是大戶,哪家是大戶。”
王氏自然知道鎮上那家書齋的,可一臉莫名,“一個幫工,主家富不富與什麼相干,你想多了。”
婦人笑起來:“是你想了,你家漁兒生得那樣好,你看我們這些人敢替家里小子上門提親不?這樣漂亮的姑娘就不是嫁寒門貧戶的,陳槐花和姐心里能沒數啊,所以我猜著,說不定是替主家來瞧的,你家漁兒最近不是天天往鎮上去?沒準兒就是陳家人見著了。”
王氏一愣,那婦人尤不知,繼續一邊洗一邊道:“陳槐花倒是,我昨天問是一句話也沒問出來,我瞧著八九不離十的,你就等著老來兒福吧,這要是嫁進陳家,那就是天上的好日子嘍,我聽說陳家太太小姐,上穿用的都是到縣里采買,你呀,以后指定……”
一句跟著沾兒的沒說完,王氏手里洗的裳不知怎麼就松了,被湍急的河水沖了下來。
那婦人驚呼:“呀,你裳!”
一邊提著搗杵去撥弄,河水急,把那裳沖著就往下游去了,婦人忙喚:“柳麻子家的,快,勾住那裳。”
那被做柳麻子家的是個面皮黑的矮婦人,背駝起好大一個駝峰,就顯得沒有脖子,頭都著一樣,瞧生得這樣,手腳卻是個再利落沒有的,一聽上游婦人喚,顧不得鞋被打,一個大步就下了水,把王氏被沖下來的那件裳撈了起來,連呼幾聲好險,道:“要是再沖出一點,我也不敢下水了。”
此原是渝水河一條主要分支,經長鎮流下,河面極寬,邊沿半丈許還好,河中心段水深過人高,不會水的下去了腳都打不著底,沒人搭救恐怕就上不來了。
王氏面煞白,被旁邊那婦人提醒了好幾聲,才知道去那柳麻子媳婦手上拿被沖走的裳,又謝過。
后面的裳洗得都不是對付兩個字好概括的,幾乎是水里晃一晃,撈上來,擰干,扔進籃子里就提著回去了。
把旁邊那與說話的婦人瞧得一愣一愣,家去時上伍氏,特意拉住了,懵頭懵腦問一句:“你婆婆是不是對你們家漁兒婚事有什麼打算啊?”
伍氏聽了前因,魂都震了一震,可管不著王氏的古怪,管的是眼見要到手的銀子就要飛了。
這一天四月初十,恰是逢集的日子,走回自家院里和林氏打了個招呼,就往鎮上去了。
柳漁尚不知陳嬸那位姐姐來一趟,能被個瞧見的婦人把目的猜出花來,且還傳到了王氏并伍氏耳中,更不知伍氏已經鬣狗一樣往鎮上追來了。
也不知陸承驍滿鎮子主街上轉著找的影,只當先時瞧見不過偶然。
在李宅附近徘徊,好容易等到附近一個孩出來,悄悄哄了套出話來,才知那位李爺出門還不曾歸,滿腹心事的準備打道回柳家村去。
同一時間,陳升離了家先回了趟書齋,問伙計柳漁再沒來過,因想著柳漁來鎮上次次都是去繡鋪,就急往繡鋪走了一趟,在兩家繡鋪都沒看到柳漁的影,陳升一急,牙一咬,決意往鎮北看看。
這般打算著,疾步就朝鎮北去了,恰是湊巧,柳漁剛走出鎮北主街,陳升瞧見一個背影,急忙出聲喚道:“柳姑娘,柳姑娘,等等!”
柳漁不消回頭都聽得出這是陳升的聲音,眉頭一挑,竟出來得這麼快?
所以是陳升戰斗力不行,還是那位陳太太太段位太高?
側駐足,靜候著陳升走近。
陳升一路小跑著到柳漁近前,氣息還沒勻,一雙眼就灼灼看著柳漁,道:“柳姑娘,你還沒走真是太好了。”
柳漁從他話音里聽出細微的愉悅,有些奇怪,那位陳太太可不像是這麼好擺平的。只不久前才說過不相往來的話,面上的樣子還是要做的,冷著臉向后退了一步,一副不肯與陳升有糾纏的模樣。
陳升心里那點子愉悅霎時散了個干凈,面一,就想手拉住柳漁。
柳漁眉頭一皺,正要避開,陳升后領被人整個提起向后一扯,他雙手拉住袍前襟才沒被勒得背過氣去,只是腳步便整個虛浮懸空的被人摜向了后方,站立不穩,嘭地一屁結結實實摔在了地上。
陳升痛得整張臉都扭曲了,更因為在柳漁面前丟了丑,一張臉脹得豬肝一般,正要看看是哪個渾人干的好事,想找個后賬尋回些氣勢來,抬眼就看到陸承驍冷著臉,居高臨下睨著自己。
他與陸承驍已是多年未打道了,然而十五歲那年被十三歲的陸承驍碾著揍的記憶這輩子都沒辦法忘,乍一看手的人是陸承驍,他心下就是一,到的質問就卡殼一般噎了回去。
陸承驍這一年十八,遠比陳升記憶中十三四歲的他高大,在袁州書院讀書幾年,看著多了讀書人的斯文,可陳升太清楚陸承驍是怎麼去的袁州城的。
年僅十四就能從幾個水匪手里救下一條命來,袁州城的書院聽聞是騎劍都教的,現在的陸承驍只會更難招惹。
陳升那一怒氣都不及騰起,氣焰就已經搖搖將滅了。
只是想到柳漁也在,自己這般被陸承驍摜到地上若是連吭也不敢吭一聲,未免也太窩囊丟臉,怕是柳漁也要看他不起了,陳升這才強作鎮定,厲荏地喝道:“陸承驍你發什麼瘋!”
陸承驍遠遠過來,見陳升要去拉扯柳漁時,腦中的弦在那一霎就崩斷了,此時看著陳升,他滿面霾,聲音里都冷沉沉浸染了幾分戾氣:“說話就說話,你什麼手腳,再有一次,我看你那手別要了!”
陳升腦子里轟隆隆的像沉雷滾過,陣陣悶響。
陸承驍果真喜歡柳漁!
陳升被伏得搖搖墜的勇氣似乎又燃了起來,他仰著陸承驍,才覺自己這樣坐在地上,實在是輸了氣勢,忙又爬起,站到了陸承驍面前。
這一相對而立,陳升就絕的發現,從來個子都屬中上的他,十五歲時個頭不如十三歲的陸承驍,五年過去了,竟還是要微仰著頭才能與之對視。
盡管誰的注意力也沒在高差上,陳升一張臉仍舊脹得通紅,垂在側的手攥拳,一子邪氣突突地直往腦門竄去,口就道:“我與柳姑娘已是在議婚嫁了,站一說幾句話又與你什麼相干!”
陸承驍臉驟然沉下,看著陳升的目更添七分涼意:“人去了嗎?柳家應了嗎?三書六禮過了幾禮!”
陳升霎時啞然。
陸承驍冷聲道:“既然都沒有,你又憑什麼在這里大放厥詞!”
陸承驍和陳升還對峙著,后邊的柳漁卻因無意掃到河對岸一眼,倏然變了面。
猜你喜歡
-
完結433 章

農女為商:撿個王爺來致富
「無事」青年柳小小機緣際會到了古代,卻成了一個還沒進門就死了丈夫的「掃把星」。爹不疼娘不愛就算了,還要繼續把她嫁給「公公」沖喜!行吧,既然你們要這樣做,那就別怪我不客氣了,柳小小開啟了實力虐渣爹,懟渣孃的狀態。之後,本想手握靈泉發家致富奔向小康,偏偏有那不長眼睛的鄰居和親戚湊過來非要「借光!」光,沒有。懟,管夠!當日你們對我百般刁難,如今我讓你們高攀不起。隻是,我後麵那個尾巴,雖然你長的是高大帥,可現如今的我隻想發家不喜歡男人,你為什麼要一直跟著我!!!尾巴在身後委屈巴巴的看著她:「我賬房鑰匙在你那呀,我沒錢,所以隻能跟著你了呀。」柳小小:「……」誰特麼想要這玩意,如果不是你硬塞給我我會接?
74.2萬字6.4 76356 -
完結105 章

盲妾如她
俞姝眼盲那幾年,與哥哥走散,被賣進定國公府給詹五爺做妾。詹司柏詹五爺只有一妻,伉儷情深,因而十分排斥妾室。但他夫妻久無子嗣,只能讓俞姝這個盲妾生子。他極為嚴厲,令俞姝謹守身份,不可逾越半分。連每晚事后,都讓俞姝當即離去,不可停留。這樣也沒什…
49.6萬字8 28752 -
連載205 章

食全食美
餐飲大王師雁行穿越了。破屋漏雨,破窗透風,老的老,小的小,全部家產共計18個銅板。咋辦?重操舊業吧!從大祿朝的第一份盒飯開始,到第一百家連鎖客棧,師雁行再次創造了餐飲神話!無心戀愛只想賺錢的事業型直女VS外表粗獷豪放,實則對上喜歡的女人內心…
75.2萬字8 15211 -
完結56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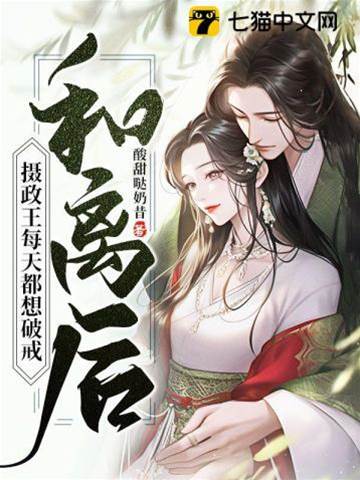
和離後攝政王每天都想破戒
葉芳一朝穿越,竟然穿成了一個醜得不能再醜的小可憐?無才,無貌,無權,無勢。新婚之夜,更是被夫君聯合郡主逼著喝下絕子藥,自降為妾?笑話,她葉芳菲是什麼都沒有,可是偏偏有錢,你能奈我如何?渣男貪圖她嫁妝,不肯和離,那她不介意讓渣男身敗名裂!郡主仗著身份欺辱她,高高在上,那她就把她拉下神壇!眾人恥笑她麵容醜陋,然而等她再次露麵的時候,眾人皆驚!開醫館,揚美名,葉芳菲活的風生水起,隻是再回頭的時候,身邊竟然不知道何時多了一個拉著她手非要娶她的攝政王。
99.6萬字8 900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