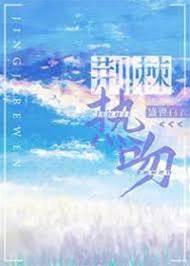《誘餌》 第63章 只給我一個月
萬喜喜凝視他,“陳淵,我們單獨談。”
說完,退出書房。
陳淵攥著拳,許久,松開。
冗長的走廊,墻壁遮住,他佇立在影,面容晦暗不明。
他究竟過多人的夢,又殘忍。
“沒有轉圜了嗎。”
陳淵聲音沙啞,“抱歉,喜喜。”
“同我結婚,你很委屈嗎?”萬喜喜紅著眼眶,“我不嗎,不嗎?鄭野的堂姐,易名的妹妹,們也不聯姻的丈夫,易蘊在婚禮前甚至要逃婚,可最終,們也留下了。”
挨近他,揪住他領,用力哭訴,“你為什麼死活不愿試一試?哪有一個丈夫對妻子這樣冷漠,你拒我千里之外,當然無法我。”
陳淵閉上眼,依然那句,“抱歉。”
萬喜喜無力垂下手,一向濃妝艷抹,奢華張揚。萬家的人,,母親,繼母,都如此。
可陳淵不喜歡,他鐘糯糯的人,不風浪,純白無瑕,依附著他,脆弱易碎。
于是,萬喜喜再不那些,學著干凈收斂的模樣,陳淵卻看不到。
“所有人都出席了我們的訂婚宴,你提出退婚,要死我嗎?”
他鄭重面對,“我會澄清,最大限度保全你的面。”陳淵膛鼓起,又塌陷,像在爭斗,“我盡力了。”
“你認真和我往過嗎?”笑出來,“你所謂的盡力,是抗爭陳伯父的施,沒有馬上娶我,不至于將分手演變離婚,這也是你的義?”
陳淵低眸,的憔悴落魄映在他眼底,“我欠你的。”
萬喜喜抹了一把眼角,“接你了嗎。”
“跟無關。”他掏出打火機,“是我沒分寸。”
“你會娶嗎?”
陳淵點煙的手,一。自從函潤離世,他沒想過結婚。
西崗陵園那座墓碑,碑文寫著陳淵之妻。
業說,津德的長公子是癡得過頭,富誠的長公子是長念舊。
區別在于,前者就了,后者,沒瘋狂到那地步。
權勢,利益,陳淵并非不顧。
只不過,喬函潤死在最燦爛、他最濃烈之際。
一切猝然覆滅,無助,絕,抑,番攻擊著他。
想不深刻,都難。
因此,陳淵荒廢緬懷了十余載。
讓男人恨,和讓男人疼,這兩者,都刻骨銘心。
陳淵猛吸一口,煙霧慘淡,環繞他潦倒的胡茬,消沉的眉目,“我不知道。”
萬喜喜在這時抱住他,臉埋進他口,“我同意你退婚,陳伯父才會允許。”
煙灰掉在肩膀,陳淵立刻撇開,火星子蹭過,堪堪墜地。
他鼻息滿是煙草味,“你肯嗎。”
“換來你高興,解。我就肯。”萬喜喜注視化為一灘的白灰,“我不想為上流圈的笑柄,我們相好一個月,哪怕你演戲,再分。”
崩潰的哭腔,“陳淵,對我好一點,只一個月,你一輩子那麼長,我只索取一個月。為我的意,為萬家的面,行嗎?”
到底是他對不住。
頂著未婚夫的名頭,沒盡過半分責任。
彌補一次,他也好過些。
半晌,陳淵掌心摁在后背,虛虛地回抱,“我答應你。”
萬喜喜仰面,淚眼朦朧,“我承認,我不甘心。我我的男人也能我,萬一假戲真做,你也了呢?陳淵,我像一個孤注一擲的賭徒,是不是?”
“別說了,喜喜。”他打斷,視線從眼淚間離,“我能給的,就這麼多。”
陳淵沒再回書房,直接走出客廳,正要上車,對面地庫里程世巒的吉普震起來,夾雜著細微的低語。
那音很悉,他下意識駐足。
地庫線昏黯,揭過擋風玻璃,后座兩軀投映在窗戶上,影影綽綽。
顯然太忘,車門被男人大力的作踹開,都沒發覺。
“我們給陳政下藥,你照顧他的起居,下在牛里,慢藥查不出問題。”
人嚇壞了,“世巒!你別沖。”
男人不罷休,“程毅是醫生,他很容易搞到這類藥,保證神不知鬼不覺。”
“這太冒險了。”人慌里慌張,攀著他胳膊坐起,“陳政他...”
男人惱了,“你什麼意思?你不舍得他?”
人沒聲響。
“他有老婆,有兒子,他要是你,你會當三十年的人嗎?江蓉的娘家早沒落了,他娶你,是難事?你還執迷不悟他的蒙騙!”
人興致全無,系著扣子,“陳政一旦沒了,陳淵是長子,順理章繼承家產,那崇州呢?我的心全白費了,你只考慮私,我要顧及他的前途。”
“好好,是我著急了。”男人重新摟住,“你去哪?”
“我去倒茶。”
“有保姆,用得著你?”
人推搡他,“陳政習慣我伺候了。”
男人反鎖門,“你天天伺候他,有空不伺候我?”
車又開始晃。
大約二十多分鐘,何佩瑜從吉普車下來,整理自己擺,盤發有些垂垮,顴骨浮著兩團紅。
“何姨。”
一驚,當看清院中的男人,臉瞬間煞白,“陳淵,什麼時候回來的?”
他著半支煙,神高深莫測,“回來很久了,打擾何姨了嗎。”
何佩瑜心虛,總認為他話里有話,像挖掘到什麼,陳淵越是平靜,這預越強烈。
如今,兩房斗得如火如荼,二房在部險勝,大房在外頭風,江蓉又失勢,倘若陳淵真逮到什麼重磅把柄,沒理由不趁機扳倒二房。
何佩瑜稍稍平復,“沒打擾,我已經痊愈了。你父親和岳父在書房商定婚期,10月28,宜嫁娶的吉日。”
“見完面了。”陳淵越過頭頂,向車里的程世巒,他并未揭穿剛才的勾當,“何姨既然痊愈,您在程醫生的車上,是詢問父親的病嗎?”
陳政有心炎,不嚴重,但大戶權貴個頂個的惜命,心療養多年了。
何佩瑜用指甲蓋梳著鬢角凌的發,“我不舒服,程醫生替我檢查,他車上有械。”
陳淵笑了一聲,“何姨多保重,母親犯錯,我代向您賠不是了。”
何佩瑜沒由來的,渾一抖。
這話,明著恭敬和,暗藏玄機。
“我是老病了。”竭力表現得鎮定,“不干你母親那次...”
做法二字,哽住。
在老穩重的陳淵面前,神佛鬼怪的言論,實在太荒謬。
何佩瑜被他審視得不自在,編了個借口,“你父親晚餐想喝揚州的鴨筍湯。”
陳淵仍舊溫和客氣,“有勞何姨。”
何佩瑜邁上臺階,聽著后面的靜,直到他發,才扭過頭,目送那輛車駛離。
程世巒隨即從車庫出來,“佩瑜,他發現了?”
神凝重,沒應聲。
***
沈楨到國際商場,傍晚6點。
廖坤在大門接,手里捧一束黃玫瑰。
警惕,“干嘛?”
“沈大,求你幫個忙。”
沈楨接過,略一數,18朵。
11,19,都有特殊寓意,18,正常的。松口氣,對廖坤這型的,不冒。
國最頂級的高知分子了,醫學博士后,才二流本科,沒共同語言。
自己憋不住笑,“我差點誤會,你故弄玄虛?”
廖坤嘬牙,“我談了個博士友,陳主任跟你講了沒?”
“哪個?”
他一噎。
廖坤的博士前任,多到數不清。
“最新那個,37歲科研所的,說我打扮土氣。”
沈楨聞了聞花香,“幫你挑服?”
廖坤拉著進商場,“七折,便宜啊,我適合哪款?輕風,要不日韓系,歐太顯老吧。”他一拍大,“校園學長的風格,我麼,扎領結。”
另一只手沒閑著,給陳崇州發消息。
——我不擅長騙人,以后找我。
很快,他回復:三樓,裝店。
扶梯上,沈楨作嘔,“學長風...你年紀奔四了。”
“崇州老師!”
石破天驚的一嗓子,和廖坤齊刷刷看過去。
李妍舉著一款白蕾,走到休息區,男人坐在椅上,翻看一本雜志。
“我喜歡。”
男人蠻有耐心,配合,“不錯。”
“和我搭嗎?”
他打量,“可以。”
陳崇州上的格子襯衫,還是沈楨買的。
覺得,他穿藍好看。
清俊,英朗。
當即調頭。
“哎——”廖坤拽住,“是李妍,知道陳主任在蕪城,打著旅游的幌子,到醫院約他。”
“開房也是李妍主的?”
“應該是...”
“我在場。”沈楨盯著廖坤,“他主的。”
這海王。
廖坤咂舌。
就算賭氣,也玩太大了。
猜你喜歡
-
完結133 章

偏執顧爺今天也很病嬌
“你還是想逃離我,對不對?” 脖頸上的血腥味開始肆意瀰漫,男人仿若感受不到絲毫痛意。 “你恨我嗎?” 男人的眸光淡淡的,卻依然貪戀的在虞思思的臉頰上停留。 “這麼恨我啊?” 男人輕描淡寫的反問道,眼底卻染上了異樣的興奮。 “這樣也好,至少我是你最刻骨銘心的人。”
12萬字8.09 17419 -
完結13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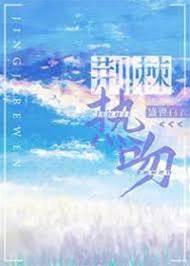
荊棘熱吻
季弦星有個秘密,她在十六歲的時候喜歡上了一個人——她小舅的朋友,一個大她八歲的男人,后來,無論她怎麼明示暗示,鐘熠只當她是小孩。她安靜的努力,等自己長大變成熟二十歲生日那天,她終于得償所愿,卻在不久聽到了他要訂婚的消息,至此她一聲不響跑到國外做交換生,從此音訊全無。再見面時,小丫頭長的越發艷麗逼人對著旁邊的男人笑的顧盼生輝。鐘熠走上前,旁若無人的笑道:“阿星,怎麼見到我都不知道叫人了。”季弦星看了他兩秒后说道,“鐘先生。”鐘熠心口一滯,當他看到旁邊那個眉眼有些熟悉的小孩時,更是不可置信,“誰的?”季弦星眼眨都沒眨,“反正不是你的。”向來沉穩內斂的鐘熠眼圈微紅,聲音啞的不像話,“我家阿星真是越來越會騙人了。” 鐘熠身邊總帶個小女孩,又乖又漂亮,后來不知道出了什麼事,那姑娘離開了,鐘熠面上似乎沒什麼,事業蒸蒸日上,股票市值翻了好幾倍只不過人越發的低沉,害的哥幾個都不敢叫他出來玩,幾年以后,小姑娘又回來了,朋友們竟不約而同的松了口氣,再次見他出來,鐘熠眼底是不易察覺的春風得意,“沒空,要回家哄小孩睡覺。”
51.8萬字8.18 229727 -
完結2033 章
盛世婚寵:帝少難自控
她的孩子還未出世便夭折在肚子裏!隻因她愛上的是惹下無數血債的神秘男人!傳聞,這個男人身份成謎,卻擁有滔天權勢,極其危險。傳聞,這個男人嗜他的小妻如命,已是妻奴晚期,無藥可治。他說:夏木希,這輩子你都別想從我身邊逃開!你永遠都是我的!她說:既然你不同意離婚,卻還想要個孩子,那就隨便到外麵找個女人生吧!我不會怪你。五年後她回來,發現那個男人真的那麼做了。麵對他已經五歲的孩子時,她冷冷地笑著:秋黎末,原來這就是你放棄我的原因?那時她不知道,這個男人已丟掉了一隻眼睛……而這個五歲的孩子,竟也滿身是謎!——那是夏與秋的間隔,夏的末端,是秋的開始。秋,撿到了失意孤寂地夏的尾巴。夏,許諾終生為伴,永不分離。經曆了離別與失去,到那時,秋,還能否依舊抓住夏的氣息?
566.6萬字8 14158 -
完結1081 章

唐門大佬在影壇
【娛樂圈+女強+爽文+馬甲】精通毒術和暗器的唐門少主唐舒穿越了,變成了以白蓮花女配黑紅出道的十八線小新人。綜藝播出前:黑粉:“白蓮花人設已深入人心,怕是本色出演,就別強行洗白了吧!”綜藝播出後:黑粉:“我竟然覺得唐舒有點可愛,我是不是不對勁了?”當國家機械工程研究院表示:唐小姐是我們重點聘請的研究顧問。黑粉:“啊這...
131萬字8 24551 -
完結637 章
重生後,豪門父母和五個哥哥找到了我
她,國際第一殺手,一次任務遭人暗算,穿成一個因早戀被退學,且被發現不是父母親生後被趕出家門的假千金。收養她的農戶還要將她嫁給隔壁老王?剛搞砸婚事,親生父親便來接她,她從假千金一躍成為真正的豪門千金小姐。五個哥哥,各個妹控。回到原來的學校後,同學們嘲笑她是個假千金?嘲笑她學習成績差?嘲笑她當眾和校草表白被拒?嘲笑她除了長相一無是處? 哥哥們︰天涼了,這些人家里該破產了!
93.4萬字8 12296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