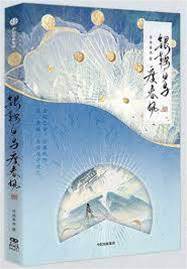《玲瓏四犯》 第26章 第 26 章
是一心盼著云畔能在幽州辦喜事的,漁縣主死后,家里一直沒有起筵的名頭,自己掌家掌得怎麼樣,也沒個人知道。外人只說妾代君之職,急于要替自己正名,好讓那些人領教的能干。結果指好的事又落空了,反倒連江珩都要上人家家里禮去……這麼說來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愈發地不上算起來。
還有一樁,柳氏站在邊上問:“舒國公夫人那麼潑辣的子,能容咱們登門?”
江珩垂下了眼,漠然道:“你們都不必去,原就是借著人家府邸辦事,還拖家帶口全數登門,人說起來不好聽。”
這是始料未及,柳氏簡直有些傻眼,“不……不是……既然借人家府邸,辦自己家的事,咱們怎麼不能出席?”
這就是小婦見識淺薄了,以為偌大的舒國公府是賃鋪,當真能夠借用嗎?
江珩有些不耐煩,擰眉道:“說是借辦,實則是我邀上那里送巳巳出閣罷了,喜宴從頭到尾都是舒國公夫婦持,你怎麼不懂其中的道理?”說著別開了臉,著膝頭道,“上回和長姐鬧得那模樣,敢請你,你倒敢登門?還是安生在家吧,等這樁婚事辦完了,其他再從長計議。”
柳氏無話可說了,為自己不平了半晌,最后問:“那雪畔他們呢?雖說是庶出的弟妹,好歹是一藤上下來的,小娘子不會連弟妹都不認了吧?”
“還要把雪畔雨畔和覓兒送到人家府上,看人面、人冷眼?”江珩提高了嗓門,出食指朝門外指點,“人家是巳巳的姨母,和三個孩子拐著十八道彎呢,你就算要讓孩子見世面,也不該挑在這個時候。”
“那……那……”柳氏搜腸刮肚,把江珩的兩個姐姐都搬了出來,“兩位姑母怎麼辦?侄婚,總不能跑到人家府上道賀去吧!”
江珩聽了,胡擺了兩下手,“們嫁的都不是什麼值得夸口的人家,依著我說,不去也罷。”想了想又添上一句,“回頭在莊樓擺上兩桌,到時候請們補一杯喜酒,意思到了就了。”
柳氏茫然了,喃喃說:“這麼辦,可是要淪為全幽州的笑柄了……”
提起這個江珩就惱恨,高聲道:“笑柄?我早就為兩地的笑柄了,你不知道嗎?”
他從來沒有發過這麼大的火,這一聲,把柳氏都給吼得呆住了。
所有的怨氣積攢起來,總有要決堤的一天,是宅婦人,一輩子就那麼大一片天地,哪里知道外頭的境況。男人要在場上行走,要立世為人,但凡有半點錯,要遭多人的冷眼,知不知道?
為了巳巳那件事,弄得朝中人人恥笑,就連家都聽說了他府上的奇事,那日問起魏國公的婚事,還特意叮囑了一句,讓他好生善待江侯嫡,其中包含著怎樣的意味,還用得著細說嗎?
唉,真是提了就來氣,雖然宅之事用不上宰牛刀,男人們也都有過偏妾的經歷,但被朝野上下矚目,總不是什麼彩的事。這會兒是真懷念縣主在時的年月啊,簡單庸碌地活著,好過將上種種弊病,無限放大在眾人眼前。
可是怎麼辦呢,他不是不知道柳氏的病,當面一套背后一套,眼皮子淺、會算計、貪小便宜……但這些病不足以讓他狠下心來懲治。畢竟十幾年的,陪他度過了多個郁郁不得志的日夜。自己是可憐的,柳氏則是可悲的,到最后這筆糊涂賬混作一團,已經說不清誰是誰非了。
這頭的柳氏呢,驚愕之余腦子轉得飛快,自己催促著他去找了魏國公,最后商議出這麼一個結果來,想必其中的過程愉快不到哪里去。
這回是真的有些怕了,不怕別的,只怕江珩對的由濃轉淡。于是無聲地哭起來,就是那種梨花帶雨卻不見泣的模樣,知道,這樣最能擊中男人的心。
“原是我錯了……”輕聲說,“是我忘了自己的份,拿小娘子當自己兒一般,竟還想著親手送出門。”
江珩抬了抬眼,看見的就是那樣一副雨打梨花的景。
里平靜地說著,眼里的淚珠卻大顆大顆地掉落下來,“我原想著,沒了親娘,總要有個替遞紗扇,蓋蓋頭的人……沒想到是我充人形,忘了分寸。”
江珩忽然又有些不落忍了,蹙眉道:“好好的,你哭什麼。”
柳氏低下頭,抬起袖子掖了掖眼睛,眼眶里還含著淚水,臉上卻掛起了一個委曲求全的笑,嗐了聲道:“正是的,小娘子婚,既然還愿意認郎主這個爹爹,那也是樁好事,我有什麼可哭的呢……”說著又落下淚來,囁嚅著,“我只是心疼郎主,自己的兒出閣,竟要在人家府上辦喜事,弄得寄人籬下一般。”
這短短兩句話,確實又中了江珩的心事。
誰能知道表面上歡歡喜喜地聲稱合辦,背后飽含了無盡的委屈。兒是他的骨,魏國公也是江家正經的郎子,他舒國公算個什麼,如今竟賽過了自己這個親爹。江家一口飯一口湯地把孩子養到這麼大,難道還不及向家夫婦這一個多月的噓寒問暖嗎?
可世上的事偏偏這麼古怪,親爹錯不得半點,否則就有人站在公親的立場上口誅筆伐你,讓你淪為上京的笑談。
現在還有誰心疼他呢,無非煙橋一個罷了。
江珩忽然下了心腸,手替了眼淚,“好了,你的心我知道,可事已至此,沒有旁的辦法,只有屈就這一回,才能保全面了。”
柳氏順地點了點頭,在他旁坐了下來。
略一思量,又問:“那小娘子的妝奩,郎主打算怎麼料理?”
江珩長出了口氣,“不過盡我所能吧。先前東昌郡公家的聘金上頭再添置一些,湊上個兩千兩,送去也就是了。”
柳氏聽了有些為難,猶豫了下才道:“東昌郡公的聘金是五百兩白銀,并黃金二十兩,折算到一起,也還有千把兩的空缺呢。眼下家里進項有限,除了莊上的收,就指著鋪面的租子。早前君在時,上房一個吃醉了酒的嬤嬤曾說過,府里一年能得兩三千兩進項,竟不知怎麼,君走后只剩下了七八百兩……”
話沒有說,但江珩已經聽出來了,“你是說縣主離世前,把那些看不見的產業全給了巳巳?”
“唉……”柳氏蹙著眉笑了笑,“君思慮得很周全,畢竟兒是要嫁出去的,又不好掌娘家的權,君的東西不給小娘子,難道還給覓兒嗎。”見江珩恍惚,借機又道,“其實當日得知小娘子還活著,偏不去找你,我心里就明白是怎麼回事了,左不過翅膀了,離了家也能活。那舒國公和夫人做什麼一心維護小娘子?還不是瞧著小娘子手里有那些產業嗎!”
這麼一說,又好像有些道理,以江珩的認識,明夫人只見過巳巳幾回而已,怎麼就生出這樣匪夷所思的護犢之來,如今想來恍然大悟,世上果真沒有無緣無故的。
然而事已至此,終究沒有辦法,怪自己教無方吧。
他垂下了腦袋,柳氏見狀便道:“咱們肚子里明白就了,小娘子總是郎主的兒,郎主也不必因這個煩惱。眼下要給小娘子添妝奩,依我說,盡了咱們的意思就行了。雪畔的年紀不小了,過上一年半載得議親,還有雨畔和覓兒,眼見著都長起來……年下又要搬府上京……細想想要花費的地方多了,郎主哪里知道我的難。”
反正就是當家當出了一的功勞,好比巧婦做出了無米之炊,開國侯府能支撐到今日,全賴省吃儉用善于經營。
江珩這才想起,上回快馬加鞭趕到家,他們娘四個中晌吃白粥,當時沒覺得什麼,現在想來竟是因為節儉?好好的一個公侯府邸,何至于弄這樣!
可惜不當家的人,問了賬也是一頭霧水,他忖了忖道:“不拘怎麼,先把這件事辦妥要。我已經想好了,將宕山的鋪面和上京那個別業賣了,作籌建府邸之用,七拼八湊的也差不多了。”
柳氏道是,半晌咬了咬試探道:“那小娘子的嫁妝,就籌個一千兩吧!剩下再拿二三百兩置辦些床褥用什麼的,又喜興,看著排場又大,打發人從我們這里浩浩運送出去,也好讓幽州的人瞧瞧,堵住他們的。”
江珩覺得倒也可行,便頷首,“就這麼辦吧,快些預備起來,只剩十來日了。”
柳氏應了聲是,“我想著,還是通知姑母們一聲吧,畢竟小娘子是郎主的嫡長,姑母們也一直將放在心上。且二妹妹府上恰好離幽州不遠,明年家換了坐朝的日子,也要隨彭郎子搬到上京去的。”
江珩不愿意料理那些瑣碎,站起隨意抬了下手指,便負手踱出去了。
柳氏看著他的背影,臉上悲苦的神一瞬褪盡,吩咐一旁侍立的孔嬤嬤道:“找牙郎來,把沉香發賣了。”
孔嬤嬤有些疑,“姨娘是怕這丫頭不嚴?”
“終究是云畔屋子里的人,雖調理得聽了我的話,年下搬到上京后,萬一云畔要追究地那天的事,只要拿住了沉香說出實,這事就穿幫了。”柳氏喃喃說,“還是發賣了吧,就說了房里的東西,賣得遠遠的,這輩子最好不得上京,這事就沒個對證了。”
至于那兩人送到莊子上的婆子,當日就算知道死的是木香,時隔幾月無憑無據也說不清。算來算去只有沉香一個患,只要把料理妥當,搬到上京也不必懸心。
***
江珩一連在家休息了三日,第四日要返回上京,柳氏把該預備的陪嫁都預備起來,拿大紅大綠的綢帶捆綁上,裝了滿滿六車,就停在府門前的直道上。
這回也跟著往上京去,不是去登舒國公府的門,是去江珩二妹妹的府上。經營了這些年,和這兩位小姑子深得很,江奉珠和江奉玉比起那位高高在上的縣主嫂子來,和反倒更親厚。
馬車搖晃著,從清晨走到下半晌,這回不必負荊請罪,因此也不覺得燥熱。柳氏坐在車,還有閑心挑起窗上簾子,看一看外面曬得發白的道和遠的群山。
江奉玉嫁在距離上京十來里的貫口,郎子是東上閤門副使彭盛,從七品的小,掌文武員及外使朝見引導事宜。婆家家世式微,男人進項也有限,住著以前還算面的老宅子,潦草置了房妾室,闔家上下只有四五個仆婦小廝伺候,上頭還有一位常年臥床的婆母,因此江奉玉每次來幽州走親戚,柳氏總會預備些布料香料之類的,不空手而回。
人嘛,就是這樣一次次細微積累的。當家主母不屑于結的人,去結,當家主母不屑于干的事,去干,總會拉攏些相投的人,將來要時候可堪一用。
頂著烈日走了好幾十里,因車上裝著嫁妝不好策馬,只能放緩速度前行。江珩起先還撐傘,無奈薄薄的兩層油紙擋不住滾燙的熱流,走了一程便躲到車里暫歇了。
太將要落山的時候,車隊終于抵達貫口,便在岔路上分了道。
柳氏乘坐的車馬了市集,一直循著街道往前走,彭家就在直道盡頭。因提前打發了小廝過去傳了話,彭夫人早就在門上等著了,見柳氏的車到了門前,笑著上來迎接,客客氣氣了聲“小嫂”。
本來一般的姨娘,哪里當得一聲“嫂”,到底多年的籠絡不是平白丟進水里的,漁縣主稱“長嫂”,柳氏便掙了兩位小姑一個“小嫂”的稱。
彭夫人雙手來攙扶,柳氏借著的力走下了馬車,一頭親親熱熱問好,一頭轉向隨行的婆子招了招手。
婆子捧著兩匹上好的折枝五瓣花緞子到了面前,柳氏含笑說:“這是幽州新出的花樣,我特意帶了來,給二妹妹添兩件裳穿。”
彭夫人寵若驚,瞧了瞧那緞子,赧然笑著,“總小嫂這麼破費,我又不能為你做什麼,真是怪不好意思的。”一面說著,一面將人引進了門。
猜你喜歡
-
完結1979 章

萌寶在上:邪魅王爺追妻忙
穿越成廢物如何?咱未婚先孕有個天才萌寶罩!不知道孩子他爹是誰又如何?咱母子聲名鵲起還怕冇人倒插門?萌寶:孃親,神獸給你牽來了!天材地寶給你搶來了!漂亮的男人給你帶來了!某女嫌棄:無錢無勢無實力,不要!某隻妖孽邪笑:錢財任你揮霍,大陸任你橫走,夠冇?母子兩人對視:美男在手,天下我有!成交!
177.5萬字8 130419 -
完結5533 章

冷王邪妃太逆天
救人一世,儘落個滿門抄斬,再世為人,她要逆天改命,毒禍天下!獲神劍,契神獸,修神訣,煉天下神器!欺我者亡!虐我者死!誅我全家之人,讓你連活都冇有可能!再活一世,就是這樣猖狂!他是世上最冷漠的九爺,戰場見到他的人,都已經死了,人送“活閻王”。本以為他是最無情的九王爺,卻變成了自己夜夜變狼的大師兄!“小師妹,我可以罩你一生!”“大師兄,我可以毒你全家!”“太好了!小師妹,我們一起雙修禍害全天下!”雙煞合併,天下誰人不抖!
363.3萬字8 119518 -
完結37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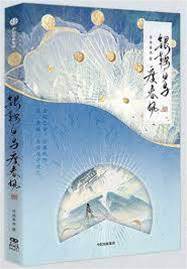
銀鞍白馬度春風
君主剛愎自用,昏庸無能,掩蓋在長安錦繡繁華之下的,是外戚當權,蟻蛀堤穴。 賢仁的太子備受猜忌,腐蠹之輩禍亂朝綱。身爲一國公主,受萬民奉養,亦可濟世救民,也當整頓朝綱。 世人只掃門前雪,我顧他人瓦上霜。這是一個公主奮鬥的故事,也是一羣少年奮鬥的故事。 ** 你該知道,她若掌皇權,與你便再無可能。 我知道。 你就不會,心有不甘嗎? 無妨,待我助她成一世功業,他日史書之上,我們的名字必相去不遠。如此,也算相守了。
55.4萬字8 187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