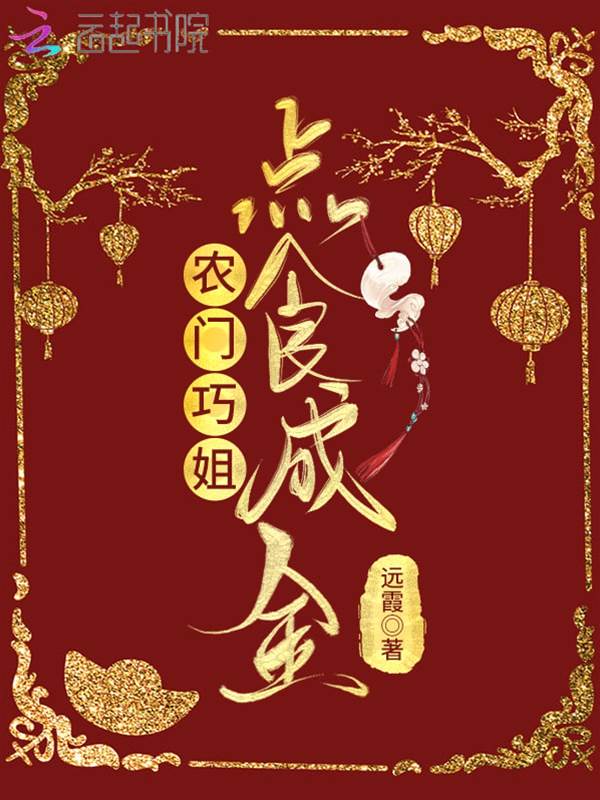《凰權至上》 第254章 試探
京郊的一民宅里,魏明華做了一副民的打扮,頭上戴著一方藍底黃花的頭巾,上是一件薑黃土布做的短衫和長,面塗得蠟黃,眉加,一副缺短食的模樣。
魏明華這裝扮走在大街上,路人大概連一個眼神都不會給。
天漸漸暗了下來,眼看著就宵,院門被人從外面推開。
喬裝打扮的太子帶著護衛走進這座二進的院落。
「堂姐明知道孤不便出宮,還要把會面的地點選在京郊,這就是堂姐的誠意嗎?」
魏津俊的面龐上掛著一抹冷笑,一副冷言冷語的不耐之。
通過這幾次短暫的鋒,魏明華早就看出來,眼前的太子就是一個厲荏的草包,心中不免起了幾分輕視之意。
嗤笑:「太子殿下若是覺得我沒有誠意,又何必前來赴約呢?」
「你以為孤真的拿你沒有辦法?」魏津眉宇間閃過一道戾。
「郝七!」伴隨著魏津的一聲斷喝,他後站著的侍衛上前一步,「錚」的一聲長刀出鞘,轉瞬手起刀落……
鮮飛濺。魏明華獃滯地看著桌上面的一截斷手。半晌,嚨里發出一聲尖:「啊!」
凄厲的喊聲劃破天際,在深夜裡顯得格外瘮人。
院子里的暗衛破門而,全都擁進了屋子裡,雙方人馬呈對峙之勢,分別站在各自主子的後。
「疼,我好疼!我的手……」
魏明華痛的臉發白,豆大的汗珠從的額頭上滾落,混著瘋狂湧出的眼淚和鼻涕,沖花了可以偽裝出來的妝容。
「你敢對我手!我要殺了你!」
魏明華看著魏津的目,像是一頭暴怒的母豹子,那是將一個人恨毒了的眼神,恨不得將魏津碎萬段。
「郡主,快讓陳太醫看看您的手。」
站在魏明華後的護衛右手按在劍鞘上,虎視眈眈地盯著魏津一行人。
魏津勾了勾,淡淡道:「皇姐,孤希你能夠認清事實。現在是你們需要孤,而不是孤一定要跟你們合作。」
「魏津,是我小瞧了你!」
魏明華的斷口被陳太醫撒上了金瘡葯,疼地「嘶」了一聲,整個五都扭曲在一起,看上去異常猙獰。
「堂姐,孤勸你最好放尊重一些。」魏津嫌惡地看了一眼桌上的斷手,吩咐郝七:「把這礙眼的東西移開,孤看了就倒盡胃口!」
「太子殿下不要欺人太甚!」魏明華後的侍衛朝著魏津怒目而視。
魏明華的傷口已經被包紮好了。就在剛剛,失去了一隻手,除了最初的尖和失態,魏明華除了面過於慘白了一些,一雙秀的眼睛平靜無波,彷彿剛剛經歷了斷手之痛的人不是。
「是我冒犯了。還請太子殿下大人不記小人過。」魏明華放低了段,睫微垂,語氣恭敬了許多。
魏津說的沒錯。他已經是儲君了,隨時都可以而退。但自己不一樣。費心籌謀了整整八年,眼下就是最好的時機,魏明華連魚死網破的勇氣都沒有。
更何況,魏明華已經為自己的「輕敵」付出了代價,將永遠失去自己的左手,從此之後,左腕只剩下一個平整的斷口!
魏明華如何甘心就這樣放棄!
早晚有一天,會將魏津千刀萬剮,以還今日之辱。
魏明華的能屈能讓魏津勾了勾薄,他的目里流出幾分譏諷,意味深長地說道:「識時務者為俊傑,堂姐若是早點認清自己的位置,也不會這皮之苦了。」
聞言,魏明華差點咬碎了銀牙。斷口的疼痛更是讓魏明華差點昏過去。
狠心咬了下舌尖,刻意忽略到魏昭語氣里的譏諷,朝著屋裡喚了一聲:「聶先生,請您現吧。」
與花廳隔著一道簾子的室里走出來一位年逾花甲的老者,看到魏明華的傷口,老者嘆息了一聲,目里難掩心疼:「郡主了傷,還是儘快歇息為好,這裡有老夫在。」
「聶先生,我就先告退了。」
魏明華不想讓聶老看到自己的狼狽,朝著聶老先生福一禮,起向太子時,眼神涼淡至極:「太子殿下,告辭。」
魏明華走出屋子,因為劇痛而變得十分混沌的大腦頓時一陣恍惚,再也撐不下去了,向後一倒,被後的侍衛眼疾手快地扶住,將打橫抱在懷裡。
「郡主,屬下冒犯了。」
男人在花廳里的時候,聲音低啞,可是出了正屋之後,男子不再掩飾,嗓音里著些詭異的尖利和低。
魏明華已經痛極,眼淚完全不控制,不斷地從眼眶裡滾落,可是的目卻平靜至極。
「阿軒,當初你為了陪我進宮,在凈事房……是不是比我現在還要痛?」
驟然被魏明華道出了自己最不想提及的往事,男人的一瞬間變得繃,瞬息之後,他更加用力地抱了懷裡的人,搖了搖頭。
……
房間裡頭,聶老坐在魏津的對面,不聲地打量著面前的男子。
這位太子殿下有著一副十分俊的容貌,氣質溫潤儒雅,僅僅是坐在他對面,便有一如沐春風之。
誰能想到,就是眼前的人,就在剛才,面不改地讓後的侍衛砍下了自己堂姐的手。
果然。皇室中人,無論聰明還是愚蠢,全都一脈相承的心狠。
「這位便是大名鼎鼎的聶老先生?」魏津拿起從東宮帶過來的茶,自己給自己斟茶,放在邊啜了一口。
魏津對魏明華沒有半分的信任,本不會這個宅院里的任何一樣東西。
倒是聶老先生看了魏津的這番作為,揚了揚,意有所指地說道:「太子殿下是不是太過小心了?我們可沒有對盟友捅刀子的習慣。」
「小心駛得萬年船。聶老可是多智近妖的人。孤若不謹慎一些,只怕孤就是第二個扶南王。」魏津對著聶老先生出一抹意味深長的笑容。
聶老先生聞言,眼睛微瞇,淡淡說道:「太子殿下的消息倒是靈通。」
「孤那位堂姐渾上下都是心眼,孤又豈能毫不設防。查出聶老先生的份,對孤來說,倒是意外之喜了。」
魏津像是沒有聽出聶老先生的譏諷,慢條斯理地說道。
聶老先生為了儘早京,服下了虎狼之葯,原本還有半年的壽命,如今只能再撐上一個月。
自從服藥之後,聶老先生很久都沒有再咳嗽了,眼下聽了魏津的話,聶老先生只覺嚨一陣發,心知這是牽了心肺的緣故。
這位太子殿下看著就不是個聰明的,他是從哪裡得來的消息呢?
聶老先生收拾了一下心,說道:「太子殿下,你我今夜來此,想必都是帶著誠意前來的。與其互相攻訐,不如省下時間,早些商討出大計。」
魏津轉了轉茶盞,角勾起一抹十分涼薄的笑容,他深深地看了聶老先生一眼,緩緩道:「聶老先生快言快語,不妨跟孤個底。此次宮變,聶老先生手下能有多人?」
「拜當今所賜,我們這些舊臣,早就被今上殺的七七八八了。至於這次起事的人手,自然要以太子殿下馬首是瞻,只要太子殿下一聲令下,我們定會傾力配合。」
聶老先生不疾不徐地說道。
魏津的神頓時變得極其難看。
自家人知道自家事。
魏津手底下只有兩萬金吾衛,再加上前日策反的一個副將,撐死了也就三萬人。剩下的宮衛可是足足有七萬。
這位聶老張口就給自己畫了一張大餅,說什麼傾力配合,卻連底細都不肯,這是想要坐收漁翁之利,也要看自己肯不肯答應。
「聶老先生的如意算盤打得也太了,孤堂堂太子,給你們這些逆臣來做馬前卒,聶老先生還真是自視甚高。」
魏津毫不留的譏諷道。
聶老先生原本不打算跟魏津對上。這位太子殿下可不像顧全大局的人。
可是太子言辭間,竟然將他們這些忠臣打了臣賊子,事關名譽,聶老先生豈能坐視不理。
「太子殿下此言差矣。您的父皇得位不正,元太子才是先帝指定的繼承人。」
聶老先生據理力爭道。
聞言,魏津了眼皮,諷刺道:「聶老先生難道連自知之明都沒有嗎?元之一字,乃是元嫡,元長,意指嫡長子。戾太子只是一個區區庶子,還是不要玷污這個元字了。」
魏津雖然決心和戾太子的舊部合作,反的還是自己的父皇,可是他卻不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父皇清名被污。
若是父皇得位不正,那自己這個太子豈不是更加「名不正、言不順」,所以,魏津當即反駁了回去。
聶老先生沒有想到魏津的口舌這樣鋒利,只覺間一哽,辯解的話全部被堵在了臆中,憋的難。
當今陛下的確是先帝的嫡子,而元太子卻是庶子承位,這一點,連聶老先生都無法幫自己的舊主洗白。
「聶老先生既然默認了,我們是不是該談正事了?孤耐心有限。聶老先生最好想好了再開口。」
魏津慢條斯理地說道。
「我這裡,只有五千人。」聶老先生在心中暗自斟酌了一番,最終說道。
聞言,魏津握著茶盞的手指倏然間攥,因為用力,骨節都發白了。
到了這個時候,面前的人還不說實話。
魏津摔碎了手裡的茶盞。
瓷片飛濺。他冷笑:「既然聶老先生不肯拿出誠意來,恕孤耐心有限,不奉陪了。」
魏津起,朝著後的護衛揮了揮手,大步流星地往院子里走去。
猜你喜歡
-
完結1620 章

神醫娘親她又美又颯
九千歲獨孤鶩因疾被迫娶退婚女鳳白泠,滿朝轟動。 皇子們紛紛前來「恭賀」 : 鳳白泠雖貌丑無能又家道中落,可她不懼你克妻不舉之名,還順帶讓你當了便宜爹, 可喜可賀。 獨孤鶩想想無才無貌無德的某女,冷冷一句:一年之後,必休妻。 一年後,獨孤鶩包下天下最大的酒樓,呼朋喚友,準備和離。 哪知酒樓老闆直接免費三天,說是要歡慶離婚, 正和各路豪強稱兄道弟的第一美女打了個酒嗝:「你們以為我圖他的身子,我是饞他的帝王氣運」 九千歲被休后, 第一月,滿城疫病橫行,醫佛現世,竟是鳳白泠。 第二月, 全國飢荒遍地,首富賑災,又是鳳白泠。 第三月,九朝聯軍圍城,萬獸禦敵,還是鳳白泠。 第某個月,九千歲追妻踏遍九州八荒:祖宗,求入贅。 兩小萌神齊聲:父王,你得排號!
284.6萬字8.18 32474 -
完結4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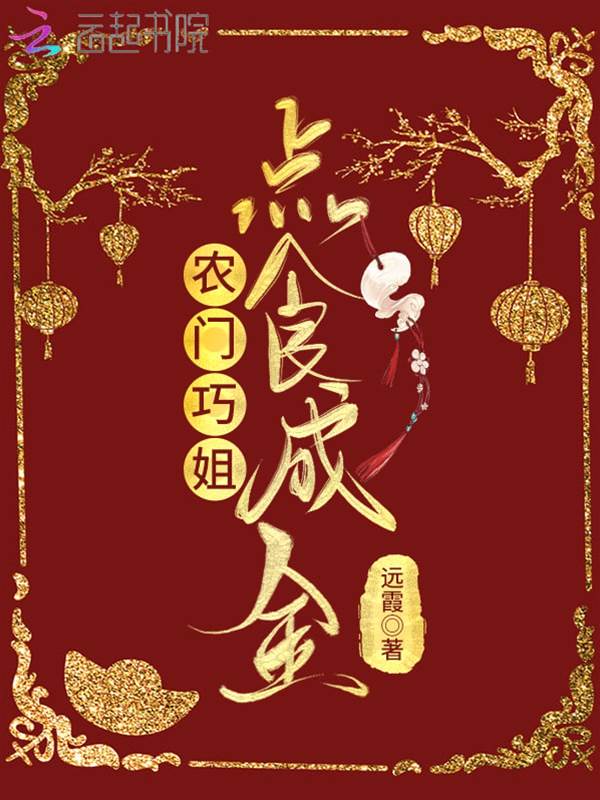
農門巧姐點食成金
高級點心師意外穿成13歲彪悍小農女-包蓉。後奶惡毒,親爺成了後爺。,爹娘軟弱可欺,弟弟幼小,包蓉擼起袖子,極品欺上門,一個字:虐!家裏窮,一個字:幹!爹娘軟弱慢慢調教,終有一天會變肉餡大包,弟弟聰明,那就好好讀書考科舉,以後給姐當靠山,至於經常帶著禮物上門的貴公子,嗯,這條粗大腿當然得抱緊了,她想要把事業做強做大,沒有靠山可不行,沒有銀子,她有做點心的手藝,無論是粗糧、雜糧、還是精糧,隻要經過她的手,那就都是寶。從此,包蓉銀子、鋪子全都有,外加一個自己送上門的親王夫君,氣得後奶一概極品直跳腳,卻拿她無可奈何。
77.6萬字8 33875 -
完結506 章

爺快跪下,夫人又來退親了
中醫世家的天才女醫生一朝穿越,成了左相府最不受寵的庶女。 她小娘早逝,嫡母苛待,受盡長姐欺負不說,還要和下人丫鬟同吃同住。 路只有一條,晏梨只能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鬥嫡母踹長姐,只是這個便宜未婚夫卻怎麼甩都甩不掉。 “你不是說我的臉每一處長得都讓你倒胃口?” 某人雲淡風輕,「胃口是會變的」。 “ ”我臉皮比城牆還厚?” 某人面不改色,「其實我說的是我自己,你若不信,不如親自量量? “ ”寧願娶條狗也不娶我?” 某人再也繃不住,將晏梨壓在牆上,湊近她,“當時有眼不識娘子,別記仇了行不行? 晏梨笑著眯眼,一腳踢過去。 抱歉,得罪過她的人,都拿小本記著呢,有仇必報!
90.4萬字8 2908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