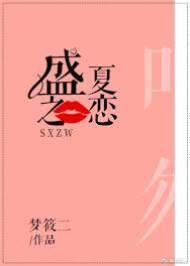《上癮》 [上癮] - 第 72 章
偏廳的佈置很淡雅舒適,平時姜奈在謝家養胎,經常過來小坐片刻,久而久之,管家就主把沙發墊換厚的,那些瓶瓶碎碎的擺件收起,連照明的燈都變不刺眼的暖黃。
夜很深,姜奈枕着男人的膝蓋上,一頭烏黑的秀髮四散開,襯着臉頰的廓有種模糊的。謝闌深的心思,不在電視機那幾只豬上,他偶爾低頭,用修長的手指穿過髮,挲幾許白瑩的耳垂,又緻小巧,看着細微卷的眼睫輕抖了下。
姜奈去握他手指,微微擡頭說:“老公……我想把頭髮剪了。”
手比劃了個位置,想剪到肩膀過,詢問他:“這樣會不會很醜?”
謝闌深端詳的臉,突然落下一吻,力度都是輕的:“不會,你怎麼樣都好看。”
姜奈沒有剪過短髮,是猶豫了好些天的,見謝闌深這樣說,開心了起來,無比信任他:“那幫我剪頭髮吧。”
謝闌深問:“你確定?”
“我可是第一次留短髮。”姜奈從沙發爬起來,又擡手圈住他的脖子,聲音很好聽,的,骨:“在我心裏,我家謝公子是無所不能的,是天底下最厲害的男人。”
“我自然是最厲害的。”
這點上,謝闌深當仁不讓,輕易就被的甜言語哄住,又思忖幾秒問:“有沒有圖片參考下?”
姜奈笑倒在他懷裏,還真去找手機,從網上翻了張圖給他。
夫妻倆琢磨了半會,謝闌深把放在沙發上,起去找剪髮的工。
大晚上的突然找這個,使得管家都出了,看着謝闌深站在桌前,形依舊是高,在謝家的緣故,他換下了正裝的西服,只穿着休閒上長,米白系列的,會顯得整個人愈加的溫和無害。
或許,也是因爲即將爲父親的緣故,連斂藏鋒的眉骨間沉澱了下來,不見冷。
有一點連管家也不得不再次承認,娶妻生子後的家主,比以前,更有人味了。
謝闌深挑了把白順手的剪刀工,一邊,拿手機翻閱着剪髮的教程,用了十分鐘反覆的學習。等他折回偏廳時,發現才這會功夫,姜奈已經蜷了一團在角落裏睡着了。
電視機的畫片尚未結束,捲翹的眼睫閉,在臉蛋落下一排漂亮影。
連男人的腳步聲靠近,都沒有把給驚醒。
懷孕前,姜奈淺眠容易醒來,夜裏在邊的話,反而不能弄出多大聲響。
但是自從懷孕後,就瘋狂瞌睡,不睡死過去。
謝闌深將剪髮的工放在一旁,落座於旁邊,深暗的眸先是注視了許久,呼吸過於的淺淡,幾乎是聽不見,半響後,微微彎起指節,在鼻息下停留了幾秒。
不自覺中,他的背部竟然有了一層薄汗,險些染溼了襯的面料。
謝闌深不聲收回手,薄脣似在嘲笑自己大驚小怪,長指重重了眉骨幾下。
管家端了杯茶過來,看到這幕,又顧及姜奈在睡覺,低聲道:“人懷孕的力會大不如從前,夫人瞌睡是正常的,家主勿擔憂。”
謝闌深長指接過茶,遞到薄脣極淡的抿了口,潤,並沒有說話。
擔心姜奈的狀況,是出於本能反應,饒是旁人怎麼解釋,還是無法抵消。
管家站了會,等電視機的畫片終於播放結束,才低聲說:“二公子回來了。”
謝闌深眼皮子都沒掀起,沒多大關注。
謝臨如今安分許多,也沒有再敢去招惹尤意,也不知是不待見姜奈,還是知道自己在謝家不招待見。隔三差五的出去遊戲人間,好幾天不見蹤影,半夜回來一趟,可能天不亮就走了。
只要謝臨沒鬧出什麼事,謝闌深都懶得去管這個同父異母的弟弟。
管家還說:“小小姐之前說出門半個月,到現在還沒回來……聽說是留在了鄔鎮。”
鄔鎮是裴賜的老家,他的養父母如今還居住在那邊,而謝闌夕說出門散心,卻留在那裏一直未歸,管家將這事告訴謝闌深,提醒他:“要不要派人去將小小姐帶回來?”
在謝闌深眼裏,裴賜是謝家的提線木偶,被用來榨剝削的工人,他的價值,是給當年謝闌夕解悶用的。
要能哄得住謝闌夕開心,也不吝嗇給予他一點小恩小惠。
當謝闌夕不想要裴賜的時候,謝闌深自是不會管什麼分,直接無地將他踢出局。
換句話說,整個豪門上流圈裏,妹妹看中哪個男人,他總有辦法弄回謝家的。
所以裴賜當初鬧出醜聞,在謝闌深眼裏不值一提,隨時可以換個更乖、更聽話的上位。如今謝闌夕待在鄔鎮不回謝家,他只是淡淡皺眉了下,薄脣扯道:“你給打個電話,說哥哥回。”
管家聽從吩咐點頭,眼角餘將姜奈慢慢轉醒來,便識趣沒有在偏廳繼續停留。
沙發上,姜奈還沒睜開眼,指尖先憑藉着本能,去索到了謝闌深的襯鈕釦,勾着,聲音在深夜裏着模糊意味:“你要誰回?”
謝闌深將抱起,手掌沿着肩膀落到了背部,跟抱小孩一樣,淡淡說了句:“兮兮”。隨後,薄脣着的髮,呼吸着溫淡的熱氣:“還要剪頭髮麼?”
姜奈差不多睡清醒了,重重點點腦袋:“要。”
-
管家的這通催回家的電話,當晚就撥打過去了。
謝闌夕接到前,正待在小巷院子的二樓上,坐在窗邊的地方,外面夜跟潑了濃墨似的,連路燈都沒有幾盞,格外的靜。
過了會,手心託着腮,認真地打量起了院子外牆面上,爬滿的不知名綠植。
樓下的廚房裏,裴賜的表嫂幾人,正忙着洗碗收拾。
而不會做家務,想手,也未必會讓做。
所以只能在這兒發呆,在夜深人靜時,難免會想點事。謝闌夕想到了半個月前,來這裏的原因。
不是想來的,是裴賜的養母查出了癌症,晚期,打電話來的。
當初在學校的時候,謝闌夕就很清楚裴賜的家庭況,他是孤兒,被鄔鎮生活清貧的養父母養長大,沒什麼錢,從小讀書靠的是學校給的獎學金,連住的都是破舊的老房子了。
結婚時,想請裴賜的養父母搬到泗城居住,結果卻被兩個老人家婉拒,稱是住慣了小地方,大半輩子的親戚都在鄔鎮,要是去了大城市,反倒是不知道該怎麼生活。
裴賜並沒有強迫養父母,每個月都會給一筆生活費,給他們養老。
後來,裴賜的養父母坐着綠皮火車,來泗城找過一次。
謝闌夕在謝家自小就寵,什麼奇珍異寶,山珍海味,都是見慣喫慣的,沒覺得什麼稀奇。當看到裴賜的養父母扛着大包小包,將洗淨封好的土,土蛋掏出來給,那雙皺紋很深的老手,又微抖着給遞了一張存摺時。
那刻,心間是被到……
裴賜從讀書開始寄回家的錢,以及這些年拿回家的。
他的養父母一分錢都沒捨得花,都存在了這張薄薄發黃的存摺裏。
那時,兩個老人家坐在高檔的包廂裏,很不自在,如同針扎,連水都顧不得喝幾口,尷尬笑着對謝闌夕說:“小賜從小就是很努力的孩子……他是要留在大城市的,我們年紀大了,就不麻煩他了,留在鄔鎮養老好的……夕夕,我們不是文化人,漂亮的場面話不知道該怎麼說,這存摺,你就收着吧,當是我和你老姨的一點心意了。”
謝闌夕堅持不收,都沒盡到做兒媳婦的責,又怎麼敢拿這些。
但是兩個老人家一再堅持,後來將存摺給了裴賜,讓他給。
說是裴家娶媳婦的聘禮,錢不多,卻是一份心意。
不能白白虧待了。
再後來,裴賜的養父母就沒有來過泗城了,而因爲坐椅的緣故,平時連大門都不出。
每次裴賜獨自回鄔鎮看養父母,又回來時,都會提一大包的土特產,和蛋是必須有的,說是給補的。
漸漸地,謝闌夕覺到兩個老人家對自己的好,對們,也是有了。
這些年過來了,裴賜老家的土蛋,都是給謝闌夕喫掉的。
……
離婚時,裴賜的養父母並不知,兩個老人家也很看新聞上說什麼。
一年多過去了,要不是接到了鄔鎮的電話,謝闌夕都不知道裴賜是沒有跟家裏坦白的。當初錯過了最好的時機。如今養母檢查出癌症晚期,時日不多,年紀大又不住打擊,就不便說清楚了。
所以,來到鄔鎮,只能以兒媳婦的份過來。
和裴賜裝了快半個月的表面假夫妻了,人前,和他依舊,只有私下的時候,纔回到最真實狀態。
謝闌夕看着夜想,吃了人家這麼多的土蛋。
就像哥哥曾經一句戲言那樣:
早晚是要還的。
猜你喜歡
-
完結2295 章

都市至尊聖醫
一代武神葉修,靈魂重歸故鄉, 歸來時,重生日,兩世仇人,以牙還牙! 上一世,他慘遭綠茶未婚妻殘害,含恨而死。 這一世,守護親人,登頂神位! 逆天功法,至尊寶具,最強修為,唾手可得! 縱橫逆天霸血,登上至尊神座。 葉修微微一笑,“有些人血中有風,注定要漂泊一生······”
427.2萬字8 35916 -
連載1087 章

財閥小千金:老公,我吃定你了
首富唯一繼承人還需要聯姻?還是嫁給穆樂樂的死對頭?! 穆樂樂不舍得氣死爺爺,但舍得氣死老公! “總裁,太太新婚夜去酒吧。” 晏習帛:“卡停了。” “總裁,太太準備給你帶綠帽子。” 晏習帛:“腿砍了。” “總裁,太太準備和你離婚。” 辦公室一瞬間的沉默,晏習帛問:“她想懷四胎了?” 最初,穆樂樂用盡了各種辦法想離婚,后來,她在追逐離婚的道路上,逐漸迷失了自己。 本以為,穆家半路撿來的孤兒包藏禍心,欲要獨霸穆式集團。后來才發現,他煞費苦心只為了她。 穆樂樂當初寧可相信...
185.9萬字8.18 24479 -
連載400 章

訂婚宴,陸總偷偷勾她尾指
[又名:訂婚宴,被前任小叔親到腿軟]、[京圈佛子強勢上位!]京圈太子爺陸野的未婚妻顧言驚豔、勾人、脾氣好,圈內皆知有陸野的地方必有顧言,某天,聽說顧言提了分手。陸野散漫,“說了她兩句重話,不出三天,她會自己回來。”三天又三天。陸野醉酒沒人接,忍不住撥了顧言號碼,竟然被拉黑了。有八卦拍到顧言被神秘男人送回家,陸野驀地心裏空了一塊。後來,聽說陸野不顧暴雨狼狽,偏執的在前女友家門口站了一夜。第二天,那扇門終於打開。“言言!我想你…”一抹頎長的身影裹著浴巾走來。“小叔?……言言?”那個驕矜尊高的男人攬顧言入懷,睨向陸野,“你該改口了。”—那晚,顧言把陸野的小叔給睡了,第二天她又怕又後悔,轉身就逃。她辭了工作,換了住處。電梯遇到他,她假裝等下一趟。直到她在酒吧與人相親,直接被人擄走。逼仄的小巷,沉重的氣息侵入,強吻,“再跑,腿打斷。”—他一步步誘她深陷,怎麼可能逃出他手掌心。
70.5萬字8.18 27891 -
完結17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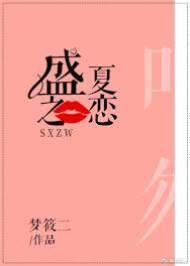
盛夏之戀
那天,任彥東生日派對。 包間外走廊上,發小勸任彥東:“及時回頭吧,別再傷害盛夏,就因為她名字有個夏沐的夏,你就跟她在一起了?” 任彥東覷他一眼,嫌他聒噪,便說了句:“煙都堵不住你嘴。” 發小無意間側臉,懵了。 盛夏手里拿著項目合同,來找任彥東。 任彥東轉身,就跟盛夏的目光對上。 盛夏緩了緩,走過去,依舊保持著驕傲的微笑,不過稱呼改成,“任總,就看在您把我當夏沐替身的份上,您就爽快點,把合同簽給我。” 任彥東望著她的眼,“沒把你當替身,還怎麼簽給你?” 他把杯中紅酒一飲而盡,抬步離開。 后來,盛夏說:我信你沒把我當替身,只當女朋友,簽給我吧。 任彥東看都沒看她,根本就不接茬。 再后來,為了這份原本板上釘釘的合同,盛夏把團隊里的人都得罪了,任彥東還是沒松口。 再再后來,盛夏問他:在分手和簽合同之間,你選哪個? 任彥東:前者。 那份合同,最終任彥東也沒有簽給盛夏,后來和結婚證一起,一直放在保險柜。 那年,盛夏,不是誰的替身,只是他的她。
25.4萬字8.18 761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