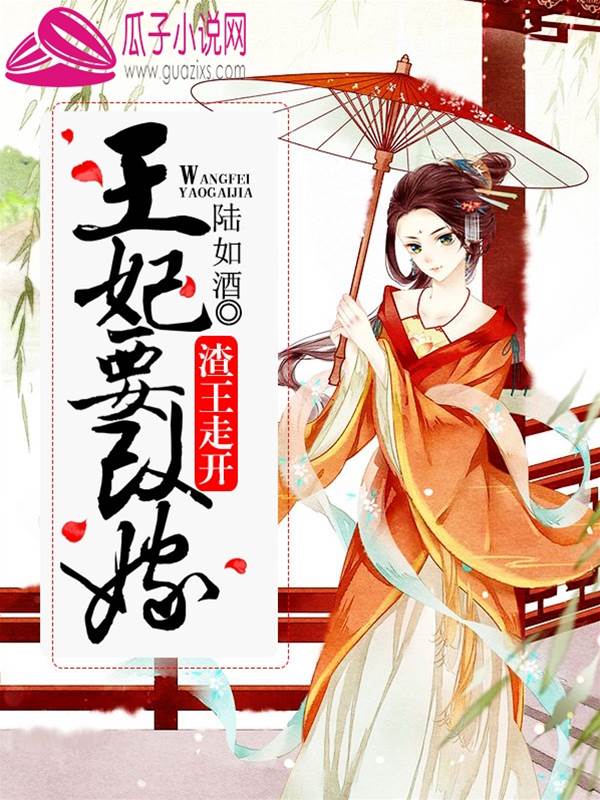《締婚》 第49章 第 49 章
茶館。
譚建正替自家大哥發愁,反覆看著門前,大哥還沒有將大嫂找回來的跡象,而街道卻越發了。
譚建多半的時間都在清崡,清崡有譚氏坐鎮,他從沒見過這般混場景,但這些日出了清崡,見到的混越來越多了。
世道的艱辛一直都在,只是太平的年景如織了一場夢一般將人蒙蔽,卻在人夢醒之後,訇然發。
譚建嘆氣,看向縣衙。
「縣衙是怎麼回事?難道知縣不在?!」
譚家的人將縣衙門前的鼓敲了一邊又一邊,裏面就像是空了一樣,一點靜都沒有。
還是楊蓁冷哼了一聲。
「狗指不定跑路了!」
縣城大,知縣還跑了路,這等混場面什麼時候才能停止?
恐怕不僅不會停止,還會引來周邊的匪賊強盜......
然而就在這個時候,有人忽然喊了一聲。
「縣衙前來人了!」
茶館里的眾人急急向縣衙看了過去,譚建一眼就看到了騎在高頭大馬上的自家大哥。
只見大哥一個眼神過去,蕭觀拎了個乾癟老頭出來,老頭踉蹌地趴在縣衙門上。
「快開門,本、本回來了!」
那老頭竟就是本地的知縣!
縣衙大門一開,譚建就帶著茶館眾人轉移了過去。
他急忙奔去,一眼就看見那乾癟知縣一平民百姓的打扮,恨不能就這麼混在人群里逃竄出去。
太平日子他作威作福,到了之時竟就敢這麼跑路。
不等譚建上去,楊蓁就過去將那知縣質問了一通,只問得那小老頭說不出話來,哭喪著臉。
只是兩人卻發現,此只有自家大哥,嫂子並沒在。
「大嫂呢?」楊蓁不住問。
譚廷在這問話里眸一暗,眉頭下來。
蕭觀在旁小聲回了楊蓁,「......夫人還沒找到。」
「怎麼會這樣?」楊蓁和譚建訝然。
譚廷眸沉沉地看了一眼遠四起火的縣城,抿回看了那知縣一眼。
「把縣衙的人手都過來。」
知縣不敢違背,連忙讓人把兵都了過來。
然而知縣本人都要跑路,縣衙又有多兵?
知縣忍不住道,「只靠我們縣衙這些人,只怕也管不住外面的啊。」
譚廷冷哼了一聲。
若是起初開始的時候,知縣就聚攏人手出去管控,本不至於此。
而到了現在,這些人手確實不夠了。
他也沒指這些人能作什麼,只問了一句。
「離縣城最近的衛所是哪一個?」
知縣聽了,急忙回應,「是、是距縣城來回一個時辰的湖門千戶所。」
那湖門千戶所的千戶是個不好說話的人,平日給他禮尚往來都十分困難。
知縣在之就想去千戶所求助,但一想到那千戶與本地的馮薛兩族關係平平,甚至還有些不待見,就打消了念頭。
可他剛說完,就見那位清崡譚氏不知是何份的男子,問了一句。
「那千戶可是魏乾?」
知縣訝然,「是是,正是!」
他驚訝地看著眼前的男人,又見一旁的譚家二爺走上了前來。
「大哥認識那千戶?」
譚廷點頭,「譚氏與他有些。」
知縣更驚訝了,但沒等他弄明白這些清崡譚氏的人的份,就聽見那人直接差遣了縣衙里為數不多的差。
「五人一隊,上街巡邏,以鎮、趕走匪賊為要。」
他說完,還特特強調了一句,「不許打殺百姓。」
知縣不知道他到底是什麼路數,是向著庶族百姓,還是要替世族出頭。
他寡言語,知縣也不知道他到底怎麼想,只能吆喝著手下照做。
譚廷看了一眼被四火染紅的天空,又低聲吩咐了蕭觀派人與差一起組隊,繼續去尋找項宜的下落。
而他了譚建守好縣衙和眾人,剛要上馬帶人去千戶所請求支援,就見有馮薛兩家的人奔了過來,讓知縣派差支援他們。
「......那些暴民竟要燒了世家的宅子,就要攻破世族的門了!」
知縣素來與這兩家好,但此刻的縣衙已經不是他的了,他只能看向了譚廷。
譚廷又是一聲冷哼,一點要幫襯的意思也無。
「他們自己做的孽,讓他們自己著吧。」
這一句擲地有聲,知縣再不敢有任何違背。
而譚廷言罷直接翻上馬,帶上人手飛奔離去。
*
困在狹窄過道里的項宜等人,完全找不到出去的機會。
護衛趁著外面稍安,從路邊的攤子裏,取了被攤主棄下的燒餅,照著項宜的吩咐放了銀錢,拿給眾人吃。
眾人雖然都壞了,但外面幾乎了燒殺搶掠的修羅之地,誰都沒有心思吃喝。
府的人遲遲沒有現,項宜幾乎斷定那知縣跑了路了,只能留在此地繼續等待時機。
初春的北地甚是寒冷,眾人只能在一起,幸而此在高牆下面,算得一個避風之了。
四下湧起的火讓人算不清時辰。
就這樣又過了一陣子,項宜約約竟然聽見了差敲鑼的聲音。
護衛和喬荇們也都聽見了。
眾人神皆是一振,等著那差的鑼聲靠近,們就可以離開此地了。
不想就在這時,一旁被鎖起來的空院子裏好似有了靜。
眾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接著便聽到了隔壁傳過來的七八個男人的聲音。
這些男人自然不是那空院子的住戶,而是趁從城外跑進城中搶劫的強盜。
這幾個人在城中劫掠了一番,恰找了這個空院子做落腳地。
他們低聲議論的聲音,街道上的人聽不清,可避在一旁狹窄過道里的項宜他們,卻聽得一清二楚。
眾人除了護衛,便都是人孩子,當下聽見隔了一道牆的院子裏有七八個亡命之徒,皆驚得大氣都不敢。
項宜亦不安了起來,他們只等著差過來便能離開此地了,誰曾想竟遇到強盜。
然而下一瞬,忽然一個小孩在害怕發抖之中,踩到了一旁的枯枝。
枯枝發出噼啪一聲響,在寂靜的狹窄過道里,聲音似被無限放大了一般。
而隔壁空院子裏,強盜們低聲議論的聲音,驟然靜沒了影。
項宜心下一沉,再抬頭看去,只見那些亡命之徒極其警覺地從牆的另一邊翻了過來。
只是當他們看到這狹窄過道里,大多除了人就是孩子,那臉上的笑意都充滿了玩弄。
有兩個混不吝的,看著黃六娘主僕,直接調笑了起來。
「還有這等送上門來的好事?」
說話間徑直向黃六娘走了過去。
說時遲那時快,護衛騰的一下跳了出來。
「小人擋著他們,夫人和姑娘們快跑!」
項宜也深知再沒有旁的辦法了,跑上街或許還有生機,但留下來,誰都沒得好過。
在這一瞬間,一把拉開了通往街道的門。
「快跑!」
眾人呼啦一下從狹窄過道里跑了出去。
護衛拔劍與這些強盜抵擋起來。
但他到底勢單力薄,很快就抵擋不住了。
強盜們亡命天涯多年,怎麼能是吃素的,當下有幾個徑直越過侍衛,向著項宜他們追了過來。
「到了的可不能丟了!」
不過三下兩下的工夫,其中一人扯住了黃六娘,一人更是越到了項宜面前,生生擋住了項宜的去路。
「嘖嘖嘖,一個比一個漂亮,今晚可真是要了大福了。」
項宜驚詫後退,已經顧不得許多,連聲喊了起來。
然而方才明明在附近的差鑼聲,此刻竟不知到了何,連聲呼喊,卻沒有任何回應。
強盜都笑了起來。
「就算那些差來了,你覺得有用嗎?差若是有用,還能等到此時?」
言罷此人一探上前來,項宜驚詫躲閃,還真就躲開了那人的手。
但那強盜反而越發興起來,手下更是力道重了起來,一把抓住了項宜的肩頭。
項宜肩頭一痛。
說時遲那時快,忽然一破風之聲嗖的傳了過來。
那聲極快,又在下一瞬,驟然扎進了之中。
有滴濺了出來,在項宜瞪大眼睛的一瞬,落在了的鼻尖。
而方才抓著的那隻手,陡然落了下去,那人口有一箭橫穿而出。
不過一息的工夫,那人目眥盡裂地倒在了地上。
項宜方才的陡然變故里怔了一時,再抬頭,卻看到了火衝天的夜空下,男人手裏握著一把長弓,姿高地騎在一匹黑馬之上。
在他後,衝天的火下,烏泱泱全是從天而降的兵。
譚廷在方才那一瞬里,腦袋幾乎空了一時,手下的箭想都沒想就了出去。
他眼下更是立時翻下馬,兩步到了項宜前。
項宜鼻尖還有那強盜上迸出的鮮。
只見男人拉著的手臂,著眉眼,上上下下地打量了,半晌,才閉起眼睛大鬆了口氣。
接著他抬起手來,骨節分明的手指落在鼻尖,輕輕掉了那滴鮮。
他的作輕極了,項宜怔了一瞬,這才堪堪回過神來,
整條街幾乎都是他帶來的人。
猜你喜歡
-
完結336 章

狂妃來襲:丑顏王爺我要了
殺手之王穿越而來,怎可繼續受盡屈辱!皇帝賜婚又怎樣,生父算計姨娘庶妹心狠又怎樣?淪為丑顏王爺未婚妻,她嗤笑:“夫君如此美如天仙,不知世人是被豬油蒙了眼嗎?”“女人,嫁于我之后,你還以為有能力逃離我嗎?”…
89.5萬字8 120879 -
完結905 章

空間娘子要馭夫
二十一世紀神醫門后人穿越到一個架空的年代。剛來第一天被浸豬籠……沒關系,她裝神弄鬼嚇死他們……又被打暈喂狼?沒關系,她拉下一個倒霉蛋……只是,這個倒霉蛋貌似很有性格,白天奴役她,晚上壓榨她……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五年翻身得解釋。雙寶萌娃出世…
127.8萬字8 22626 -
連載52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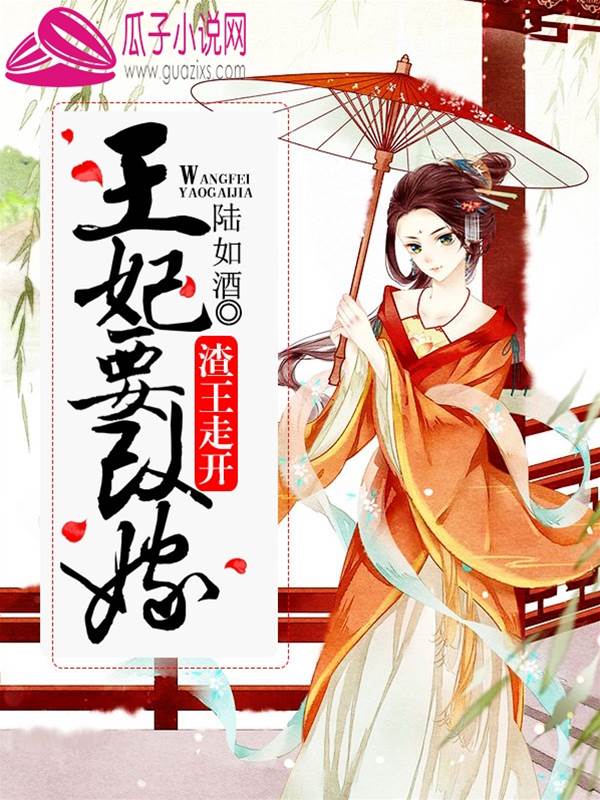
渣王走開:王妃要改嫁蘇妙妗季承翊
蘇妙,世界著名女總裁,好不容易擠出時間度個假,卻遭遇遊輪失事,一朝清醒成為了睿王府不受寵的傻王妃,頭破血流昏倒在地都沒有人管。世人皆知,相府嫡長女蘇妙妗,懦弱狹隘,除了一張臉,簡直是個毫無實處的廢物!蘇妙妗笑了:老娘天下最美!我有顏值我人性!“王妃,王爺今晚又宿在側妃那裏了!”“哦。”某人頭也不抬,清點著自己的小金庫。“王妃,您的庶妹聲稱懷了王爺的骨肉!”“知道了。”某人吹了吹新做的指甲,麵不改色。“王妃,王爺今晚宣您,已經往這邊過來啦!”“什麼!”某人大驚失色:“快,為我梳妝打扮,畫的越醜越好……”某王爺:……
99.7萬字8 12789 -
完結163 章

嫁三叔
顧長鈞發現,最近自家門口總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少年徘徊不去。一開始他以爲是政敵派來的細作。 後來,向來與他不對付的羅大將軍和昌平侯世子前後腳上門,給他作揖磕頭自稱“晚輩”,顧長鈞才恍然大悟。 原來後院住着的那個小姑娘,已經到了說親的年紀。 顧長鈞臉色黑沉,叫人喊了周鶯進來,想告誡她要安分守己別惹上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卻在見到周鶯那瞬結巴了一下。 怎麼沒人告訴他,那個小哭包什麼時候出落得這般沉魚落雁了? 周鶯自幼失怙,被顧家收養後,纔算有個避風港。她使勁學習女紅廚藝,想討得顧家上下歡心,可不知爲何,那個便宜三叔總對她不假辭色。 直到有一天,三叔突然通知她:“收拾收拾,該成親了。” 周鶯愕然。 同時,她又聽說,三叔要娶三嬸了?不知是哪個倒黴蛋,要嫁給三叔那樣凶神惡煞的人。 後來,周鶯哭着發現,那個倒黴蛋就是她自己。 單純膽小小白兔女主vs陰晴不定蛇精病男主
25.4萬字8.18 1639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