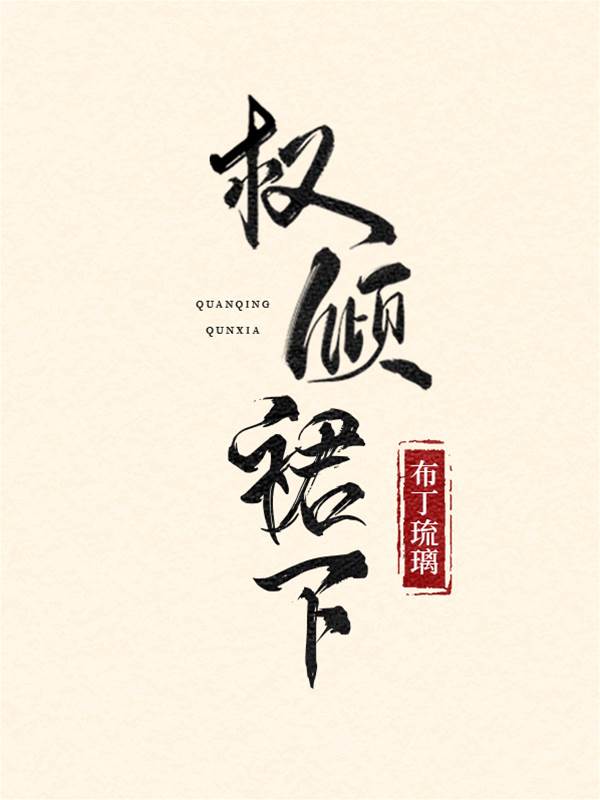《回到反派黑化前》 93、冷落(雙更合一)
自己也說了,煩這個。
他提過好幾次親的事,一直沒什麼反應,要麼就說,讓他找父母親談談,要麼就干脆當沒聽見似的。
特別是那句,六界盛會回去就閉關沖擊破碎境。
說也得上百年。
進去之前親,時間太匆促,想要風大辦的兩家肯定不會同意,那麼,就只有等出來之后再辦。
在拖延時間。
為什麼。
因為不想嫁。
除了這個原因,秦冬霖想不到別的。
“你先等等。”伍斐理了理思緒,問他:“你跟提過這事嗎?”
秦冬霖線往下:“提過。”
“你怎麼提的。”伍斐說:“你重復一遍,我覺得應該是你說的話有問題。”
秦冬霖皺著眉,簡單提了兩句。
“你這樣肯定不行。”伍斐用一種我就知道是這樣的語氣看他,道:“小十有多氣講究,你自己也知道,婚姻大事,雖說聽父母之命,你們兩個又是從小就定下來的,但哪個孩子聽到這樣公事公辦的通知話語會開心?”
“是,都知道你疼,但我們知道是我們知道,小十自己也能覺到,可你又不是沒長,說兩句甜言語哄哄人,讓開心開心也不會?”
“這個病我真是老早就想說你了。”伍斐接著說:“就拿這次你在心里跟宋昀訶較勁的事來說,雖然確實沒必要,但不得不說,你表達不滿的方式——臉臭得只讓人想遠離,這有什麼用?自己跟自己慪氣?”
“我知道,你為流岐山君,天生的贏家,有些力抗慣了,不管苦還是累,憂還是愁,你都半個字不說,永遠藏在心里,久而久之,大家習慣依賴你,信任你,那群小崽子天天在比試臺以你為目標,誰都覺得,秦冬霖是神。”
“別人也就算了,可你既然都想到了親這一步,小十是你的道,日后那麼長的歲月,難道都要看你的臉過日子不?”
“猜來猜去的,累不累?是個人都累,更何況是小十。”
一口氣說到這,伍斐看了看秦冬霖越來越不好看的神,默默停下來了一口氣。
“還有呢。”秦冬霖勉強抑住了脾氣,道:“你接著說。”
伍斐還真沒客氣,他銜接得很快,接著道:“你就是吃了的虧,什麼都不會說,什麼都不愿意說。”
“有時候,在自己喜歡的人面前服一下真沒什麼,也你想象中沒那麼困難。”
“你心里什麼想法,別都藏著掖著,見不得一樣,你就直截了當跟說自己因為哪件事不開心了,有緒了,不開心了你哄,你不開心了哄,日子不就是這麼過出來的嘛。”
說了這麼多,怕秦冬霖聽不懂,伍斐干脆擺明了跟他說:“你就告訴,流岐山君這個位置到底有多難坐,告訴天外天的劫雷劈到上到底有多難捱。”
“告訴,今天那套明明已經進你口袋但又被你眼也不眨丟回去的龍鱗,其實你還需要,之所以丟回去不是因為不了的死纏爛打,而是因為你喜歡,就樂意這麼寵著。”
“告訴你想和親不是因為父母之命,不是因為到了可以親的年齡。”
聽到這里,秦冬霖臉已經不止用一個冷字可以形容了,他瞇了下眼,懶懶地了下退,邁步之前,還不忘說一聲:“看不出來,你邊雖然連個人的影子都見不著,這滿口紙上談兵的功夫倒是不錯。”
伍斐低低地罵了句臟話,覺得自己費這麼多口舌這麼多心真是自討苦吃。
但不得不說,他的這番話是有效的。
翌日,夜深,宋湫十不知道怎麼有了興致,非要拉秦冬霖出來對練。
到中州境待了半年,出來后兩人可謂是胎換骨。
一圓月沉在天穹上,黑暗中的人,拂翩躚的影,都了鋪開畫卷中的一幕。
融合了前世之道后,宋湫十的琴意突飛猛漲,妖月琴在手中發揮出的威力幾乎達到了極破壞的程度,而且擁有前世記憶的另一個好是,除了琴,還學會了一樣別的東西。
影翻飛,劍意橫空。
宋湫十在激烈的手中選擇了近戰,秦冬霖確實對沒防備,或者說是,早知的打算,但偏不聲的縱容,想靠近,他就故意讓近。
最后時刻,湫十收回妖月琴,兩只雪白的手掌握拳,直接落到了秦冬霖的膛前。
雖然聽著沉悶的聲音不算留,可收了至一半的力道。
換在平時,也就是跟秦冬霖打打鬧鬧的意味。
可月下,秦冬霖腰微微彎了下,手指碾了碾膛的位置,臉刷白。
湫十微楞,而后連忙跑過來,問:“秦冬霖,你怎麼了?”
說完,很快反應過來:“你上有傷?”
這換在從前,秦冬霖都不會皺一下眉,傷是小傷,疼是真的,可無傷大雅,不影響接下來的事,所以沒必要說出來。
跟博取同似的。
而現在,他看著湫十關切的眼神,長長的睫微垂,沉默了半晌,承認了:“走天道的時候留的傷,沒大事,就是有點疼。”
湫十聽完,在空間戒里搜搜找找一陣,將兩顆深褐的丹藥送到他邊,皺著眉,聲音有些懊惱:“怪我,剛才興致上頭,沒想那麼多,力道沒收住。”
秦冬霖咽下止痛的丹藥,結輕微地滾了下,道:“不怪你。”
月如水,蟲鳴陣陣。
確實不怪。
他故意讓近,故意讓打出那一拳,故意表出疼痛的神。
想讓關心,想讓心疼。
“現在怎麼樣了啊?”湫十指尖的靈力躍,毫無阻礙的順著他的手腕淌到里,皺著眉,道:“你那日說沒事,都不用進室調息,我以為已經好了。”
秦冬霖抬眸,和著簌簌的夜風,聲線微低:“沒好。”
他道:“很疼。”
這樣的聲線,這樣的姿態,對秦冬霖而言,已經跟撒沒有區別了。
湫十頓了一下。
秦冬霖又道:“你不理我,心思全在宋昀訶上。”
控訴般不滿的話語,從他里吐出來,配著他那張臉,那副神,竟現出一種難以言說的無害和委屈來。
“我們瞞著他,理虧呢。”湫十看了他兩眼,有些擔心,又有些好笑:“秦冬霖,你都多大了,怎麼還真跟我哥較勁。”
“伍斐都說了,我從前可都是這樣追著你跑的,追了這麼多年,還不夠?”
秦冬霖沉默良久,在宋湫十幾乎以為他已經無聲妥協的時候,他突然輕聲道:“不夠。”
“宋小十,我沒你想的那麼大度,也沒你想的那麼完。”
“你注意力不在我上,我不開心。”
“哥哥也一樣。”
說到這,他似乎自嘲般的輕笑了下:“哪怕你追著我跑,天天嚷著我名字,時時在眼前晃。”
“還是覺得不夠。”
秦冬霖從來自律清冷,可唯獨在宋湫十上,貪得無厭,野心昭昭。他恨不得霸占每一個眼神,每一分心神。
跟瘋了一樣。
秦冬霖俯,清冷的氣息隨之近,初雪一樣冰涼的溫度一下接一下落在的眼尾,寸寸研磨,像是要將那塊皮磨化。
他聲線在不知不覺間染上了曖昧的啞:“我知道沒必要。我控制不了自己。”
所以只能擺著一張臭臉。
不是要對兇。
只是不了被冷落。
他輕輕攏開的長發,啄了啄白的耳側,聲音里帶著點難以察覺的示弱意味。
“我就是,想讓你多疼疼我。”
“宋小十。”他銜著那塊白的耳珠,話語含糊,熱氣幾乎漫到了湫十的心尖上,“別冷落我了,不?”
作者有話要說:對不起大家,今天遲到了這麼久。
下班之后就鎖了房,手機和電腦都出不來,沒法上評論區請假,后面出來了,想著時間也晚了,干脆寫長一點,這章算雙更合一。
明天臨時要上班,我盡量也多寫點。
熬不住了,困死了,晚安。
本章評論,前五十發紅包。
猜你喜歡
-
完結90 章
若春和景明
那時的他高高在上,不可碰觸;她狼狽尷尬,一無所有。在努力,也是命數,讓她看見他的夢,夢中有她的未來。跨越傲慢和偏見,他們做下一個約定——“有生之年,我一定要看到新的時代和紀年。我要看到海上最高的浪潮!哪怕窮盡一生,也決不放棄!”“好啊,我陪你一起!”他們腳下,車之河流海浪般顛簸流淌。而他們頭頂,星空亙古浩瀚,見證著一切。那一年,尚年少,多好,人生剛開始,一切皆能及,未來猶可追。
31.3萬字8.18 6148 -
完結95 章

過野
巷子吹進了末冬的冷風,一墻之隔,林初聽到幾個男生在拿她打賭—— “執哥,能跟她談滿兩個月不分就算贏。” 幾天后,他頭流著血跟她擦肩而過 她踏進巷子向他伸出了手,“請問,你身體有什麼不適嗎?” 又幾天,游戲場所外,他喊住她。 “喂,做我女朋友怎麼樣?” 林初考慮了幾天。 4月9號,她應了他。 6月9號,高考結束。 兩個月,是他的賭,亦是她的賭。 在林初心里,陳執想做的事會想法設法做到,隨心所欲,卻心思縝密。 所以,她步步為營,卻沒料到他毫不防備。 “過了這個野,你就是勝者。” *彼此救贖
26.9萬字8 7197 -
完結1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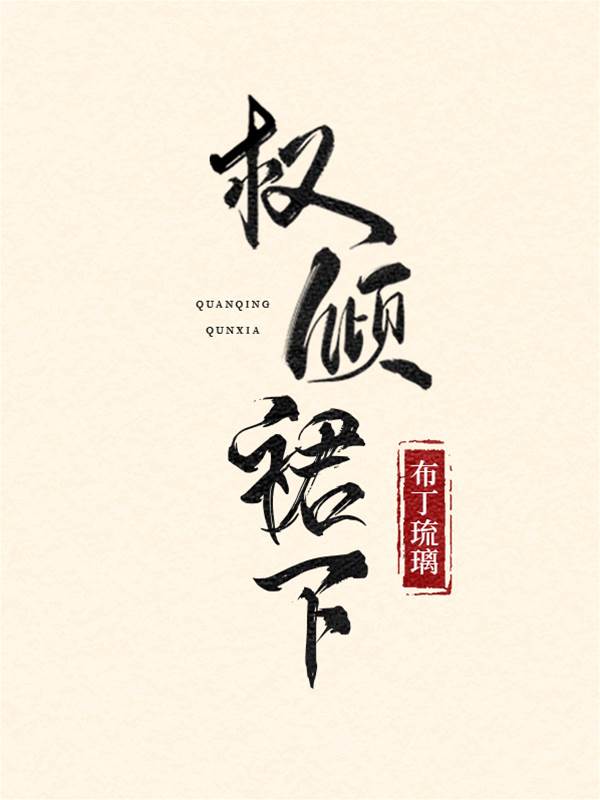
權傾裙下
太子死了,大玄朝絕了後。叛軍兵臨城下。為了穩住局勢,查清孿生兄長的死因,長風公主趙嫣不得不換上男裝,扮起了迎風咯血的東宮太子。入東宮的那夜,皇后萬般叮囑:“肅王身為本朝唯一一位異姓王,把控朝野多年、擁兵自重,其狼子野心,不可不防!”聽得趙嫣將馬甲捂了又捂,日日如履薄冰。直到某日,趙嫣遭人暗算。醒來後一片荒唐,而那位權傾天下的肅王殿下,正披髮散衣在側,俊美微挑的眼睛慵懶而又危險。完了!趙嫣腦子一片空白,轉身就跑。下一刻,衣帶被勾住。肅王嗤了聲,嗓音染上不悅:“這就跑,不好吧?”“小太子”墨髮披散,白著臉磕巴道:“我……我去閱奏摺。”“好啊。”男人不急不緩地勾著她的髮絲,低啞道,“殿下閱奏摺,臣閱殿下。” 世人皆道天生反骨、桀驁不馴的肅王殿下轉了性,不搞事不造反,卻迷上了輔佐太子。日日留宿東宮不說,還與太子同榻抵足而眠。誰料一朝事發,東宮太子竟然是女兒身,女扮男裝為禍朝綱。滿朝嘩然,眾人皆猜想肅王會抓住這個機會,推翻帝權取而代之。卻不料朝堂問審,一身玄黑大氅的肅王當著文武百官的面俯身垂首,伸臂搭住少女纖細的指尖。“別怕,朝前走。”他嗓音肅殺而又可靠,淡淡道,“人若妄議,臣便殺了那人;天若阻攔,臣便反了這天。”
52.5萬字8 22193 -
完結98 章

偏執寵愛
1 軍隊裡大家都知道,他們的陸隊長背上有一處誇張濃烈的紋身。 像一幅畫,用最濃重的色彩與最明媚的筆觸畫下一枝櫻桃藤蔓。 有援疆女醫生偷偷問他:「這處紋身是否是紀念一個人?」 陸舟神色寡淡,撚滅了煙:「沒有。」 我的愛沉重、自私、黑暗、絕望,而我愛你。 「我多想把你關在不見天日的房間,多想把你心臟上屬於別人的部分都一點一點挖出來,多想糾纏不清,多想一次次佔有你,想聽到你的哭喊,看到你的恐懼,看到你的屈服。 ——陸舟日記 2 沈亦歡長大後還記得16歲那年軍訓,毒辣的太陽,冰鎮的西瓜,和那個格外清純的男生。 人人都說陸舟高冷,疏離,自持禁欲,從來沒見到他對哪個女生笑過 後來大家都聽說那個全校有名的沈亦歡在追陸舟,可陸舟始終對她愛搭不理。 只有沈亦歡知道 那天晚自習學校斷電,大家歡呼著放學時,她被拉進一個黑僻的樓道。 陸舟抵著她,喘著氣,難以自控地吻她唇。
32.1萬字8 962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