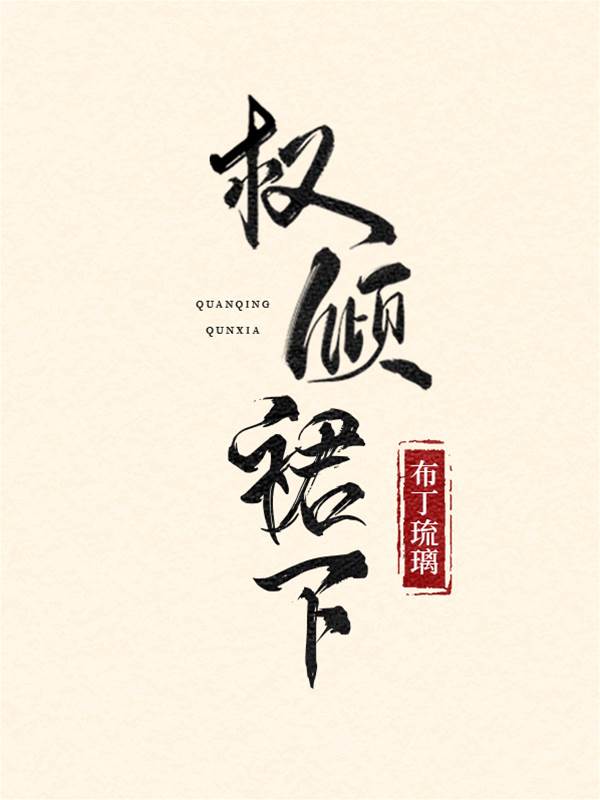《絕對臣服》 第16章 第 16 章
“外面風雪大, 把浴袍穿好,回主臥好好睡上一覺。”
傅青淮用去咬的,的, 很薄, 隨著異常強勢地吮吸走間一氧氣,得姜濃腦海中有種眩暈的覺, 下意識曲起手指攥他襯衫的第二顆紐扣, 扯松了線都不自知。
直到過了好幾分鐘, 或許可能更久的時間。
傅青淮從舌尖退回來, 修長薄燙的手掌卻還留在層層的浴袍里,用指腹,一點點的挲那片白的, 又將俊的臉龐稍側,再次含著角往下延,帶了點潤的親吻從雪頸落到咽。
天的臺寂靜,逐晚的天下已經不見遠散步孔雀的蹤影,刮來風雪反襯得姜濃缺氧的呼吸聲更清晰幾分,心臟劇烈收著, 從未嘗試過原來男間的接吻, 能親到這種可怕程度。
完全不知道要推開傅青淮, 任憑他把人吻了,也了,才順勢地把松垮的浴袍腰帶重新系好,綢質的尾端似浸飽了水一直下過雪白的大。
“還好嗎?”
姜濃聽到他低啞的問, 也不敢將被親得發紅的張開了。
離得近, 怕男人強烈的氣息會再次磨著咽浸全五臟六腑, 只能張地著卷翹睫末端, 半響后,才輕輕的應了聲:“嗯。”
臉也跟著,又紅了一片。
隨即又想到傅青淮那句回主臥睡覺,忍不住地看向他俊的面容。
比起還猶豫不決要不要留下過夜,反觀傅青淮已經著的耳朵,聲線帶著蠱的啞意:“快去,再待下去就要不統了。”
啊?
姜濃這會兒怎麼看都是副我見猶憐樣,卻猛地清醒過來,手心推開他膛,往室跑了幾步,又停了一下,才走到沒有風雪的地方。
*
走遠,傅青淮才緩慢地下樓,一熨帖合的白襯衫西裝,在清冽的下將姿襯托得拔料峭,近看才會發現,有枚致的紐扣松了線,明眼人都瞧的出是被誰扯的。
他走到酒柜旁,抬手將那瓶剩一大半的白蘭地拿了出來。
琥珀的靡芒映照在眼底,也顯得瞳略深,靜默片刻,借著烈酒來下那邪火。
客廳之外。
粱澈暗中觀察,忽而,余掃到某只戴著尾戒的手拿著黑手機從側出現。
“你活夠了?!!”他震驚。
燕杭拍了張說:“白孔雀開屏難得一見啊,迷信點說法看到就會有罕見的好運氣,拍下來發個朋友圈。”
粱澈被繞暈兩秒,竟然覺得這話沒病。
可他不敢去拍傅青淮,正要掏出手機去燕杭朋友圈盜圖時,又聽他嗓音輕謔的說:“要不要討好下你家傅總……”
粱澈不用腦子都知道這個紈绔子弟又想做什麼,雙目怒瞪了過去:“傅總有潔癖,從不用。”
燕杭把眼挑起來:“?”
……
此刻二樓上。
姜濃走進寬敞華的主臥后,第一眼就看到那張黑絨的大床,好不容易褪去些的熱意,又自耳子慢慢彌漫開了。
的經歷就如同生活一樣,像張白紙。
完全是不懂。
男間進展的速度是怎樣的?
姜濃只要稍認真地想,腦海中就無法控制的自想起和傅青淮在臺接吻的畫面——他喜歡一邊深吻著自己的,一邊將描繪著神佛紋的那只手往浴袍里,順著落的帶,一寸寸地.挲過腰側細膩的,乃至骨節清晰分明的手指還要往下點。
眼尾的緋紅浮起來,這幅子,到現在仿佛還留有一他的溫度。
先去浴室
洗個涼水澡冷靜了稍會,等再出來時。
姜濃糟糟的心緒已經徹底平復下來,選擇坐在了左側的床邊,浴袍下的兩只白的蜷曲著,借著四下安靜,出手機給季如琢發了消息:「如琢,我想跟告訴你一件事。」
「嗯?」
窗外雪夜還尚早,季如琢回的很及時。
姜濃將致的下輕輕在膝上,逐字地編輯著,將和傅青淮的事分給了這位多年摯友:「你還記得我跟你說過,十年前有個份不詳的恩人在暴風雨夜里救過我嗎?他就是傅青淮,我們在一起了。」
季如琢:「濃濃,恭喜你。」
姜濃是一直惦記著那場暴風雨夜里的恩人年,不知他姓甚名誰,卻將他容貌狠狠記在了心底,這個,唯獨只跟季如琢在私下吐過。
所以潛意識覺得,季如琢也算是多年窺不見天暗里的見證者了。
原是還有好多話想跟他討教。
比如剛打破曖昧的男間在一起該怎麼相才最合適?
奈何季如琢那邊說了句恭喜之后,就沒有在回復。
姜濃手指蜷曲地揪著黑絨被子,等了許久,才將快發燙的手機輕輕放回床頭柜。
-
藏月拍賣會所的頂樓私人藏品室,一般無人敢輕易冒然闖,眾所周知是小季老板的區。
厚重的窗簾隔絕了外面一大片的雪,線昏暗,擺在雕琢柜子上的許多古董鐘擺,都在滴答的搖轉著,似在提醒著這一分一秒過去的寶貴時間。
隨著指向夜間十點整,涼幽幽的門外驀地驚響起爭執的聲音。
「蘇荷小姐,您沒有提前預約……真的不能進去。」
「你確定要攔我?」
「……不是,小季先生今晚不見外客,我也只是聽從吩咐。」
「讓開。」
隨著這聲落地,閉的門也被重重推開。
一吊帶鎏金的年輕人影出現,只是沒走近去兩步,高跟鞋就猛地停下,連纖長胳膊的都泛起了寒意。
無人敢跟進來。
看到季如琢悉的影廓就懶散地靠在人塌那邊,于在外如竹兮的君子形象不同,此刻他長長吐了口煙霧,棱角清晰的臉孔瞬間被籠罩得模糊幾分,從側面角度看過去,襯衫領頹廢松垮,仰起的下顎線至纖瘦修長的脖頸給人一種罕見的削薄冷白。
花了好半天時間,蘇荷才從這幕里回過神,瓣微啟:“季如琢,你不是戒煙了嗎?”
問這話時。
就沒有指過季如琢能正兒八經回答自己,腳下的高跟鞋很僵冷,一步步地走到他面前,將燃燒未盡的煙奪下,置氣般往古董鐘那邊扔掉,也不怕燙出點痕跡。
因為蘇荷不在乎,為城首富獨生的,有資本可以給季如琢天底下最珍貴的古董。
扔了煙。
蘇荷還不夠解氣,卻沒忘記今晚是跑來質問他的:“你是不是又被人布局算計了?”
季如琢低醇的嗓音被煙熏染的沉啞:“什麼?”
“你裝,林樾舟都跟我坦白了——”蘇荷家族勢力也是混京圈的,今晚無意中聽到了一些關于那位傅家主和神人音的風月.事,立即就聯想到了姜濃上。
而后來,也只是稍微試探了下藏月拍賣行的另一個老板林樾舟。
就從林樾舟口中得知了季如琢曾經借著拍賣鴛鴦枕,將姜濃推到了傅家主的面前。
這讓蘇荷險些以為自己幻聽了,來這,不是為給姜濃討個說法什麼的,畢竟滿心滿眼里的,只有眼前這個薄寡義的男人:“姜濃就跟了七六一樣,對攀附權貴的事本不興趣,是你
,把介紹給了傅青淮,但是我想不通……你季如琢,怎麼舍得把姜濃拱手送人啊?”
所以、一定是出了什麼事!
蘇荷慢慢地蹲下,執著地著在黑暗中異常沉默的季如琢,聲音含著強烈乞求道:“只是需要錢能解決的麻煩,多我都可以給你。”
季如琢語調平靜問:“就像當年那樣麼?”
蘇荷格外漂亮的臉略僵,被迫著想起是怎麼不彩得到他的。
季如琢剛鑒寶界這行頗有名氣,生了一副讓人忘俗的人相,又以雅正聞名。
可以說,那時的他才是真正意氣風發,直到五年前:
那時季如琢有個至好友,為了公司融資偽造出一件天價假古董,又借他這雙眼,瞞天過海所有人,直到事被曝出,連被布局算計的他也被卷這場“假貨案”里。
主犯的下場鋃鐺獄,而季如琢也被鑒寶界的前輩們聯手封殺,還背負上了巨額負債。
他就是這時候郁郁不得志染上了煙癮,多年戒不掉。
蘇荷也是這時候,不惜倒追,拿著一份天價契約幫他解了困境,從而兩人心照不宣地私了三年,直到現在都不愿意跟季如琢徹底斷干凈。
不知是室沒有開暖氣,還是被他一句話扎痛了心,連帶致睫都變得潤起來。
季如琢清晰冰涼的臉孔似乎溫和起來,抬指,去的臉:“你今天很,不要哭花了妝。”
蘇荷很快被他轉移了重點,每次來藏月找季如琢,都會特意隆重的裝扮過,選柜里最的一條子,將慕迷的心思毫不掩藏,扯了扯鎏金擺,面頰泛紅說:“我上樓前把大了,就是想給你看看這條子。”
猜你喜歡
-
完結90 章
若春和景明
那時的他高高在上,不可碰觸;她狼狽尷尬,一無所有。在努力,也是命數,讓她看見他的夢,夢中有她的未來。跨越傲慢和偏見,他們做下一個約定——“有生之年,我一定要看到新的時代和紀年。我要看到海上最高的浪潮!哪怕窮盡一生,也決不放棄!”“好啊,我陪你一起!”他們腳下,車之河流海浪般顛簸流淌。而他們頭頂,星空亙古浩瀚,見證著一切。那一年,尚年少,多好,人生剛開始,一切皆能及,未來猶可追。
31.3萬字8.18 6143 -
完結95 章

過野
巷子吹進了末冬的冷風,一墻之隔,林初聽到幾個男生在拿她打賭—— “執哥,能跟她談滿兩個月不分就算贏。” 幾天后,他頭流著血跟她擦肩而過 她踏進巷子向他伸出了手,“請問,你身體有什麼不適嗎?” 又幾天,游戲場所外,他喊住她。 “喂,做我女朋友怎麼樣?” 林初考慮了幾天。 4月9號,她應了他。 6月9號,高考結束。 兩個月,是他的賭,亦是她的賭。 在林初心里,陳執想做的事會想法設法做到,隨心所欲,卻心思縝密。 所以,她步步為營,卻沒料到他毫不防備。 “過了這個野,你就是勝者。” *彼此救贖
26.9萬字8 7194 -
完結1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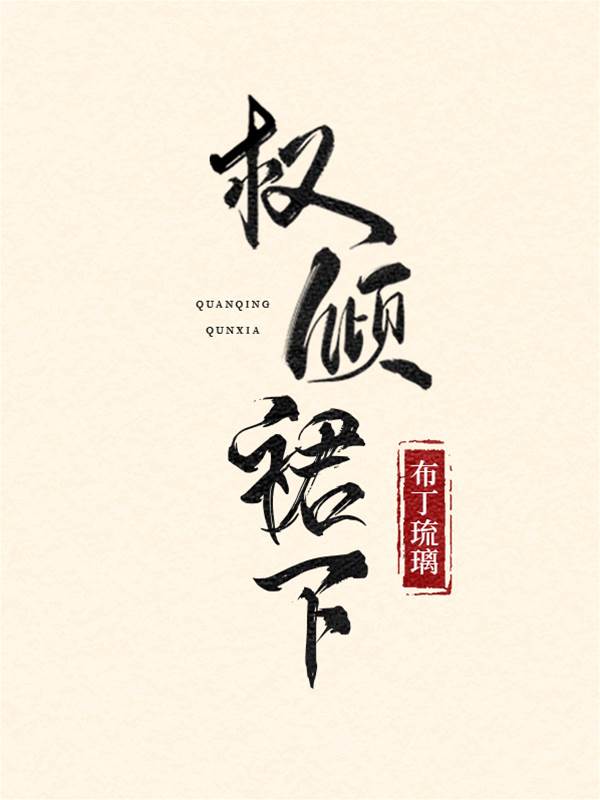
權傾裙下
太子死了,大玄朝絕了後。叛軍兵臨城下。為了穩住局勢,查清孿生兄長的死因,長風公主趙嫣不得不換上男裝,扮起了迎風咯血的東宮太子。入東宮的那夜,皇后萬般叮囑:“肅王身為本朝唯一一位異姓王,把控朝野多年、擁兵自重,其狼子野心,不可不防!”聽得趙嫣將馬甲捂了又捂,日日如履薄冰。直到某日,趙嫣遭人暗算。醒來後一片荒唐,而那位權傾天下的肅王殿下,正披髮散衣在側,俊美微挑的眼睛慵懶而又危險。完了!趙嫣腦子一片空白,轉身就跑。下一刻,衣帶被勾住。肅王嗤了聲,嗓音染上不悅:“這就跑,不好吧?”“小太子”墨髮披散,白著臉磕巴道:“我……我去閱奏摺。”“好啊。”男人不急不緩地勾著她的髮絲,低啞道,“殿下閱奏摺,臣閱殿下。” 世人皆道天生反骨、桀驁不馴的肅王殿下轉了性,不搞事不造反,卻迷上了輔佐太子。日日留宿東宮不說,還與太子同榻抵足而眠。誰料一朝事發,東宮太子竟然是女兒身,女扮男裝為禍朝綱。滿朝嘩然,眾人皆猜想肅王會抓住這個機會,推翻帝權取而代之。卻不料朝堂問審,一身玄黑大氅的肅王當著文武百官的面俯身垂首,伸臂搭住少女纖細的指尖。“別怕,朝前走。”他嗓音肅殺而又可靠,淡淡道,“人若妄議,臣便殺了那人;天若阻攔,臣便反了這天。”
52.5萬字8 21727 -
完結98 章

偏執寵愛
1 軍隊裡大家都知道,他們的陸隊長背上有一處誇張濃烈的紋身。 像一幅畫,用最濃重的色彩與最明媚的筆觸畫下一枝櫻桃藤蔓。 有援疆女醫生偷偷問他:「這處紋身是否是紀念一個人?」 陸舟神色寡淡,撚滅了煙:「沒有。」 我的愛沉重、自私、黑暗、絕望,而我愛你。 「我多想把你關在不見天日的房間,多想把你心臟上屬於別人的部分都一點一點挖出來,多想糾纏不清,多想一次次佔有你,想聽到你的哭喊,看到你的恐懼,看到你的屈服。 ——陸舟日記 2 沈亦歡長大後還記得16歲那年軍訓,毒辣的太陽,冰鎮的西瓜,和那個格外清純的男生。 人人都說陸舟高冷,疏離,自持禁欲,從來沒見到他對哪個女生笑過 後來大家都聽說那個全校有名的沈亦歡在追陸舟,可陸舟始終對她愛搭不理。 只有沈亦歡知道 那天晚自習學校斷電,大家歡呼著放學時,她被拉進一個黑僻的樓道。 陸舟抵著她,喘著氣,難以自控地吻她唇。
32.1萬字8 944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