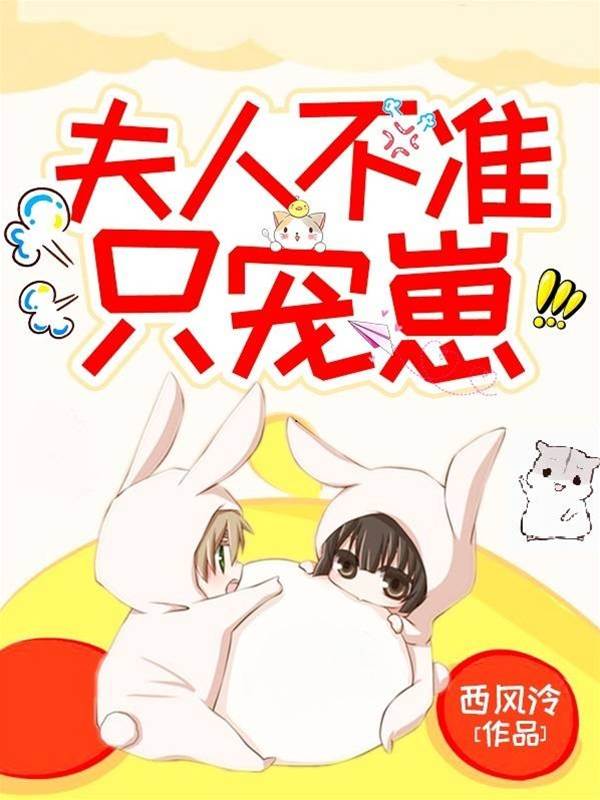《噓,國王在冬眠》 畢業典禮(。)
再上纜車,這次纜車上就他們三個人。
剛開始纜車安靜得過分。
單崇撇著頭看著纜車外雪道上的人歪歪栽栽;
衛枝低著頭摳自己手套上的一不知道哪兒來的小;
老煙還是靠在那,拿著手機不知道是在和妹妹A還是妹妹B聊天,要是換在一個小時前,衛枝可能覺得他聊得開心的,現在只品出他那自暴自棄的無所謂……
很難說是不是自暴自棄。
跟前段時間的自閉社相比較,現在的人正常喝酒,正常上課,正常妹,好像一切才剛剛回到正軌。
“說點什麼?”單崇慢吞吞把頭轉回來,著老煙,“八字站位也沒多久,走刃一共沒學幾天就轉一順了,怎麼那個后刃就深固是八字的站姿畫法擰不過來了?”
老煙明顯反應慢半拍,視線從手機上挪開,想了想說:“可能是想的太多了,其實真的高速行后刃和前刃發力姿勢都差不多,老想著后刃怎麼擺,屁要收回去,反而想太多做不好——”
“就這?”
“那不然呢,雖然是基礎行但好歹也是進階玩法,總不能半個月就隨便地大回轉,那不跟半個月上Bigair一樣荒謬麼?”
“讓你說說問題。”
“您不是看出問題了嗎,就站姿不對,沒蹬直,傾倒也不夠,您跟說唄!”
他答得語氣還理所當然,充滿著一無所畏懼的味道,單崇哼笑一聲:“我上課還是你上課?”
老煙:“我不介意您。”
單崇:“我介意。”
老煙:“您別介意。”
單崇:“老煙。”
老煙:“啊?”
“心不好就說出來,強歡笑給誰看?不知道的還以為你在拍電視劇,搞那麼悲。”
坐在纜車上,男人的指尖搭在大上隨意輕敲,掀起眼皮子掃了眼坐在對面位置上的年,“你這樣上課,不出一個月必然會有人罵你上課心不在焉,砸自己招牌。”
“……”
衛枝看了看纜車外面,久違地再一次有了想要跳纜車的蠢蠢。
懷疑單崇有那個什麼,人類牛癥——對,都不是社牛癥,而是人類牛癥——否則這人怎麼什麼話都敢往外說呢,想到什麼說什麼,一點兒也沒有要掩飾的意思。
臉都快纜車玻璃上了,衛枝用實際行真誠地展現,至不會是那個罵老煙上課心不在焉的其中一員……
只要他別畫風和他師父一模一樣那麼嚇人就行。
而這會兒,被師父一語道破,這小孩還想強撐,雪鏡摘了,認真地說:“我沒有心不好。”
“哦,你知道你剛才給我媳婦兒上課時候的畫風像誰不?”
“誰?”
“我。”
“……”
衛枝又把臉從纜車玻璃上拿起來了,轉過頭茫然地看了眼纜車中進坦白局的大老爺們,別的不想,就想先給的男朋友那驚人的自知之明鼓個掌。
而在男人直來直去的對話里,老煙面部搐了下,看了看衛枝意識到纜車里那確實沒有外人,于是終于也不裝了——
那張狗臉,眼可見地沉下來。
就像是上一秒還咧著沖主人搖尾好像很快樂的大金,這會兒耳朵耷拉了,尾也吹落了下去,一雙漆黑烏潤的眼著男人:“很明顯麼?”
單崇都懶得回答這個問題。
在崇禮雪場,他雖然像個高高在上的神仙這不搭理那不給眼神兒,但這并不代表他真就不在意別人或者說是不會察言觀了……
剛才在纜車上,他可能是唯一一個從三言兩語里品出徒弟心不對勁的,所以下了纜車,直接就跟著他們了。
背刺沒事閑著管他“阿爸”,就像是個詛咒,他一天天的除了手把手教這些王八犢子跳臺,負責他們的人安全,教導他們出活兒,偶爾還真做點親爹才干的事……
這會兒兒子失了,失魂落魄的,阿爸也是一眼看了出來。
是個合格的阿爸。
所以大概就是因為這樣,哪怕像是沒得的雪機,阿爸的邊也總是圍繞著各式各樣的人。
“看開點,”他說,“這世界上有緣無分的事多了去了。”
老煙上纜車就摘了頭盔,這會兒剛摘了雪鏡,頭盔也抱在懷里,毫無遮擋的件,于是坐在他對面的兩人可以輕而易舉地看見他紅了眼——
單崇一點反應都沒,冷著臉,著他。
衛枝覺自己屁下面長出了個仙人掌,坐立不安,頭皮發麻,心中十分后悔,當初就該做點人道主義的事兒,比如把姜南風轟去新疆,讓別來崇禮。
“我不是想不開,”老煙停頓了下,“算了,我就是想不開。”
衛枝角了。
“我們到底是有多‘有緣無份‘,才能好好的因為一件衛作為導火索,鬧到今天這個地步……”
老煙想了想,吸了吸鼻子,又繼續道,“我們都這樣了,還不能在一起……這他媽得怕不是上輩子在佛祖面前把頭磕爛了,才換來的一段短暫孽緣。”
衛枝聽他的形容詞,覺得“頭磕爛了換一段短暫孽緣”什麼的,有點形象立。
換了一個創作者,都不一定能在漫畫里搗鼓出這麼煽的臺詞。
而慨中,邊男人卻一臉平靜,聽年人絮絮叨叨,沒打斷他。
等他說完了,他才突然開口:“你哭了嗎?”
老煙抬起手,狠狠地用雪服外套袖子了眼睛,又:“沒有!”
單崇“哦”了聲,薄輕抿,淡道:“真有出息。”
而后又說。
“我問你這個話題不是為了驗證我的猜測,就是提醒你下,過去的人就讓過去了,你別老回頭看——”
伴隨著男人的低沉嗓音,在他說出“你別老回頭看”時,“吧嗒”一下,水落的聲音打斷了他的話。
一大滴水落在老煙的安全盔俱樂部紙上。
不得不說這是自己這輩子第一次正經八本看男人落淚,衛枝被嚇得挪了挪屁,崩潰心想這纜車真的沒法呆了。
別問。
問就是想跳。
老煙瞪著通紅的眼,沙啞著嗓音:“您勸人的時候倒是想得開,這事兒換你上呢!換了你,你能做到不回頭看小師妹一眼麼——”
“……”
單崇轉過頭,看了邊的小姑娘一眼。
這會兒后者也正著他,瓣微張,顯得有點兒不知所措。
“我不一樣。”
單崇盯著衛枝的眼睛。
“我不一樣,因為我永遠不會用背對著走。”
懶洋洋地收回了目,男人用無比自然與平靜的聲音告訴老煙,“所以無論如何也不會有需要回頭才能看見的那一天。”
纜車短暫安靜了幾秒。
別說是衛枝,大概連老煙都沒想到閻王爺開口說話的時候能這麼聽。
雙雙懵中,老煙崩潰了:“你就這麼安人的?”
“我沒在安你,只是告訴你過去的都過去了,回頭毫無意義,別擱這臭著臉教你師娘,要看臭臉式教學看我不好嗎?”
單崇說著,想了下,還是沒忍住真誠發問,“你是讓我安你?你有病?”
他要是會安人,那就不會對上課拒不配合、要發脾氣、一言不合哭唧唧的朋友束手無策……
也就不到老煙來上這破刻的課了。
這麼簡單的邏輯都想不明白,換作他是姜南風,他也想甩了他——
畢竟好像跟這人在一起也是會影響下一代智商的樣子。
……
到了下午,衛枝回去換了塊借給的公園板。
因為上刻課的老師被男朋友三言兩語整破防了,自閉了,不能強歡笑了。
他那個狀態本上不了課,所以只好勉為其難地跟著男朋友進公園。
坐在纜車上,衛枝摳著雪板上的積雪,逐漸品出不對味來:“你是不是故意欺負老煙呢?”
單崇面不改:“我欺負他做什麼?”
“他走了我就只能跟著你進公園了。”小姑娘抬起眼掃了他一眼,“你這個人心思怎麼這麼歹毒。”
纜車上就他們倆。
單崇長一,瞥了一眼,一臉放松:“你不是后天的飛機回家了嗎,翻了年不一定過來,過來也是準備封板了。”
衛枝:“然后呢?”
單崇語氣輕描淡寫:“我就琢磨,給你錄個視頻吧。”
衛枝:“什麼?”
單崇:“紀念朋友第一個雪季,給他們看看,從穿板開始,天天跟著我在雪上打滾,滾什麼樣了……免得他們說我教不了零基礎,不會教和不想教不是一回事。”
衛枝:“你這個人的虛榮心……”
衛枝:“不是,給他們看看是給誰們看看!視頻往哪發?”
猜你喜歡
-
完結37 章

偏偏占有你
姜晚照年少時喜歡一個男人,為他傾盡所有。可惜,男人永遠都是一幅冷漠淡然,漫不經心的模樣。喜歡無果,姜晚照喪了氣。天涯何處無芳草,何必單戀一枝花。何況她還有一堆小哥哥寵,才不稀罕他!想明白后,她瀟瀟灑灑放了手,一心一意搞事業。 沒過多久,姜晚照發現——她所在的女團,人氣暴漲,資源逆天!她所在的星空娛樂,她成了最大的股東,享有絕對的掌控權。連續幾天,她收到了不動產若干處,豪車一大排,連帶著私人飛機,郵輪,名貴珠寶琳瑯滿目,應接不暇…… 姜晚照:“……”再相見的慈善晚宴上,姜晚照瞪著剛以她的名義拍下某條價值連城的項鏈男人,揚起明艷的小臉氣哼哼地質問:“廉總這是什麼意思?”男人黑眸沉沉,似笑非笑:“求你回來啊,這個誠意夠不夠?”直到后來她才知道,他所付出的一絲一毫,最后都會變本加厲地從她身上討回來。 一手遮天冷漠貴公子X膚白貌美破產千金
12.3萬字8 8410 -
完結375 章
隱愛100分︰惡魔總裁,強勢寵
一場意外,言小清被霸道的男人盯上。 他扔出協議︰“做我的女人,一個月,一百萬!你從今天起,專屬于我,直到我厭煩為止!” “我拒絕!” “拒絕在我面前不管用!” 拒絕不管用,她只好逃跑。 可是跑著跑著,肚子里面怎麼突然多了只小包子? 她慌亂之際,他如同惡魔一般出現,囚住她,他這次非常震怒,他說他們之間的一切都不能曝光。 她摸著肚子,告訴肚子里面的小包子︰“寶寶,你爸爸說不能曝光我和他的事,那我們也不告訴他你的存在好不好……” 某日,男人得知小包子的存在之後,立刻慌了。 他強勢的將她和孩子保護起來,從現在起,誰要是敢動她和孩子一下,他絕對讓對方吃不了兜著走。 她和寶寶,都是他的!
34.6萬字8.09 113800 -
完結10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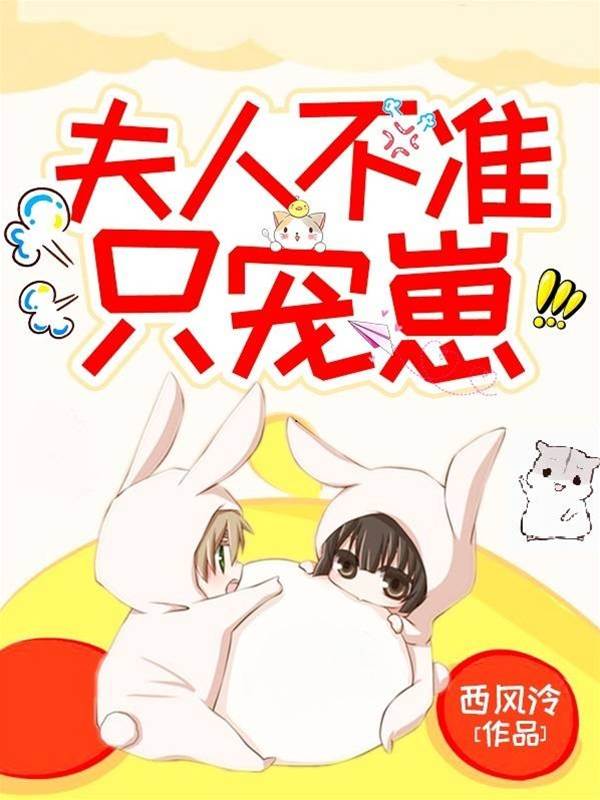
夫人不準只寵崽
南悠悠為了給母親治病為楚氏集團總裁楚寒高價產子,期間始終被蒙住眼睛,未見楚寒模樣,而楚寒卻記得她的臉,南悠悠順利產下一對龍鳳胎,還未見面就被楚家接走。
24.6萬字8 706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