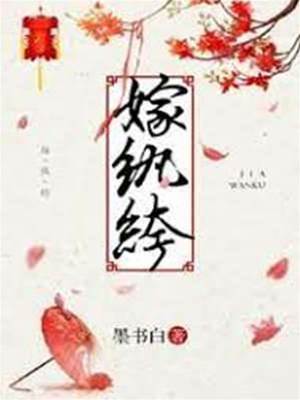《妄折她》 第28章 上藥
穆雷額頭上的青筋跳了一下。
男人攥了拳頭, 賁張的隨著呼吸起伏,他的目好似實質的利刃,二人這麼隔著一段不近不遠的距離四目相接, 最終還是商寧秀先敗下陣來,是被護在溫室中的花,比不得草原上風吹雨淋的雄鷹更能明白如何讓獵自陣腳。
商寧秀眼神左右閃躲, 開始有點后悔為什麼要去主挑釁他。
男人‘嘩’地起,商寧秀被這一個簡單的作嚇了一跳,福至心靈掉頭就跑,步子邁大了扯得下生疼, 也仍然還是被撲食的獵豹給輕易追上。
商寧秀渾戰栗被他在了柜子邊上,男人的鐵臂撐在側, 用手臂和膛筑建起了一道堅實的圍墻,那異氣息撲面而來。
即便是他都還沒有到面前的小云紡鳥, 就已經被這迫給激的呼吸急促了。
穆雷幾乎要咬碎了一口鋼牙,一拳頭重重砸在了柜子上, 卻又別無他法,只能魯低聲罵了一句, 然后便氣息暴躁地轉走了。
柜壁被這無妄之災砸出了一個下陷的坑, 逃過一劫的商寧秀著子,心里狂跳,但更多的卻是在為這頭一次對壘勝利而升騰起開心得意的緒, 畢竟之前無數次被他強抱強吻從無拒絕的余地。
穆雷獨自出門去了,外套都沒有披, 頂著外面的夜與寒風, 重重地將帳門摔上, 一聲悶響之后關得嚴嚴實實。
眼看著男人憋悶被迫無功而返, 商寧秀雖然仍然不適,但的心卻是因此而好了許多,甚至有心思坐在了梳妝臺前,出玉簪后解開自己蝎子辮,用牛角梳開始慢慢梳開頭發。
夜晚降了寒氣,商寧秀坐了沒多久就開始手腳發冷了,再加上傷在了不能久坐,將頭發放松開來之后就吹了燈自己鉆上了床,伏在絨毯里,慢慢睡了過去。
這一覺睡得并不踏實。
恍惚間好像油燈又有了亮,但并不刺眼,只影影綽綽似有似無,商寧秀迷糊間含糊不清地嘟囔了一聲:“熄燈……”
那微弱線果真就熄滅掉了。
但仍然沒能好好睡,混沌的意識中覺自己好像在做夢,夢到自己似在騎馬,馬背上的兩合不攏,半夢半醒著,緩了有好一會仍然趕不跑睡意,又再次沉沉睡去。
昏暗的屋子里,穆雷坐在床邊,確定床上的人沒有被驚醒,才放心地繼續用巾布拭著手指。
他看著酣然的睡,心想維克托說的沒有錯,果真就是心里頭的病,人醒著挨一下都要死要活的,睡著了怎麼都沒事。男人回憶起剛才到的,令人回味卻又隔靴搔的十分夾磨,他由衷嘆著,怪不得會傷,確實是太了些。
穆雷將自己的中指拭干凈,藥膏彌漫著淡淡的薄荷香味,是消腫化瘀的良藥,估著只要飲食清淡些不食辛辣,再有幾日應該就能大好了。男人將白瓷瓶蓋好,又取出了另一只口服的綠瓷瓶,將藥倒了一蓋子出來,慢慢喂進了商寧秀的角中。
第二天清晨,商寧秀醒的要比穆雷早一些。
躺在床上緩了好一會才反應過來自己在何,邊是還在沉睡中的穆雷,他昨晚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回來的,商寧秀一點印象都沒有。
男人的五鋒利闊,即便是睡著了,那線條看起來也是凌厲人的。
二人中間隔著約莫一條手臂的距離,商寧秀氣息不順,又再默默將自己挪遠了一些。
草原上的溫度仿佛被那場雨一下子就給拉進了初冬,之前蓋上還很暖和的絨毯現在竟是已經覺得有些發寒了,商寧秀一晚上下意識地將自己裹了一團,原本還保留了一些暖意,現在往外一挪,床沿上冰涼涼的,冷得又再趕將子回了毯子里。
這麼一來一回的兩下,后的男人就醒了。
穆雷還沒睜眼,習慣地在床頭盒子里了薄荷葉出來嚼著醒神,他大咧咧地躺著,忽然覺得上搭著的絨毯在一點點挪,很快就被扯了一半下去,男人睜開眼,就看見邊的商寧秀裹著滿的毯子在往床角落里挪,然后把自己團了一個球,蜷一團靠在那回頭看他。
睡飽了的人氣看著比之前好了許多,臉頰上終于又有了,雖然滿臉謹慎,但披散著一頭青,眼角嫣紅,那模樣看起來像極了才被男人好好疼過。
穆雷也沒,就這麼半睜著眼睨著,結滾了一下:“你這副表,看起來真的很勾引人。”
商寧秀和他對視著,嫌棄他的鄙不尊,不輕不重地‘嘁’了一聲,打定主意他現在沒法真的自己,頗有幾分將人吃定的挑釁。
這副模樣,力量不小的在男人心里搔撞了一下。
他眼里涌上的興味更濃了,冷哼一聲道:“你給老子等著,有你求饒的一天。”
商寧秀只當聽不見他的言語,不再理會,徑自將絨毯再拉了一些,但忽然覺得自己雙傳來的好像不太對勁,明明睡前穿了外與長袴,但現在完全沒有該有的束縛,像是只著了一件綢短绔,的雙空空如也,直接接在了絨毯短的絨上。
剛才剛醒的時候還沒反應過來,也難怪之前會覺得冷。
商寧秀如遭雷劈地僵在那,后知后覺地發覺傷有種清涼的覺緩解了之前火熱的腫痛。
的腦子直接炸裂,恍然想起昨天男人說過給他上過藥,而且晚上還要再換藥。當時穆雷摔門出去也沒再提及此事,就給忘了。
一想到男人趁睡著了對做了那般的事,商寧秀的臉頰再一次充般艷滴。
穆雷只掃了一眼就大概猜到的心里活了,活了一下頸骨,徑自起了,讓自己慢慢消化這個信息,“外面降溫了,冬天很快就要來了,這兩天給你做兩雙兔靴子,等落了雪,我帶你去后面的山坡上玩,那里有很大的草場,冬天變雪坡之后相當漂亮。”
商寧秀本沒心思聽他說話,急切出手:“你把藥給我。”
“嗯?”穆雷蹙眉發出了疑的聲音,很快反應過來說的是什麼,但沒接話。
“你給我,我自己會上藥,不需要你幫忙。”商寧秀咬著牙,無法忍自己在無知無覺的況下竟然被那男人這般猥.過。
“你自己涂不勻。”穆雷說話時無意識地挲了一下指尖,沒太把的這句話當回事,輕笑了一聲,繼續自己手中的活計,將柜子里的紅豆倒了一些出來煮湯,“那藥抹均勻了好得快些,你也些苦。”
穆雷態度強,商寧秀也是完全拿他沒辦法。
又過了一會,外面又下起了小雨,秋風卷得雨幕東倒西歪。
商寧秀手里捧著穆雷剛煮好的紅豆湯暖手,熱氣蒸騰地往上竄,遮擋住了些許的視線,讓桌子對面男人的臉稍顯朦朧。
商寧秀垂頭看著碗中自己的倒影,忽然兩手指捻著一塊冰糖到了的眼前,商寧秀下意識將臉往上一揚,穆雷就直接松手,讓那冰糖自己落進了的碗中。
“拿勺子攪一攪,不然下面甜得齁。”穆雷也沒再多做什麼多余的舉,就著大碗喝了一大口熱湯,就開始大快朵頤剛蒸好的牛包子。
商寧秀捧著瓷勺有一搭沒一搭地攪著,熱湯下肚讓手腳都回暖了些,緩緩咀嚼著紅豆,向男人打聽道:“那天藏在蘆葦里的那些蛇部落的人襲擊商隊殺了好多人,他們是經常會躲在那里打劫嗎?”
穆雷笑天真:“哪能經常,釣魚都還講究一個打窩,蛇又不是傻子,要是長期蹲守在那,以后哪還敢有商隊敢走這條路,久而久之了荒路,他們連西北風都沒得喝,必須得放上一陣子養養路,下一次才能再撲到食。”
商寧秀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我想也是……”
穆雷見那副深思模樣,嗤笑了一聲道:“我看你也沒被那陣仗嚇到多麼,下次還敢是吧?”
“嗯?”商寧秀眼神不自然地轉了轉,搖頭否認道:“你在說什麼,我只是在替那些人可惜,他們都是本分的生意人,一輩子兢兢業業為了養家糊口,就這麼被殘殺在了草原上,連尸骨都沒人收。”
若說是否還敢逃跑,商寧秀捫心自問必然還敢,堂堂郡主,即便再驚嚇,心中所愿也不會被輕易磨滅,只是經此一役,明白須得靜待一個萬全的好時機,輕易不能以涉險。
穆雷點著頭,也不穿,只自顧自說道:“是,不過現在中原許多人已經收市準備過年了,即便還有零星商隊,估著也就是賣點小玩意不會大面積采購,你那招數怕是不好使第二次。”
猜你喜歡
-
完結758 章

慕紅裳
個性活潑的女大學生謝家琪抹黑下樓扔個垃圾,不小心跌下了樓,再睜開眼,她發現自己變成了右相府的嫡小姐謝淑柔;榮康郡王正妃顧儀蘭絕望自裁,一睜眼卻發現自己回到了十四歲,一切都可以重頭再來。這一切的一切原本都與安國公家的小姑娘穆紅裳沒關係,紅裳怎樣都想不明白,她的人生怎地就從此天翻地覆……
123.8萬字8 6394 -
完結1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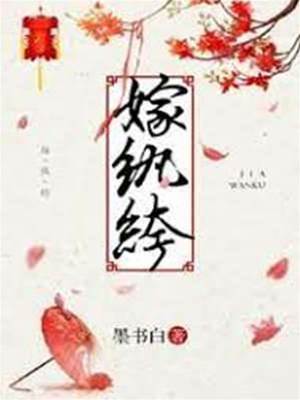
嫁紈绔
柳玉茹為了嫁給一個好夫婿,當了十五年的模范閨秀,卻在訂婚前夕,被逼嫁給了名滿揚州的紈绔顧九思。 嫁了這麼一人,算是毀了這輩子, 尤其是嫁過去之后才知道,這人也是被逼娶的她。 柳玉茹心死如灰,把自己關在房間里三天后,她悟了。 嫁了這樣的紈绔,還當什麼閨秀。 于是成婚第三天,這位出了名溫婉的閨秀抖著手、提著刀、用盡畢生勇氣上了青樓, 同爛醉如泥的顧九思說了一句—— 起來。 之后顧九思一生大起大落, 從落魄紈绔到官居一品,都是這女人站在他身邊, 用嬌弱又單薄的身子扶著他,同他說:“起來。” 于是哪怕他被人碎骨削肉,也要從泥濘中掙扎而起,咬牙背起她,走過這一生。 而對于柳玉茹而言,前十五年,她以為活著是為了找個好男人。 直到遇見顧九思,她才明白,一個好的男人會讓你知道,你活著,你只是為了你自己。 ——愿以此身血肉遮風擋雨,護她衣裙無塵,鬢角無霜。
81.5萬字8.46 48442 -
完結283 章

代嫁太子妃
簡介: 一朝穿越,她成了出身名門的官家小姐,青梅繞竹馬,卻是三人成行……陰差陽錯,定親時她的心上人卻成了未來姐夫,姐姐對幾番起落的夫家不屑一顧。她滿懷期待代姐出嫁,不但沒得到他的憐惜,反而使自己陷入一次更甚一次的屈辱之中。他肆意的把她踩在腳下,做歌姬,當舞姬,毀容,甚至親手把她送上別人的床榻……
23.2萬字8 10719 -
完結74 章

投喂病弱男配
陸云初一朝穿書,成了一個癡戀男主的惡毒女配,欲下藥強上男主,卻陰差陽錯地設計到了男主名義上的病弱弟弟頭上,最后不得不嫁給他。 書中這個n線男配就是個工具人設定,存在的意義…
26.2萬字8.38 1017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