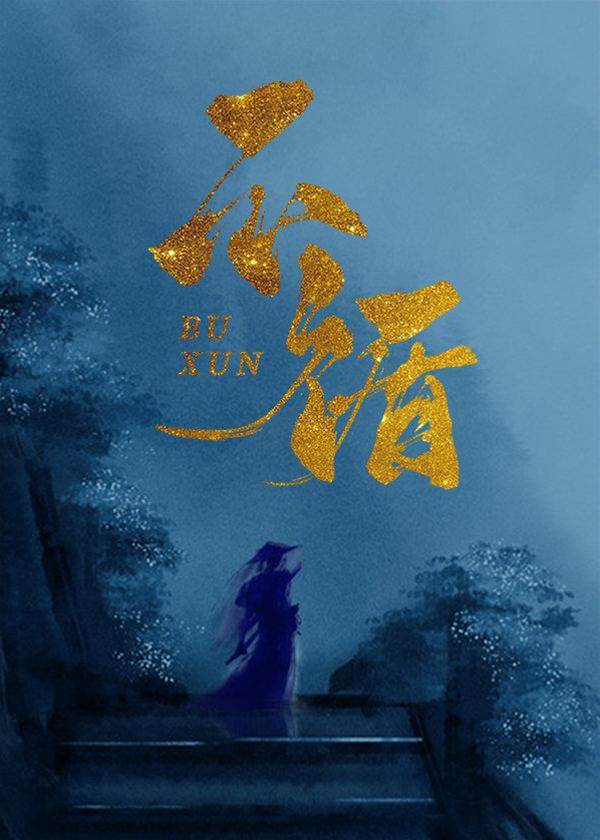《做太子侍寢的她逃了》 第35章
趙凜回頭看了馮效一眼,馮效立刻識知趣地跳上另一條船,無聲無息地遠離了這片蘆葦。
蘆葦裏靜悄悄的,趙凜輕輕劃了兩下船,就到了船邊。
毫沒有察覺,帕子敷在臉上任由風吹著。
趙凜見這模樣,突然起了玩心,從一旁摘下來一葦棒,在耳邊輕輕晃了兩下。
程玉酌搖了搖腦袋,好像在趕走耳邊的蚊子。
趙凜又用那葦棒在耳邊輕蹭,程玉酌終於有了明顯的反應。
開了口,懶洋洋的,“哪裏來的小蟲子?我要小憩,沒工夫搭理你,快走吧。”
趙凜一聽,愣了一下,旋即又笑了起來。
居然以為他是小蟲子。
被當做小蟲子的趙凜,又拿那棒在耳邊了。
程玉酌被擾得哼哼了兩聲,“我好不容易才找了這麽個清淨地,你又做什麽來打擾我?不是個好蟲子。”
手在耳邊扇了兩下,想把蟲子打走,可仍舊躺著不坐起來,還理了理麵上的帕子,讓帕子更實一點,“難得有這樣懶的時候,如今爹娘都不在了,師父老人家......也鞭長莫及啊。”
程玉酌說到這裏,笑了一聲,活像個從崔尚功了油吃的小老鼠。
趙凜平日裏見勤快,凡事親力親為,從不累苦,沒想到也會這般懶。
趙凜的心像被羽刮蹭過一樣,的。
他舍不得再拿那葦棒鬧,收回了手。
不曾想,卻自言自語起來。
“娘若是曉得我在這裏躲清閑,定然要說:”理了嗓子,了腔調,“‘阿嫻怎麽可以這麽懶?早知道就不取名阿嫻,改阿勤了!’”
程玉酌自說自笑了起來。
趙凜也在旁笑了起來,隻是他保持著沒笑出聲。
他可要好好聽聽,還能說出什麽話來。
這些話,他平日裏可聽不到!
他這樣想,程玉酌真就如了他的願,又嘀咕起來。
“若是師父曉得我躲清閑,肯定要板了臉,”正了正形,“‘在宮中可不能懶!你這樣的懶散子,也就勉強在人前糊弄糊弄,還是想方設法出宮去吧!’”
學著崔尚功的語氣,趙凜越發揚起了角。
隻是說完了,自己卻沒笑,沉默了一會兒。
“師父,玉酌真有些想您呢。隻不過,那皇宮我是再也不敢去了。”
趙凜斂了笑意,又聽低聲說了一句。
“那吃人的地方啊,但願我下輩子也不要靠近。”
趙凜一聽這話,像被人住了心頭,不悅地抿了。
可帕子覆在臉上,完全瞧不見他的臉,反而輕哼了兩句宋詞小調。
“小憐初上琵琶,曉來思繞天涯。不肯畫堂朱戶,春風自在楊花。”
趙凜一聽,更是不悅之心平地而起。
這小調最後兩句,正是說,楊花不肯進畫堂朱戶,在春風裏飄才最自在!
趙凜沒法說程玉酌這意思是錯的,可是他就是不高興,特別不高興!
趙凜回頭看了馮效一眼,馮效立刻識知趣地跳上另一條船,無聲無息地遠離了這片蘆葦。
蘆葦裏靜悄悄的,趙凜輕輕劃了兩下船,就到了船邊。
毫沒有察覺,帕子敷在臉上任由風吹著。
趙凜見這模樣,突然起了玩心,從一旁摘下來一葦棒,在耳邊輕輕晃了兩下。
程玉酌搖了搖腦袋,好像在趕走耳邊的蚊子。
趙凜又用那葦棒在耳邊輕蹭,程玉酌終於有了明顯的反應。
開了口,懶洋洋的,“哪裏來的小蟲子?我要小憩,沒工夫搭理你,快走吧。”
趙凜一聽,愣了一下,旋即又笑了起來。
居然以為他是小蟲子。
被當做小蟲子的趙凜,又拿那棒在耳邊了。
程玉酌被擾得哼哼了兩聲,“我好不容易才找了這麽個清淨地,你又做什麽來打擾我?不是個好蟲子。”
手在耳邊扇了兩下,想把蟲子打走,可仍舊躺著不坐起來,還理了理麵上的帕子,讓帕子更實一點,“難得有這樣懶的時候,如今爹娘都不在了,師父老人家......也鞭長莫及啊。”
程玉酌說到這裏,笑了一聲,活像個從崔尚功了油吃的小老鼠。
趙凜平日裏見勤快,凡事親力親為,從不累苦,沒想到也會這般懶。
趙凜的心像被羽刮蹭過一樣,的。
他舍不得再拿那葦棒鬧,收回了手。
不曾想,卻自言自語起來。
“娘若是曉得我在這裏躲清閑,定然要說:”理了嗓子,了腔調,“‘阿嫻怎麽可以這麽懶?早知道就不取名阿嫻,改阿勤了!’”
程玉酌自說自笑了起來。
趙凜也在旁笑了起來,隻是他保持著沒笑出聲。
他可要好好聽聽,還能說出什麽話來。
這些話,他平日裏可聽不到!
他這樣想,程玉酌真就如了他的願,又嘀咕起來。
“若是師父曉得我躲清閑,肯定要板了臉,”正了正形,“‘在宮中可不能懶!你這樣的懶散子,也就勉強在人前糊弄糊弄,還是想方設法出宮去吧!’”
學著崔尚功的語氣,趙凜越發揚起了角。
隻是說完了,自己卻沒笑,沉默了一會兒。
“師父,玉酌真有些想您呢。隻不過,那皇宮我是再也不敢去了。”
趙凜斂了笑意,又聽低聲說了一句。
“那吃人的地方啊,但願我下輩子也不要靠近。”
趙凜一聽這話,像被人住了心頭,不悅地抿了。
可帕子覆在臉上,完全瞧不見他的臉,反而輕哼了兩句宋詞小調。
“小憐初上琵琶,曉來思繞天涯。不肯畫堂朱戶,春風自在楊花。”
趙凜一聽,更是不悅之心平地而起。
這小調最後兩句,正是說,楊花不肯進畫堂朱戶,在春風裏飄才最自在!
趙凜沒法說程玉酌這意思是錯的,可是他就是不高興,特別不高興!
他在一旁鬱悶了一會兒,又聽程玉酌開了口。
“小蟲子,你是飛走了嗎?其實你在我耳邊繞兩下,也好的,就像靜靜一樣,也稍微顯得熱鬧一點,不至於太冷清,是不是?”
趙凜聽見這樣說,才又稍微舒緩了一下心,沒有在意把他比作蟲子和靜靜,又拿起了那棒,在耳邊了一下。
“咦?”程玉酌驚訝了,“你這小蟲子,能聽懂我說話不?”
趙凜沒忍住,又被逗笑了。
他靜默地笑著,棒在耳邊輕蹭。
程玉酌“哎呦”了一聲,更驚訝了,“真通人了,讓我瞧瞧.......”
邊說著邊坐了起來,揭開麵上的帕子,一眼瞧見了旁邊含笑看著的人。
話頓住了,人愣在了當場。
簡直就是一副驚的小貓的樣子,連眼睛都不會眨了。
趙凜隻覺得,那貓爪子在他心頭撓了一把。
“你怎麽在這?”程玉酌盡力下驚詫。
這才瞧見他穿了一亭臺樓閣暗紋的銀白錦袍,腰間的石珮甚是巧,而他腰帶束,越發顯得他腰實,而膛寬闊。
程玉酌連忙錯開目,這才發現他簪了一支白玉簪,程玉酌隻瞧了一眼,見那玉簪澤不同尋常,同他腰間石珮一樣的巧而質地不凡。
好似......宮中之?
程玉酌轉眼就被這兩見金玉寶貨吸引了。
趙凜見打量,還以為被自己神俊逸之姿吸引住了,抬頭任打量。
他可是一國儲君,風姿不是什麽人都能見到的!
這會他得讓好好瞧瞧!
卻沒想到突然問,“你那石珮和簪子倒是不錯,回頭能給我瞧瞧麽?”
趙凜一愣,差點氣暈過去。
他決定,以後再也不帶這些玩意了!
趙凜不回答,隻是定定地看著。
程玉酌終於從老本行金玉寶貨裏回過了神來。
趙凜定定看來的目,讓覺得比頭上的日頭還要熱!
不自在地想要別開去,隻是還必須鎮定。
問他,“你今日過來,是不是要替太子爺先行清理一遍大明湖?”
可趙凜還是不說話,不回答,仍舊那樣目灼灼地看著。
在那如日頭一樣灼熱的目下,程玉酌心跳快了起來,不僅快了起來,還下意識開始心慌。
側過臉去,別開他的目。
“你乘船過來多久了?”這麽一問,也提醒到了自己,“剛才那小蟲子......不會是你?”
程玉酌想到自己剛才嘀嘀咕咕那一番,登時尷尬起來。
不由地道,“你......是在聽我說話嗎?”
趙凜這才開了口,可是目仍然停留在臉上。
“是你自己要說,我可沒聽。”
他這麽說,程玉酌咬了。
明明是他裝作那小蟲子,才引了胡言語,他竟然還不承認。
程玉酌可看見他手下的葦棒了!
他這是睜著眼說瞎話嗎?
程玉酌暗氣,可也拿他沒辦法,要讓自己冷靜些,說句什麽把這一茬揭過去。
猜你喜歡
-
連載771 章

心有瑤光楚君意
陸瑤重生後,有兩個心願,一是護陸家無虞,二是暗中相助上一世虧欠了的楚王。 一不小心竟成了楚王妃,洞房花燭夜,楚王問小嬌妻:“有多愛我?” 陸瑤諂媚:“活一天,愛一天。” 楚王搖頭:“愛一天,活一天。” 陸瑤:“……” 你家有皇位要繼承,你說什麼都對。 婚前的陸瑤,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未來的皇帝老子楚王。 婚前的楚王,奸臣邪佞說殺就殺,皇帝老爹說懟就懟。 婚後的楚王扒著門縫低喊:“瑤瑤開門,你是我的小心肝!” 眾大臣:臉呢? 楚王:本王要臉?不存在的!
114.1萬字8 7666 -
完結16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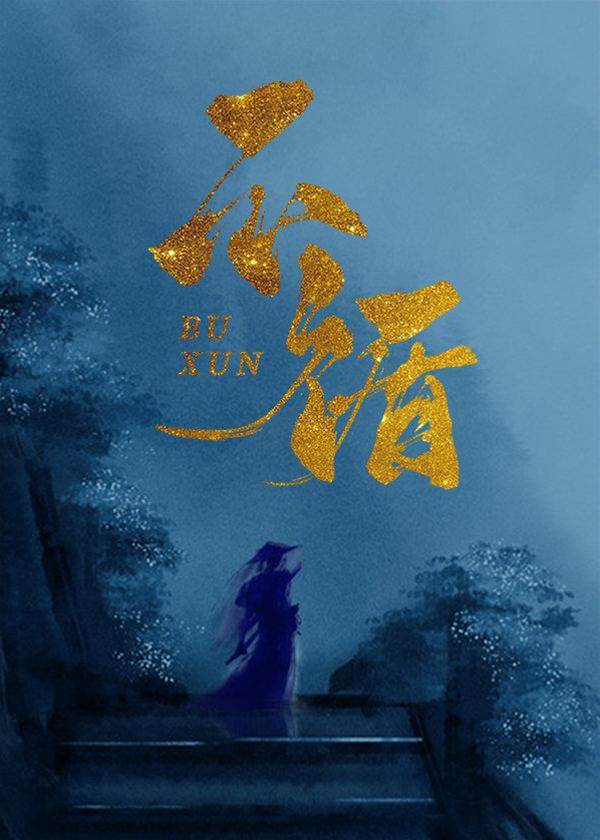
不循(重生)
邵循是英國公府的嫡長女。 父親是一品公侯,母親是世家貴女,宮裡的淑妃娘娘是她姑姑,太子之位的有力競爭者三皇子是她表哥。 人生中唯一的不足就是生母早逝,繼母不親,原本應該榮華富貴不缺,波瀾壯闊沒有的過完一輩子,誰知一場夢境打破了一切—— 邵循夢見自己的堂姑為了給兒子剷除對手,犧牲侄女的名節用以陷害風流成性的大皇子,害得自己清白盡毀,只能在鄙夷中被大皇子納為側妃。 大皇子風流成性,大皇子妃善妒惡毒,邵循醒來後生生被嚇出了一身冷汗。 誰知這夢做的太晚,該中的招已經中了,無奈之下決定拼死也不能讓噩夢成真,為了躲開大皇子,慌不擇路的她卻陰差陽錯的撞進了另一個人懷裡…… * 邵循清醒過來之後跪在地上,看著眼前繡五爪金龍的明黃色衣角,真的是欲哭無淚—— 這、這還不如大皇子呢! * 1雷點都在文案裡 2年齡差大 3請原諒男主非c,但之後保證1v1
49.3萬字8.33 4577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