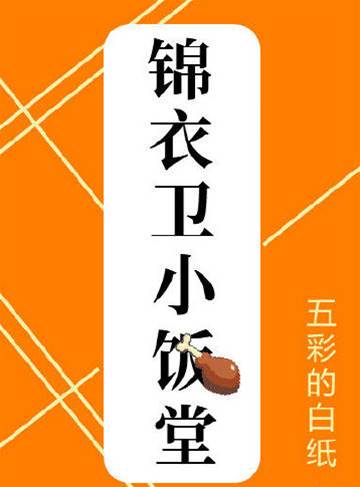《醫妃難囚:王爺請聽命》 第六百七十章 挽君閣下
「唉——」林醉柳重重地嘆了一聲氣,倒是也注意到了雪棠中央的那個冰棺。
「冰棺?」林醉柳有些驚訝,快步走了過去。
當然,也就直接看到了冰棺中,昏迷之中的淡晴宣。
「咳咳——」林醉柳正陷在對眼前冰棺的疑中,卻是聽見了後傳來輕微的咳嗽聲。
倉青!
林醉柳心裏一喜,卻是極其小心,輕手輕腳得走到倉青旁邊。
「小點聲兒!」林醉柳跟倉青打著手勢。
「沒事,可以放心說話,這個點兒,雪約莫已經是睡得很了。」倉青輕聲說道。
在雪棠也呆了有幾天,倉青倒是對雪的作息得徹。
不過想來這裏可是雪域,充足的睡眠是非常關鍵的,雪自然是懂得這個道理,所以作息什麼的都非常嚴格。
「現在可怎麼辦……」林醉柳一臉的無助。
既然倉青一直在裝暈,想必倉青比自己更加了解況吧。
「雪知道了鎮南王的份,一定不會輕易放過我們的。」倉青嘆了口氣。
林醉柳愣了下,旋即緩緩點了點頭。
正如國師所說的,南詔人天弱,但是雪不一樣,是從小就被灌輸著不同於其他家的思想,南詔因為南疆和北環開戰的往事,即便是沒有接過鎮南王,也是到了聞風喪膽的地步。
如今大名鼎鼎的鎮南王落在了雪手上,只會讓覺得,有一種把最強者握在了手心的覺。
若是不好好折磨一番,還真是對不起這個從小養起來的格。
想到這兒,林醉柳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氣。
這也太恐怖了。
「我繼續裝暈,你一定要盡量,拿雙生花和雪周旋。」倉青開口,拉回了林醉柳的思緒。
林醉柳點點頭,眼下,倒真是沒有比這個更好的方法了。
「雪給廖鑾喂的是什麼葯,你可知道?」冷不丁地,林醉柳倒是問起了廖鑾。
即便最終沒有拿到雙生花也無所謂了,只希,廖鑾快一點恢復正常。
「這……我倒是不知道,聞也聞不出來。」倉青無奈地說。
「連你都聞不出來。
」林醉柳震驚。
看來,這葯,也是非同尋常的。
「不過我倒是清楚,雪的藥材,都在哪間屋子裏頭。」倉青想了想開口道。
「哪間?」林醉柳聽見他的話,重新燃起了希。
「二樓,雪房間的隔壁。」倉青看了眼樓上,開口說道。
雪房間的隔壁……
林醉柳聽到后,一下子便像泄了氣兒的皮球,這說了和沒說等於一個樣兒,隔壁房間,怎麼下手都會被抓個正著吧。
一時之間,如何救出廖鑾的事,又陷了僵局。
挽君閣。
「來了南詔一圈,都沒有進去雪域,也太可惜了。」木惋惜唉聲嘆氣道。
跟孟郊塵兩人很是聽話,乖乖地在挽君閣落了腳。
至於為什麼能在挽君閣裏頭落腳,自然也是因為兩人出眾的樣貌了,木惋惜的易容,倒是在這兒徹底地派上了用場。
挽君閣之所以在南詔的名聲大,一方面自然是因為有富貴人家的公子哥常來,另一方面便是這挽君閣裏頭,頭牌的質量,是南詔別的任意一家,都比不了的!
因為挽君閣實施的是淘汰制,每天都在招攬新人,舊的不去新的不來,但凡這臉蛋兒上不小心收了大傷,或者是染了咽炎不能唱歌了,再或者始終是沒有金主點名的,通通都會被刷下去,繼而被新進的替代。
也正是因為這樣,孟郊塵跟淡晴宣就很自然地憑藉著外表的「天然優勢」,以兄妹的份,進到了挽君閣。
接客什麼的倒是不擔心,因為挽君閣主張的是頭牌們的質量,兩個人一進去,就得先打雜兩個月,而後再學習兩個月,方可選擇,是賣藝,還是賣。
如此嚴格的制度,沒有一個傾國傾城的容,挽君閣是不收的。
「是啊,天天在這挽君閣,看人兒都看膩了。」孟郊塵也說道。
他說的都是真心話,在挽君閣里好歹也呆了十幾天了,每天不僅能看到這挽君閣裏頭,歌舞已經非常練的頭牌和歌姬,也能看到日日進來的,容貌都極其貌的新人。
一天又一天,孟郊塵都看得乏了,兩人還是沒有找到接近那子的方法,挽君閣實在是管的太嚴格了。
「不會要等到為學徒吧?」木惋惜一陣哀嚎。
那可得再等上一個月!
那個時候,廖鑾他們應當也從雪域裏頭出來了,這樣一來,自己和孟郊塵呆在這挽君閣這麼久,還有什麼意義?還不如當初不來,乖乖地呆在北環研習的易容呢。
不過好在這只是木惋惜的隨便想想,最終,兩個人還是見到了那位子。
那日,舞臺突發事故,孟郊塵眼尖銳,立馬跳上枱子把那子給拽了下來,那子竟是當場嚇暈過去了。
老嬤嬤急於理那日不滿的客人,便暫時吩咐木惋惜和孟郊塵照看。
兩個人當時可是高興壞了,連忙抱起這子便往屋子跑。
「醒了?」終於是等到這子睜開眼,木惋惜激地撲上去,問到。
「嗯。」那子很是溫婉地點了點頭,看著木惋惜如此激,覺得很是尷尬。
「姐姐,你這模樣當真是絕了,倒甚是像南詔的前公主呢!」木惋惜直接說道。
時間迫,毫也不想周旋,能問點什麼出來便問點什麼吧。
那子的表有些不自然,但是也只是一瞬間。
「我這臉,倒還真的是按著章挽公主換的。」
「跟易容差不多,倒也很容易。」那子故作輕鬆地說道,看的表似乎並不太想過多提及這個話題。
「可南詔公主,應該不是你一屆草民,能隨隨便便就見得到的吧?」孟郊塵冷不丁地開口。
木惋惜不了解這子口中換臉,可是他恰好了解。
「與公子何干?我可是挽君閣的頭牌,公子尚且是個打雜的,連個學徒都不是,這樣質問我,若是老嬤嬤知道了,怕不是會將你兄妹二人趕出去呢。」那子裝作開玩笑的口氣,說出口的話卻是毫都不客氣
「哎喲喲,對不起姐姐,方才多有冒犯。」孟郊塵趕忙說道。
他可很是懂得見好就收的道理,若是再問下去把眼前這個人急了,說不好他還真的沒法跟木惋惜一起在這挽君閣裏頭待下去了。
「你……」木惋惜平生就最見不得這樣趾高氣揚,說話怪氣的人。
正要張口反駁回去,卻是被孟郊塵給牢牢實實地捂上了,拖走了。
「你沒看到剛剛那個樣子嗎,為什麼攔我?頭牌這麼了,本姑娘的易容,甩那張老臉十幾條街!」
進了屋子,孟郊塵一放開木惋惜的,就開始破口大罵道。
「我知道我知道……別衝。」看著木惋惜這個樣子,孟郊塵滿臉黑線,幸好自己一進屋子就趕忙把窗戶和門都關嚴實了。
就知道這丫頭方才憋了一大口氣。
其實孟郊塵心裏倒是不怕什麼所謂的老嬤嬤,只不過是有些害怕
「不是來找雙生花的,怎麼現在我們會繞到章挽上?」
「因為王爺大人的吩咐唄。」孟郊塵翻了個白眼。
在他看來,廖鑾對當年章挽的死,還是沒翻篇兒,特別是邊忽然又多了個口口聲聲說要為章挽討個說法的淡晴宣之後,封消寒也被帶了起來,這兩個人定是攪的廖鑾心裏更不安寧了。
孟郊塵到底是不了解,把廖鑾想的太脆弱了。
「會不會是看到了公主的畫像?」木惋惜忽然想了起來。
「換臉不比易容,僅僅看到畫像,是做不到的。」孟郊塵一口否定。
聽完他這句話,木惋惜臉上,倒是流出了一些欣和驚訝。
「小徒弟,什麼時候,到你來教我了?」戲謔地開口道。
「我之前四下流浪,聽得稀奇古怪的事多了些罷了。」聽到木惋惜這樣誇讚,孟郊塵卻只是心酸地笑了笑,沒有像往常一樣跟木惋惜開玩笑。
他只是說起這句話,忽然又想起了那一短孤獨又痛苦的日子。
看見孟郊塵忽然認真,木惋惜也不好意思地撓了撓頭,瞬間便收起了自己調侃。
「換臉必須要見到原臉的人,並且要那臉的主人的臉上的骨骼,說是換臉,其實也不是明面上的意思將兩個人的臉對換,而是用了一種和易容相似但是卻不是易容的方法,永永遠遠地改變一個人的容貌。」
「永永遠遠的改變?」木惋惜聽得有些驚訝了,自小便接易容,很難理解一個人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雖然易容也多多跟這樣的想法不開關係,但在木惋惜的心裏,髮之父母,木惋惜倒是從來沒有想過去永遠地改變自己的容貌,畢竟有易容,想短暫的變什麼樣子門都不在話下,可是如果要為了什麼徹底放棄原本自己的容貌,做不到。
猜你喜歡
-
完結272 章

重生之女將星
古語雲:關西出將,關東出相。 禾晏是天生的將星。 她是兄長的替代品,征戰沙場多年,平西羌,定南蠻,卻在同族兄長病好之時功成身退,嫁人成親。 成親之後,不得夫君寵愛,更身患奇疾,雙目失明,貌美小妾站在她麵前溫柔而語:你那毒瞎雙眼的湯藥,可是你族中長輩親自吩咐送來。隻有死人纔不會泄露秘密,你活著——就是對他們天大的威脅! 一代名將,巾幗英雄,死於後宅爭風吃醋的無知婦人手中,何其荒唐! 再醒來,她竟成操練場上校尉的女兒,柔弱驕縱,青春爛漫。 領我的功勳,要我的命,帶我的兵馬,欺我的情!重來一世,她定要將所失去的一件件奪回來。召天下,紅顏封侯,威震九州! 一如軍營深似海,這不,一開始就遇到了她前世的死對頭,那個“兵鋒所指,威驚絕域”的少年將軍。
110.6萬字8.38 44346 -
完結23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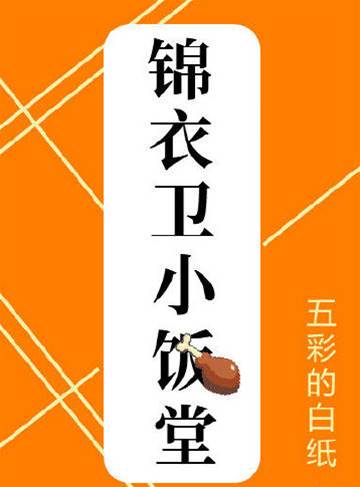
錦衣衛小飯堂(美食)
自從董舒甜到錦衣衛小飯堂后,最熱門的話題,就是#指揮使最近吃了什麼#錦衣衛1:“我看到夜嶼大人吃烤鴨了,皮脆肉嫩,油滋滋的,嚼起來嘎吱響!”錦衣衛2:“我看到夜嶼大人吃麻婆豆腐了,一勺澆在米飯上,嘖嘖,鮮嫩香滑,滋溜一下就吞了!”錦衣衛3:…
77.3萬字8.09 39090 -
完結678 章

快穿:在偏執男配心尖肆意撒嬌
【嬌軟撩系主神+瘋批病嬌男配+一見鐘情+甜寵1V1】都說:男主是女主的,男配是大家的。手拿虐文女主劇本的溫欣毫不猶豫撲進深情男配的懷里,“那邊的男主,你不要過來啊!”甜甜的愛情不要,傻子才去找虐!*霸道忠犬少爺拽著她的手腕,眸光猩紅:“不許去找他,你到底什麼時候才能回頭來看看老子?”君奪臣妻,狠厲暴君將她禁錮在龍椅上,癡迷地摸著她的臉:“天下都是朕的,夫人自然也是。
72.2萬字8 18626 -
完結282 章

國公夫人嬌養手冊/國公夫人嬌寵日常
小家碧玉、貌美身嬌的阿秀,嫁給魏瀾做了世子夫人。 魏瀾冷冰冰的,阿秀以爲她這輩子都要當個擺設,世子爺卻越來越喜歡來她的房裏,隨皇上去行宮也要帶上她一起去泡湯池。 國公府裏好吃好喝,還有世子爺百般寵着,阿秀過得像神仙一樣快活,順風順水當上了一品國公夫人,兒女也個個有出息。 直到最後,阿秀才發現魏瀾還藏了一個天大的祕密!
45.1萬字8 38862 -
完結206 章

賠罪
施綿九歲那年,小疊池來了個桀驁不馴的少年,第一次碰面就把她的救命藥打翻了。 爲了賠罪,少年成了施綿的跟班,做牛做馬。 一賠六年,兩人成了親。 施綿在小疊池養病到十六歲,時值宮中皇子選妃,被接回了家。 中秋宮宴,施綿跟在最後面,低着頭努力做個最不起眼的姑娘,可偏偏有人朝她撞了過來,扯掉了她腰間的白玉銀環禁步。 祖母面色大變,推着她跪下賠禮。 施綿踉蹌了一下,被人扶住,頭頂有人道:“你這小姑娘,怎麼弱不禁風的?” 施綿愕然,這聲音,怎麼這樣像那個與她拜堂第二日就不見蹤影的夫婿?
33.9萬字8.18 406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