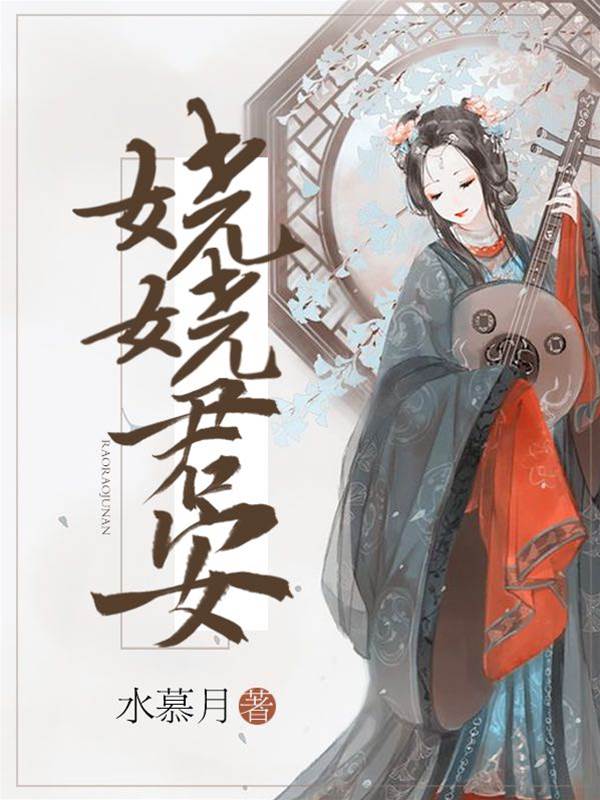《云鬢亂》 第 35 節 入骨歡
我甚是疑,只坐在黃花梨雕的高凳上,四打量,雙腳還不到地,懸在空中來去。
小蓮一邊哭,一邊替我梳頭,口中道:
「新帝登基,大赦天下,予娘娘以厚葬,準咱們搬出戒宮。十二年了,主子在天之靈總算能瞑目了。」
「陛下?」我隨口問。
小蓮點點頭,又低聲音:
「陛下是先帝最小的皇弟,便是公主的皇叔。」
我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小聲學著念了一遍:「皇叔……陛下……」
搬出戒宮對我來說,是一樁樂事兒,如此,我便能明目張膽地去苑摘花了,想想就高興。
三日后,我在麟合宮里頭一回拜見了陛下。
我自小生養在戒宮,十二年來從沒學過什麼規矩禮數,因此,覲見前,小蓮反復叮囑我見到陛下要行大禮,高呼「萬歲」。
我頗有些張,反反復復練了十來遍。故而一殿,便撲通一聲跪了下去,雙手高舉過頭頂,重重叩拜,大聲喊道:
「陛下萬歲,萬歲,萬萬歲!」殿一時寂靜無聲。
片刻后,大概是被我稽的模樣逗樂了,遠遠竟傳來朗朗笑聲,連一旁引我的老太監也忍不住輕笑。
見我還跪在地上一不,他便忍不住低聲提醒:「公主,陛下在閣,咱還沒見著呢!」
我愣愣地爬了起來,只聽簾傳來人聲:
「宜,到朕這里來。」
我懼于天子威儀,垂著頭立在原,不敢彈。
直到陛下從閣出來,一路走到我跟前,我才迫不得已見著了他——這是除了定淵外,第二個能讓我瞧得出神的人。
哪里是皇叔呢?分明是哥哥的模樣。
我驚覺自己逾越,忙再度跪下:「陛下恕罪。」
「何罪之有?」
「……」我說不出來。
我只知道,小蓮說這句話很頂用,卻沒想到還有下一句。
不過這話的確很頂用,那日過后,陛下封我為臨華公主,將華宮賞給我住。
正所謂一榮俱榮,小蓮和定淵托我的福,亦離了戒宮,一個了華宮的掌事姑姑,一個了華宮里的監總管。
小蓮還得賜了個好聽的名字——妤蓮。
直奴才們羨慕他二人踩了狗屎運,咸魚也能翻。
可見,跟對主子有多要。
……
陛下圣諱,雖與定淵同歲,二人卻截然不同。
定淵溫文爾雅,眉目如畫;而他狡黠難測,眼眸流轉里皆是權,渾上下的威儀一點兒也不似未及的年。
可陛下待我很好,總將我當作親妹一般寵著,大概是他只年長我六歲的緣故。但我不敢逾矩,仍按照輩分,敬他為皇叔。
華宮里的日子快活極了,山珍海味、奇玩異寶……應有盡有。
逍遙自在地過了兩年,我漸漸覺得陛下看我的眼神奇怪得很。
可我不敢想下去,想同定淵說,又開不了口,這一拖,就拖到了十四歲生辰。
陛下賞了我整整幾大箱華裳釵飾作為生辰禮,還非得讓我換上一套給他瞧瞧。
待我穿著藕荷的薄羅曳地自簾后走出,他竟已將宮人屏退。
乍見我,就從上到下打量了一番,隨即一步步走近,手朝我探來。
我大驚失,慌忙推開他,提起擺便跑了出去,一路哭著找到了定淵。
彼時,他正著我書房里的琴。我只會彈一首曲子,還是他教我的。
我從后一把摟住他,把頭擱在他背上,嚇得直哭,輕道:「定淵,我怕!」
我騙不了自己,我喜歡他,即便他是個奴才,是個閹人,卻仍是我的定淵。我已懂世事,自然明白公主上太監乃是天大的荒謬。
可我不怕,我只要他帶我走,去哪兒都好。
往日里,我遇著害怕的事兒,定淵總會說:「公主別怕,我在這兒。」
可那日,他只靜靜同我說:「公主,請自重。」
我難以置信,半晌,才緩緩松開抱著他的手,兀自拭去眼角的淚,轉離去。
4.
自那之后,我怕極了蕭寰,再不敢抬頭看他,只恭恭敬敬地喚他一聲陛下。
蕭寰倒一切如舊,再未近我分毫。華宮年久失修,他便大興土木,建青襲閣,造環華廊。讓我盡這天底下最尊貴的待遇,連他的皇后也要忌我三分。
可我知道,那是蕭寰為困住我而設的局,就像那九轉十八彎的環華廊,我怎麼也繞不出去,常要在廊上迷路。定淵,了我唯一的指。
「定淵,帶我走好不好?」
「定淵,我們回戒宮去好不好?」
「定淵,我怕……」
如此得來的,卻只有他一句話:
「公主,謝福只是一介奴才,沒有通天的本事。」
元延三年,我及了笄。妤蓮一早替我行了笄禮,為我綰發髻,戴上釵冠。
直至禮畢,也不見定淵。我猜他約莫是刻意回避,可他本不必如此,他是我心悅之人,自該看著我及笄。貢酒甘洌,也解千愁,我拉著妤蓮同飲,倒是先喝得大醉。
我只微醺,伏在妝案上側頭瞧著定淵映在門上的影兒,瞧了許久竟睡著了。再醒來,我還伏在妝案上,開口喚了幾聲「妤蓮」卻不得回應。我心道,醉得實在厲害,大概還未清醒。
直起時,面前的銅鏡里赫然印出了蕭寰的影,他就坐在后頭的圓桌旁,靜靜瞧著我,眉梢眼角含著幾分戲謔。
「陛下……」我只覺
自己的聲音都是抖的。
他徑自起行至我后,對著銅鏡看了許久,才低下頭來,湊到我耳畔低語:「宜終究長大姑娘了。」
我渾一便躲他,卻蕭寰牢牢按住。
「別。」
白日里妤蓮替我戴上的那支和田玉梨花簪他隨手走,任由滿頭青披覆。
我不傻,自然明白這一年來蕭寰未近我,不過是在等我長。
我早猜到有這一日,可未曾料到它來得這樣快。
「陛下!不可以,這不對!」我哭著掙他,在閣四躲竄。
他卻似閑庭信步,悠哉地笑著,看盡我倉皇模樣,仿佛料定我逃不出他的掌心。
半晌,他只問了我一句話:「那什麼才是對的?」
我說不上來,堪堪跪下,喚了他一聲:「皇叔!」
蕭寰不喜歡聽我如此喚他,即便是從前,他也不準我這般,只準我喚他陛下。我一時糊涂拂了他的逆鱗,驚覺時,已被他拽住拖到了榻上。
他將我制在下,指引我去看玉枕旁的香囊——竟是我當年繡的。
「朕在苑初見你時,你方才六歲,朕等了你九年。」
我忽地想起那年在苑瞥見的那雙玄錦靴,這些年里,我怎就未曾想到,能腳踏蟒紋,深夜仍在昭宮伴駕的,便只有當時年,未及出宮開府的蕭寰了。
蕭寰圖謀多年,早已失了耐,手便扯開我的裳。
我掙不開他,只能撕心裂肺地喊:「定淵,救我!定淵,救我……」定淵就守在門外,人影兒還印在門上,卻自始至終也未過半步。
這指,終是斷了。我再喊不出一句話來,只默默淌下一滴淚,說不清是疼,還是哀。
蕭寰見我哭了,便用指腹替我將淚拭去,輕聲道:
「無用的,別喊了,奴才永遠都是奴才。」
我已不記得他折磨了我幾遭,哭著暈過去了一回,醒時,他還在,再醒,天亮了,枕旁已空無一人。
我又見到了妤蓮,卻撲倒在我榻前哀泣:
「公主!這究竟是造了什麼孽!」
孽?大概是我前世做盡了喪盡天良之事,今生才得來如此報應。
我支起一副殘軀,才見定淵亦垂首立在閣中,手里端著一碗熱騰騰的湯藥。
他不敢看我,一步一步挪過來跪在了我的榻旁,舉著碗的手抖得厲害。
「公主,喝下這避子湯,才能不留禍。」
「呵!」我一把將碗奪過,揚手潑到了他臉上。
藥滾燙,必會傷人,但他沒躲,只咬牙忍下。
「那畜生呢?」我再不看他,轉頭問妤蓮。
聽聞「畜生」二字,嚇得忙捂住我的,「公主切莫胡言語!」我推開的手,別過頭去,見那支梨花簪子靜靜躺在地上,已碎作兩半。
5.
我如今才知道,青襲閣背靠麟合宮而建,地下暗通,能供人悄無聲息地在兩宮間來去。
怪不得蕭寰要大興土木,重修華宮。
而那些修鑿暗道的工人已被蕭寰盡數死,畢竟,在世人眼里,他是個明君,注定要名垂青史。他又怎會縱容我為他的污點?
如今,昭宮里知道這樁齷齪事的,便只有妤蓮、定淵和蕭寰的監。
有了第一次,便會有第二次、第三次……
我了一面照妖鏡,照出蕭寰心底的晦。他在我上使盡了不曾用過的手段,只因我是他養在暗,能供他為所為的人。
猜你喜歡
-
完結1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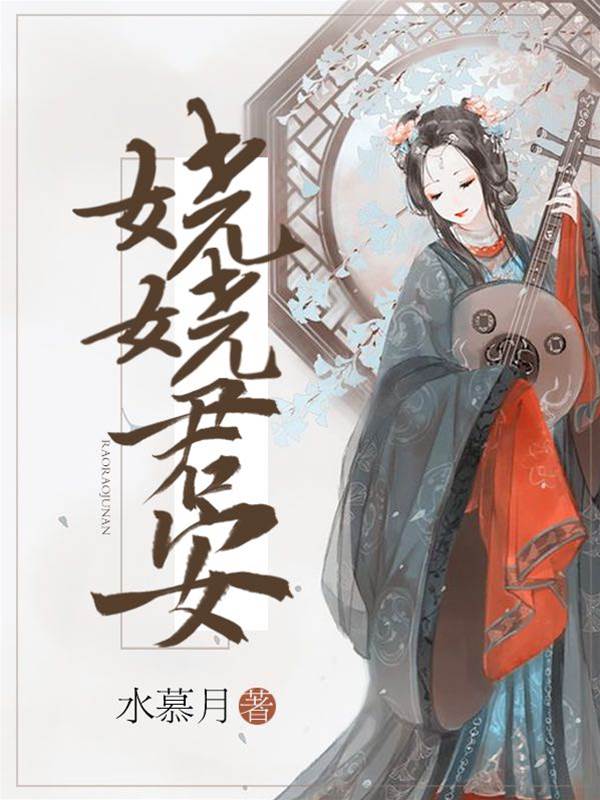
嬈嬈君安
原想著今生再無瓜葛,可那驚馬的剎那芳華間,一切又回到了起點,今生他耍了點小心機,在守護她的道路上,先插了隊,江山要,她也絕不放棄。說好的太子斷袖呢!怎麼動不動就要把自己撲倒?說好的太子殘暴呢!這整天獻溫情的又是誰?誰說東宮的鏡臺不好,那些美男子可賞心悅目了,什麼?東宮還可以在外麵開府,殿下求你了,臣妾可舍不得鏡臺了。
16.6萬字8 14001 -
完結244 章
綺夢璇璣
腹黑王爺與烏龜美女大PK。過程輕鬆小白,結局保證完滿。美女,身爲一代腹黑大BOSS的王爺趙見慎見得多了,沒見過謝璇璣這麼難搞定的…利誘沒有成效,雖然這個女人愛錢,卻從不肯白佔便宜。送她胭脂花粉首飾珠寶,拿去換錢逃跑。甚至許以王妃身份她都不屑一顧。色誘是目前看來最有效的,可惜還是次次功敗垂成。對她溫柔,她懷疑他有陰謀。對她冷淡,她全無所謂。對她刁難,基本上都無功而返,任何問題到了這個女人面前都會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解決。這個女人對他的迴應就是一句:“除了金銀古董,別人用過的東西我都不要!”
53.8萬字8 265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