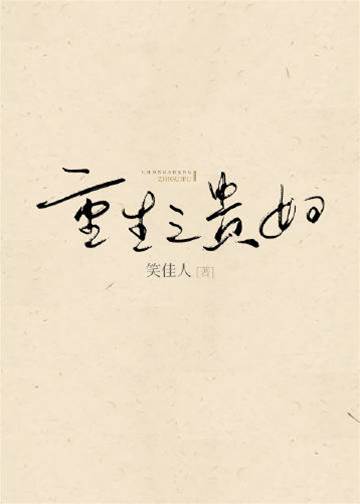《心尖意》 第1節
第一章
客舍輕薄的窗紙上映出一道側影,虛幻朦朧得不甚分明。
天剛亮不久,室昏暗。窗邊站著的影一,抬手推開道窗看出去。
客舍太小,窗外即是外院,院牆外則是一片直撲眼簾的蒼茫天地。
春三月,這片天地裏卻看不見什麽綠,遠橫亙黃塵古道,道側倚靠群山莽原,遠接蒼穹,籠蓋四野。
隔著帷帽垂紗深吸了口氣,風很大,許久沒有這樣自由地吹過風,也沒這樣行過遠路了,直至風肺腑,涼徹心扉,才有了一實。
待這陣風過去,目看向客舍院——
當中一輛馬車,左右各一小隊牽馬佩刀、著短打的隨從。院門口領隊的被他們稱作番頭,一臉絡腮胡,牽一匹壯的棗紅大馬,一樣做短打裝束,裏嘰裏咕嚕地在數落著什麽,大約是在嫌棄路途遙遠。聽不清楚,隻覺得煩躁,移開眼,又瞧見剛牽出來的幾匹矮種馬,其後跟著的都是婢,個個以薄布遮著麵擋風,好多捧著行李邊走邊打瞌睡,醒著的也是昏昏沉沉。
這支出行隊伍護前行,總共不足二十人,以如今份,卻能說是排場盛大了。
心中自嘲著,剛要去看對麵客房,驀然天邊遊蛇電閃,繼而“轟隆”一聲驚雷巨響。院牆外有什麽“嘩啦”斷裂,焦黑冒火地直直下墜,掃落牆頭瓦片砸進院中,“啪”地帶出一陣塵煙。
頓時四下驚,隨從們紛紛按住驚懼奔的馬匹,打盹的婢也被驚醒,接連慌驚。
“啐!什麽鬼天,馬上就要上路,竟大白日驚雷!”番頭扶一下腦袋上的襆頭,拽住馬韁朝天大罵,轉頭又嗬斥婢,“都閉!不過是一樹枝被劈斷了,什麽!”罵完了他猶不解氣,丟開馬過去,一腳踢開那焦黑的樹枝,“說來就來,嚇了老子一跳!”
舜音往右側著近窗口,手指還搭在推開的窗上,聽見番頭那幾句大聲的咒罵,竟牽了下角。
真是應景,人生在世,有時突然發生的事也堪比白日驚雷,就如眼下這樣。
“去,還不去看看那位新夫人!”番頭大聲指使婢,一邊就要扭頭朝客房看來。
舜音先一步拉上了窗。
一個婢慌忙跑來,推開客房門,看見舜音端正站在窗邊,頭戴帷帽、垂紗遮臉,連擺都分毫未,驚魂未定地問:“方才那麽大的靜,夫人竟沒驚到嗎?”
“沒有。”舜音聽在耳裏並不覺得那有多響。
婢隻覺得不可思議,看了好幾眼,才帶上門退出去了。
“讓開!阿姊!”有人自外大步過來,一路呼喊著到了客房門前。
一片忙嘈雜裏,番頭更沒好氣:“行行行,等一下再走!讓封郎君先好好問候去!”
客房門又被推開,來人進門前還拍了一下門框,像是怕舜音注意不到似的:“阿姊!”
舜音抬頭看見他,把帷帽摘了。是弟弟封無疾。
方才朝對麵客房看時沒見到他,便猜他一定是避著外麵這群人,果然是,這一路他都這樣,不願與那群人接近。
封無疾快步走近,上青衫微皺、披風歪斜,料想剛剛也了些驚,一到跟前先湊近看了看左耳,關切問:“方才沒有不舒服吧?”
舜音抬手攏了一下耳邊鬢發:“沒事,他們不知道我的形,你又不是不知道。”
封無疾走到右側,推窗看看外麵,見番頭已領人去客舍外觀天氣,婢們與剩下的人也去整車了,拉好窗戶,才回頭放心說話:“阿姊,眼下可是已經過會州了。”
舜音點了點頭:“嗯,遠離長安已有千裏之遙了。”
封無疾陡然急了:“你隻說這個?倒像是不知道你此行是要去做什麽的!”
舜音說:“知道,去嫁人。”
“……”封無疾被輕飄飄的語氣噎了一下。
不錯,確實是去嫁人的。他這個當弟弟的一路跟到這裏是送嫁的,外麵那一群人都是遠道來迎親的,否則怎會一口一個“夫人”的。
封無疾都因此氣一路了,不願聽那“夫人”的稱呼,能避則避,此刻已行到此,實在忍不了了:“按這行速,再往前就會進關口,然後便直往涼州去了,你這一路就如此不在意?”
舜音反問:“如何在意,難道這樁婚事我能拒絕?”
“……”封無疾又被噎住,悻悻地拂了一下袖。
前月涼州總管忽然派人遠來長安向封家提親,說要為下屬求娶良配。
從未有過這種事,以往嫁娶之事隻聽過父母之命妁之言,哪見過上首員要為下屬安排婚配的?
可涼州總管勢大,治所涼州城繁華富庶直追二都,又下轄十四州河西要地,更兼統西域諸國。如此封疆大吏,帝王尚要側目,豈敢有人小覷?他要如此行事,又有誰敢質疑?
封無疾當時隻覺得古怪,連番追問派來的人緣由。
對方回答:總管認為河西之地盛行胡風,涼州城雖也繁華,子可遠沒有東西二都的閨秀知書達禮。早聞渤海封氏有尚未出嫁,正是天賜良緣……
怎麽聽都像是一番早就背好的客套話,行雲流水都不帶打頓的。封無疾再往細了問,對方就什麽都不說了。
沒幾日,竟連今聖也得知了此事。
據說涼州總管特將此事上奏聖聽,自稱心向二都,奈何地偏僻,恨自己無適齡婚配兒,更不敢高攀皇室宗親,隻得以下屬代之,願為其求娶二都好,如此也算得蒙聖恩、澤被西北,以一段佳話……
佳話雖好,隻是沒想到會落在封家頭上。
聖人倒沒裁決,隻讓封家自行決定。然而這樁婚事封家確實無法拒絕,隻因封家早已不比當初。
何止不如當初,甚至連平民百姓也不如了……
但封無疾仍是不忿,著聲,幾乎已湊到舜音耳邊:“河西一帶可不是溫善之地,你看看方才那說變就變的天就知道了。而且他們前月提親,次月就派人來接,涼州距長安可不止千裏,明擺著他們是料定我們無法拒絕,接的人跟著人就來了!下聘匆忙,走禮草率,這些也都不說了,新郎竟也不麵!好歹你也要問問到底是要嫁給誰啊!”
舜音聽他一口氣發泄完,竟笑了:“問了又如何,我如今這樣,還能挑誰?”
“……”封無疾憋悶地臉都青了,對著這笑臉卻又沒法再說下去。
“婚書在母親那裏,”舜音忽然道,“自然知道我要嫁給誰,都同意了,還有什麽可說的,料想總不至於要讓我嫁給一個行將就木的廢人。”
封無疾皺眉不語。他們的母親對這樁婚事所言甚,也不讓他多管,他追問了好幾次都是被訓斥,不了了之。
婚書已換,其實已然禮,再計較這些早沒意義。這事突然而至,母親和舜音卻都冷靜得很,隻有他一個人最不平。
不是不能嫁人,他隻是不舍他阿姊嫁得這麽委屈罷了,已經很不易了。
舜音在桌邊坐下,扯了下手上帷帽,垂眼,目落在擺上,忽又問:“此番離開長安前,母親可有什麽話給我?”
封無疾七八糟的思緒一頓,臉忽而訕訕起來,默默退開些,在一旁坐下。
舜音抬頭看了看他的臉,神黯了下去:“我猜猜,料想母親說的是:‘也總該有用一回了’,是不是?”
“你怎……”封無疾下意識就要說“你怎麽知道”,說一半生生改口,“你怎麽能這麽想呢……”說完渾不自在。
舜音臉白淡,一言不發。
與母親關係冷淡已久,這些年也不與家人住在一,一直獨居長安城郊。甚至此番出嫁,母也不曾相見,更無半分溫脈脈地相送。-思-兔-網-
封無疾知道眼力素來敏銳,忽然有些後悔來說這些了,本已不易,又何必再惹得心中不舒坦。畢竟這婚事怎麽看都像是母親隨手就將推出去送人了……
屋沒了聲音,外麵番頭已回來了,不耐煩地高嚷:“行了嗎?沒雷沒雨,還走不走了!涼州可還沒到呢!”
封無疾剛忘卻的火氣“蹭”一下又竄出來,恨恨地對舜音道:“涼州涼州!當初連涼州武威郡公家的婚事你都拒過,如今不過一個下屬員倒橫起來了,涼州當初我們就不稀罕!”
舜音心緒一斂,忽被他的話勾起了久遠的回憶,還沒來得及細想又全下了心底,擰著眉打斷他:“可是不在當初了,現在得稀罕了。”
封無疾撇了下,終是悶頭起出去了。
舜音輕吐一口氣,起將帷帽重新戴上,取了桌上的一隻綠錦包袱,緩步出門。
外麵早已恢複如常,番頭坐在馬上揮手催促,眾人都在上馬。
如這路上的每一日一樣,在眾人注視下登上車。
猜你喜歡
-
完結181 章
鳳隱天下
洞房夜,新婚夫君一杯合巹毒酒將她放倒,一封休書讓她成為棄婦!為了保住那個才色雙絕的女子,她被拋棄被利用!可馳騁沙場多年的銀麵修羅,卻不是個任人擺布的柔弱女子。麵對一場場迫害,她劫刑場、隱身份、謀戰場、巧入宮,踩著刀尖在各種勢力間周旋。飄搖江山,亂世棋局,且看她在這一盤亂局中,如何紅顏一怒,權傾天下!
17.9萬字8 42896 -
完結418 章
鳳逆九天:一品毒妃傾天下
她是將軍府的嫡女,一無是處,臭名昭著,還囂張跋扈。被陷害落水後人人拍手稱快,在淹死之際,卻巧遇現代毒醫魂穿而來的她。僥倖不死後是驚艷的蛻變!什麼渣姨娘、渣庶妹、渣未婚夫,誰敢動她半分?她必三倍奉還。仇家惹上門想玩暗殺?一根繡花針讓對方有臉出世,沒臉活!鄰國最惡名昭著的鬼麵太子,傳聞他其醜無比,暴虐無能,終日以麵具示人,然他卻護她周全,授她功法,想方設法與她接近。她忍無可忍要他滾蛋,他卻撇撇唇,道:“不如你我二人雙臭合璧,你看如何?”【情節虛構,請勿模仿】
109.7萬字8 73357 -
完結2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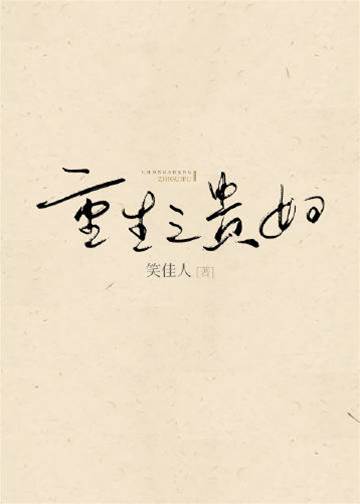
重生之貴婦
人人都夸殷蕙是貴婦命,殷蕙也的確嫁進燕王府,成了一位皇孫媳。只是她的夫君早出晚歸,很少會與她說句貼心話。殷蕙使出渾身解數想焐熱他的心,最后他帶回一個寡婦表妹,想照顧人家。殷蕙:沒門!夫君:先睡吧,明早再說。…
66.6萬字8.71 18701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