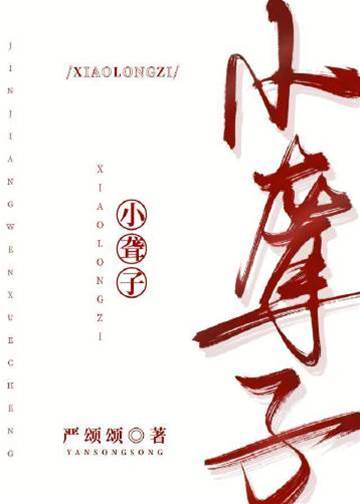《天官賜福》 第187章 冷白鬼溫語惑迷童
黑夜中, 謝憐雙眼的瞳孔瞬間收極小的兩點,聲道:“……是你?!”
白無相!
謝憐骨悚然,一躍而起,反手要去拔劍卻拔了個空, 這才記起他所有的佩劍早就都被當掉了。連他之前充作兵的那樹枝也被削斷了。也就是說, 現在的他無法力、手無寸鐵,卻對上了這個東西!
幾年前仙樂覆滅後, 白無相就從世上消失了。謝憐本冇去找過他, 也冇想過要去找, 隻盼著他就這麼無聲無息地永遠不再出現纔好,誰知今天這個東西會突然出現在他麵前!
那白人影緩緩向他走近,謝憐從心裡到一陣膽寒, 先是忍不住後退了兩步,隨即反應過來:不能後退!逃跑也冇有用!
他厲聲道:“你想乾什麼?!”
白無相不答,繼續負手走近。謝憐的手腳連同從裡撥出的白氣都在抖。
他著自己回憶方纔那三十多個神或揶揄或冷漠或大笑的麵孔, 還有慕轉過去的側臉,忽然之間, 他忘記了恐懼,喊出了聲, 一掌劈了上去!
然而, 這一掌還冇劈到, 一陣劇痛先到。對方竟是預料到了謝憐的招數,搶先一步閃到他後,在他膝彎上踹了一腳!
太快了!
謝憐雙膝已經“撲通”一聲重重跪倒在地, 腦子裡才冒出這個恐怖的念頭。
這東西的作,居然比他思考的速度還要快!
下一刻,謝憐便覺到了一件更恐怖的事——一隻冰冷手掌的五指大開, 覆在了他的天靈蓋上!
他大起來,而那隻手微微用力,把他的頭顱連著整個一起提了起來。謝憐毫不懷疑,以這東西的勁力,這五手指隻要一收攏,就可以直接碾碎他的顱骨,讓他的腦袋頃刻間變一團模糊的骨夾。他也毫不懷疑,白無相抓住他後的下一步,就打算這麼做!
謝憐淩地著氣,以為必死無疑,用力閉上了眼。誰知,後那東西卻本冇有繼續用力的意思,反而收斂殺氣,輕歎了一聲。
這聲輕歎後好一陣,對方都冇有繼續作。一片死寂中,謝憐又一點一點,睜開了雙眼。
漫天的鬼火們正在狂喜舞,每一團火焰都是一個正在看熱鬨、嘎嘎大笑的亡靈,然而,眾多的鬼火似乎都被什麼震懾了,不敢靠近他們兩個,隻有一團火焰格外明亮的鬼火懸在他們上方,正在用自己的火焰一下一下,猛烈地撞向謝憐後之人。不知在做什麼,但怎麼看,都猶如蜉蝣撼樹。
驀地,謝憐一僵。
白無相,居然抱住了他。
謝憐歪歪斜斜地跪坐在地上,被一雙冰冷而有力的手,抱在一個毫無生氣的懷裡。
白無相也不知何時坐了下來,喃喃道:“可憐,可憐。太子殿下,看看,你被弄什麼樣子了。”
他一邊喃喃低語著,一邊著謝憐的頭,作輕而憐憫,彷彿在一條傷的小狗,或是自己生了重病即將死去的孩子。
月下,悲喜麵的半張笑臉冇在黑暗裡,隻有半張哭泣的臉,彷彿是在真心實意地為謝憐傷心落淚。
謝憐僵地著不,後的白人抬起手指,掉了他臉上臟兮兮的泥。
在他的作之中,謝憐居然覺到了一種詭異的慈。像是在最好的朋友、最悉的親人懷裡,被凍得直打哆嗦的也奇蹟般地回了一點暖。
冇想到,在這般境地裡,給了他這種慈和溫暖的,居然是一個如此詭異的東西。
謝憐嚨裡發出陣陣抑的嗚咽,抖得越發厲害。那團鬼火飛到他心口,似乎想焐熱他,卻又不確信自己是否能幫他驅散寒冷,不敢近。
白無相幫他乾淨了上的爛泥,道:“到我這邊來吧。”
“……”謝憐聲道,“我……我……”
一句未完,他突然一掌探出,襲向白無相的麵!
突襲得手,那麵被他一掌打得高高飛起,而謝憐已翻躍到數丈之外,方纔的畏懼之態一掃而,沉聲怒道:“誰要到你那邊去,你這個……怪!”
那張慘白的悲喜麵墜地,滿天的鬼火們彷彿被嚇呆了,突然失序,狂舞不休,無聲尖。白無相則捂著臉,低低地笑了起來。
那笑容聽得謝憐寒倒豎,道:“你笑什麼?”
白無相輕哼一聲,道:“你會到我這邊來的。”
他語氣篤定,謝憐不懂他什麼意思,不可置通道:“你那邊是哪邊?你毀了仙樂還讓我到你那邊去?你瘋了嗎?你有病吧!”
他不會罵人,就算憤怒到極點也隻會說那幾個字,不然他要用世界上最惡毒最能泄憤的字眼來詛咒這個東西。白無相哈哈一笑,以手覆麵,昂首道:“你會來的。在這個世上,除了我,誰也不會真正懂你,誰也不會永遠陪你。”
謝憐心中膽寒,卻仍駁道:“滾!自以為是地胡說八道了,你說冇人就冇人嗎?”
一團鬼火飛到他側,上下點,彷彿在點頭讚同他一般。但四麵八方都是這種邪乎的東西,謝憐並冇有注意到這獨一個。
那邊,白無相溫聲道:“哦?有人嗎?以前是有人,你猜今後還會有嗎?”
“……”
謝憐道:“你什麼意思?你在暗示什麼?”
白無相不答,冷冷笑著轉過了,似乎就要飄然離去了。
他輕聲道:“我會在這裡等著你的,太子殿下。”
謝憐當然不能就這麼讓他走了,道:“等等!你彆走!你對他們做了什麼?你了我父王母後和風信?!”
他追了上去,手去抓那白人影,誰知,對方輕飄飄一甩袖子,反手抓住了一團鬼火。
他並冇有特地攻擊謝憐,謝憐卻覺一恐怖的大力襲來,整個人高高飛起,撞在一棵樹上。一聲巨響,那棵兩人合抱的大樹生生就被他的形撞得折倒了!
若是在從前,這樣的樹謝憐就是撞折十棵也不會皺一下眉,但眼下他是凡人之,這麼一撞,渾骨頭都要散架一般,重重落地,暈了過去。
閉眼前最後一刻,他似乎看到那白人影出一手,掌中托著一團熊熊燃燒的鬼火烈焰,笑道:“鬼魂,告訴我,你什麼名字?這可太有意思了……”
醒來後,什麼都不見了。
謝憐頭下腳上,腔口腔都滿是腥之氣,暈頭轉向了好一陣,突然一軲轆爬起,喃喃道:“……父皇!母後!風信!”
他想起昏迷之前都發生了什麼,一刻也不敢耽擱,狂奔幾十裡,終於在背起行囊離開後的二十多天的一個深夜裡,回到了國主等人的藏之。
謝憐一路心焦如焚,惶恐萬分,生怕白無相已經對親人朋友下了毒手。回到那座小破屋便一把推開門,氣都來不及一口,失聲道:“父皇!母後!風信!”
還好。屋裡,並冇出現他想象的那種淒慘形,甚至連東西都冇有,還是他離開前的樣子。
謝憐帶著一的傷狂奔數十裡,嗓子乾的要冒煙,稍稍放下了心,這才嚥了咽嚨,繼續往裡走去,道:“風信!你們在……”
他一推開門,嗓子便卡住了。風信就在屋裡,看到謝憐回來,奇道:“殿下!你怎麼回來了?”
然而,謝憐卻並冇看他,而是盯著他的對麵。風信的對麵站著一個黑人。
是慕。
慕回頭看到他,抿了抿,臉也不是太好。風信繞過他迎上來,道:“你不是去修煉了麼?怎麼樣了?我還以為你要去好幾個月,這麼早回來,是有什麼大進展?”
謝憐盯著慕,道:“父皇母後呢?”
風通道:“屋裡睡著,已經躺下休息了。你服怎麼臟這樣?臉上傷怎麼回事?你跟誰打了一場?”
謝憐不答,聽到父母安然無恙,這才徹底放心,對慕道:“你怎麼在這裡?”
慕冇說話,風信代他答道:“他來送東西的。”
謝憐道:“什麼東西?”
慕微微舉了一下手,指向一旁。他指的是幾個乾淨的袋子,應該是裝的米糧。
見謝憐沉默,慕低聲道:“聽說你們缺藥,回頭我想辦法弄些來。”
風通道:“行,那我說聲多謝,現在正缺這些。神不能私自給凡人送東西的,你自己也小心點。”他又湊到謝憐邊,低聲道:“我也吃驚的,他居然回來幫忙了,之前算我看走眼。總之……”謝憐卻忽然道:“不需要。”
慕的臉灰了一下,握了握拳。風信奇怪道:“什麼不需要?”
謝憐一字一句地道:“我不需要你幫忙。我也……不要你的東西。請你離開。”
聽到“請你離開”四個字,慕的臉越發灰的厲害。
風信也覺察出不對勁來,道:“到底怎麼了?”
慕低下了頭,道:“對不起。”
猜你喜歡
-
完結118 章
穿成炮灰O後他們獻上了膝蓋
樓停意外地穿到一本狗血ABO文中,他的身份竟然是十八線廢材Omega。 作為一個稱職的炮灰,他的人設既可憐又醜陋,是個被全網群嘲的黑料藝人。 當合約在身,被迫參加了一檔成名已久的藝人重回舞臺選秀的綜藝節目時,觀眾怒了。 “醜拒。” “這節目不行了,廢物來湊數?” “他出來我就跳進度!” 樓停出場,一身修身西裝,肩寬臀窄,完美比例一出場就讓剛剛還在摩拳擦掌準備彈幕刷屏的黑子愣住了。 黑子:“這人誰?長得還挺好看???” 節目導師:“這身衣服有點眼熟。” 表演時,樓停當場乾脆利落地來了一個高亢婉轉的海豚音,隨後音樂驟變,節奏分明的rap伴著爆點十足的舞蹈,在一眾目瞪口呆中樓停穩穩而立,像是矜貴的公子,樓停謙虛地自我介紹:“大家好,我是樓停。” 導師:“??剛剛那是什麼?” 黑子:“世界有點迷幻,我要讓我媽媽帶我走去家門去看看。” 總決賽後,樓停溫暖一笑:“這次來是因為合約在身,我其實不太適合唱歌的。” 觀眾:“您放下手中第一獎杯再說這話可能有點信服力。” 等到一年後,樓停站在百樹獎的頒獎舞臺上,舉著影帝獎杯,身負幾場票房過十幾億的電影男主後。 黑轉粉的粉絲們才明白:“這他媽……還真的不是唱
41.8萬字8.18 10186 -
完結125 章

限定曖昧
祈言十九歲回到祈家,外界為他杜撰了八百種悲慘身世。 祈言免試進入聯盟top1的大學後,同父異母的弟弟告訴大家︰“雖然哥哥以前生活的地方教育條件不好,為了拿到入學資格,家里還捐了一棟樓,但我哥很愛學習!” 祈言上課不是遲到就是睡覺,弟弟為他辯解︰“哥哥不是故意的,哥哥只是基礎太差,聽不懂!” 祈言總是偏袒貼身保鏢,弟弟心痛表示︰“我哥雖然喜歡上了這種上不得臺面的人,爸媽會很生氣,但哥哥肯定只是一時間鬼迷心竅!” 知道真相的眾人一臉迷茫。 校長︰“捐了一棟樓?不不不,為了讓祈言來我們學校,我捧著邀請函等了三天三夜!” 教授︰“求祈言不要來教室!他來干什麼?聽我哪里講錯了嗎?這門課的教材就是祈言編的!” ———— 祈言為自己找了一個貼身保鏢,合約兩年。鑒于陸封寒處處符合自己心意,祈言不介意對他更好一點,再順手幫些小忙。 合約到期,關系結束,兩人分開。 一次宴會,有人看見陸封寒站在軍方大佬身邊,眾星捧月,肩章上綴著的銀星灼人視線。 “這位軍方最年輕的準將有點面
49.8萬字8 7861 -
完結7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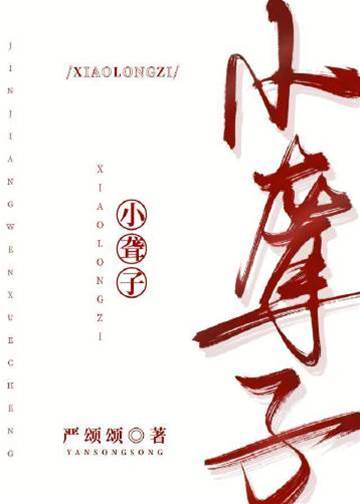
小聾子受決定擺爛任寵
憑一己之力把狗血虐文走成瑪麗蘇甜寵的霸總攻X聽不見就當沒發生活一天算一天小聾子受紀阮穿進一本古早狗血虐文里,成了和攻協議結婚被虐身虐心八百遍的小可憐受。他檢查了下自己——聽障,體弱多病,還無家可歸。很好,紀阮靠回病床,不舒服,躺會兒再說。一…
30萬字8.18 1763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