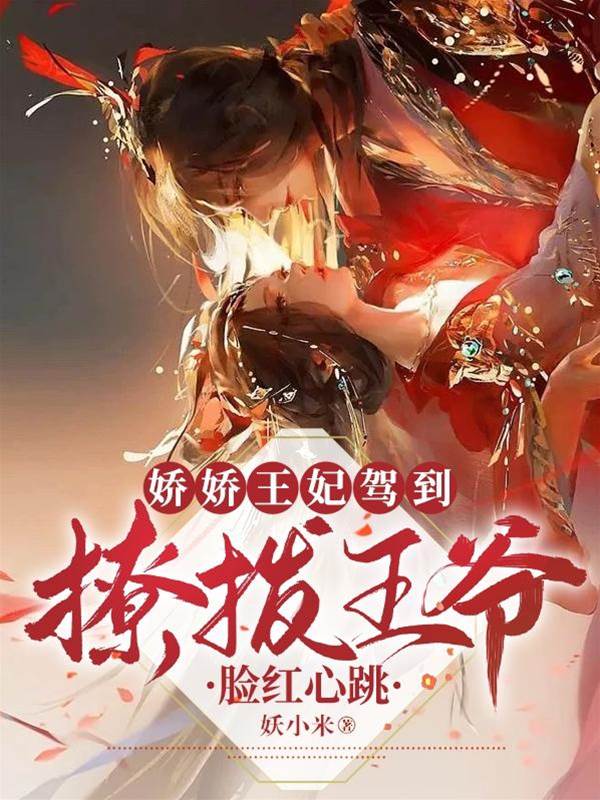《將軍榻上》 第196章 番外2·卿言與烏勒
·
卿言每天就想著逃跑。
烏勒且嘉不在,想辦法趁著別人不注意,逃出大帳。
烏勒且嘉加強了看守,堅持不懈,把人打暈,仍舊逃走。
即便烏勒且嘉在,也會趁其不備,突然用短刀捅他,趁他吃痛,拔狂奔。
可是烏勒且嘉總是不厭其煩地追回來。
卿言忘了穿鞋,跑得腳底全是草屑,還被碎石刮破了。
烏勒且嘉將放在床上,單膝跪地,耐心地為洗腳底。
“阿菟,別逃走了,好不好?”
卿言冷冷地看著他,說:“除非你殺了我。”
烏勒且嘉繼續為腳,“你知道,我不舍得殺你。”
他又抬起頭,“不過,阿菟,我聽說你有了一個兒?”
卿言一愣。
“告訴我,那是誰的兒?”烏勒且嘉輕聲細語地問,“我的?還是梁國皇帝的?”
卿言皺著眉頭,沒有回答。
烏勒且嘉放下的腳,道:“但是那都沒關係了。對於我來說,最重要的是你。”
“你要怎麽樣?”
“我不怎麽樣呀,”烏勒且嘉揚起燦爛笑臉,“阿菟,我隻是想要你一直在我邊。”
烏勒且嘉用上好的金子,打造了一副腳銬,把卿言鎖在他的帳中。
他每天來看,和說話。
每天都罵他、打他,他全都著,從不反抗。
數載,不涉風月。
烏勒宗挈來看卿言,他歎:“我們三個兄弟,最得孩子歡心的是就是且嘉,可他因為你,沒和其他任何一個人接過。現在他都二十多了,一個孩子都沒有。”
卿言的回應就是,把他一把扯過來,一頓暴打。
烏勒宗挈的麵被打壞裂開,卿言一拳打在他麵門,冷笑道:“再多,打死你。”
烏勒七彷聽說烏勒宗挈被打得那麽慘,出於好奇,也來看卿言。
他一句話沒說,也被一頓暴打。
烏勒七彷苦不迭:“我什麽也沒說,什麽也沒做!打我做什麽?”
卿言踹他一腳:“就是你造的兵,害得我們大梁軍隊死傷慘重,不打你打誰!”
那幾年,王帳裏人但凡接近過烏勒且嘉的大帳,基本上都被卿言打過。
有的還不止一次。
每次他們私底下議論起來都滿臉惶恐,隻有烏勒且嘉笑容滿麵,說:“多完啊。”
後來他們給烏勒且嘉一個評價:抗揍小子。
不過卿言不打人。
烏勒且嘉留下來照顧的人裏,有一個子秩回雅。
卿言一開始不願意和說話。
秩回雅卻會自言自語:“我聽說你阿菟,這是你的名字,對嗎?”
“你是綏都人吧?我從來沒去過綏都,聽說那兒的人和我們長得不一樣。”
“綏都是不是有很多好吃的?我聽說有一種很有名的,魚羹。”
在喋喋不休十幾天後,卿言忍無可忍,說:“天興樓的魚羹,最好吃。”
秩回雅先是一怔,而後目驚喜:“阿菟,你和我說話了!”
在帳中快樂地打轉,“阿菟居然和我說話了,這是阿菟和我說的第一句話!”
卿言煩不勝煩:“不就是和你說了句話,這麽大反應做什麽?站住!”
秩回雅立馬站定,雙頰紅撲撲地看著,說:“我……從小就沒什麽朋友。他們覺得我出低賤。”
“出低賤?你姓秩回,這在呼延氏是個大姓吧。”
“但是我的娘親是梁國人……”秩回雅的聲音輕了下去。
卿言微微一愣。
這才知道,呼延氏的人看不起梁國人,就好像梁國人看不起呼延氏。
兩個國家和各自百姓之間,存在著越百年的偏見與仇恨。
這天晚上,卿言破天荒地沒有打烏勒且嘉,而是問起他秩回雅的事。
烏勒且嘉委屈撇:“阿菟,你怎麽關心別人,都不關心我?”
卿言麵無表:“說說,不說滾。”
烏勒且嘉立馬老實:“爹以前是行商的,南下賣貨,看上了一個梁國子。他回來北地後不久,那子找了過來,邊領著個小孩。原本秩回一族不肯認,說這是那子和別的男人生的也不一定。這子也是烈,直接一頭撞死明誌。此事鬧大了,秩回一族隻能收下這個孩子。”
卿言若有所思:“呼延氏看不起,是因為是梁國人的兒?”
“差不多。”
卿言不說話了。
烏勒且嘉連忙說:“可是你不一樣,阿菟,不管怎麽樣我都會很你。”
卿言指了一下腳踝:“那你把這個解了。”
烏勒且嘉閉上了。
卿言冷笑:“廢。”
·
卿言與秩回雅絡起來。
秩回雅教卿言呼延氏的語言和文字。
卿言則對講綏都的風土人。但是說著說著,卿言就覺,在的那些回憶裏,似乎本該有另外一個人的存在,可記不起來。
不過秩回雅最關心的,還是卿言與烏勒且嘉的故事。
卿言不理解,為什麽想知道這個。
起初秩回雅不肯說,後來被卿言一嚇唬,說出了實:“我的姐姐,秩回真,很喜歡且嘉。”
卿言冷笑。所以這是利用秩回雅。
“要是我不打聽清楚,會不高興的。”秩回雅聲音很輕。
卿言頓了一下,道:“我在戰場上打贏了烏勒且嘉,所以他我得無法自拔。”
秩回雅一怔,沒想到真的說了!
“那……你會嫁給他嗎?”
“嫁給他?”卿言都覺得好笑,指了一下腳上鏈子,“他都這樣對我了,我還嫁給他?”
“這不是他你的表現嗎?”
“不是。”
卿言板起了臉,“你,就會讓你自由,讓你去做你想做的事。而不是把你關起來,鎖在邊。”
秩回雅若有所思。
·
春去秋來,北地有關卿言的爭論越來越多。
有的說:“這麽個子,養在帳中,傳出去實在不好聽。”
還有的說:“而且太暴力了!那麽多人都挨過的打!”
更有的人說:“可是個梁國人!那麽低賤,本不配留在北地!”
最後這種偏激的說法,主要是秩回一族提的。
吵得特別兇的時候,秩回一族還向烏勒宗挈囂:“當年推舉你們父輩當王,是因為你們能引導我們,可現在看來,你們連自己的人都搞不定!這樣的家族,不配做呼延王!”
烏勒且嘉坐在一旁,一言不發,眸中泛起冷殺意。
與此同時,卿言在大帳裏待得越來越不耐煩。
頭腦中有關小孩的形象愈發清晰,朦朦朧朧,有兩個。
一個很掉眼淚,還很會撒。
一個總是跟在小哭包的邊,經常會笑。
尤其是麵對烏勒且嘉,看著他,卻總想起另外一張臉。
烏勒且嘉懷抱卿言眠,聽到夢中呢喃:“嗯嗯。”
他愣了一愣。
卿言仍在說著夢話:“魚羹好不好吃呀?嗯嗯,今晚和我一起睡覺,好不好?”
烏勒且嘉切齒。
所以和生兒的,不是他,不是梁國皇帝,而是一個嗯嗯的人?
什麽狗男人,連個名字都娘們唧唧!
烏勒且嘉特別生氣,翻下床,出去了。
帳外月明星稀,曠野上的風那麽冷。
他打了個寒戰,不好意思回去,而是跑去大哥那兒了一晚上。
床上,烏勒宗挈說起來:“你一直鎖著,這也不是辦法。”
烏勒且嘉歎氣:“我也知道。”
“畢竟是卿言,遲早會逃走。”
“可是沒有,我不知道該怎麽活下去,”烏勒且嘉很認真地考慮,“大哥,你說我該不該跟去綏都?”
烏勒宗挈頓了一下,說:“你還記不記得,多年以前,卿言和我們打仗,但是他們的戰略布局,都被我們知道了?”
“嗯,記得。”
“那是軍中出了。”
說起這個,烏勒且嘉也記起來,“我在戰場上找到,邊上的人是想殺。”
“能安排這一切的人,不簡單。”
“你覺得會是誰?”
“不好說。”
“那查查看吧。”
他們真的查出來了。
梁國的員胡平伯、謝柬之,參與了當年的戰役,他甚至和呼延氏串通,一直派人去暗殺卿令儀。
這個姓不常見,烏勒且嘉直皺眉:“該不會是阿菟的兒?”
“難說。”
“敢阿菟的兒,真是找死!”烏勒且嘉眉眼間滿是戾氣。
烏勒七彷打著哈欠經過,問他們:“在聊什麽呢?”
烏勒宗挈簡單地說了一下。
烏勒七彷皺起眉頭:“這麽說來,我造的那些兵,都被用在阿菟兒上了?”
烏勒且嘉踹了他一腳。
“是誰來找你要那些兵的?”烏勒宗挈問。
“秩回一族啊。”烏勒七彷道。
“果然是他們。”烏勒宗挈呢喃。
烏勒且嘉真起了殺心。
原本他想著,等把事都理好,就好好向卿言認錯,保證以後不再鎖著。要是生氣,他就乖乖被打一頓。
一頓不行,那就兩頓。
但他不知道,他數日不去帳中,卿言落得個輕鬆,還製定了一個逃走的計劃。
先對秩回雅說:“我打算走了。”
秩回雅一驚,“……走?”
“你和我一起走,我們去綏都,”卿言道,“不過,你得幫我做一件事。”
“什麽事?”
卿言一字一頓,“鑰匙。”
腳上鐐銬的鑰匙,被烏勒且嘉常年帶在上。隻有解開金鎖,才有機會逃走。
秩回雅猶豫了一會兒,了拳頭,“好,我去!”
卿言忐忑地在帳中等待。
沒多會兒,秩回雅急匆匆地跑了回來。展開右手,掌心正好躺著一把金燦燦的鑰匙。
卿言不由欣喜:“小雅,你可以呀!”
秩回雅被誇了,害地笑了一笑。
卿言打開腳銬,對秩回雅道:“你一定要跟我!”
“好!”
卿言製造了混,趁此拉上秩回雅奔向馬廄。隻要一人騎上一匹馬,就可以離開草原。
這些年,卿言對北地有了更多的了解,不會再像過去那樣,輕而易舉被烏勒且嘉追回。
“秩回雅,你膽子真是越來越大!你居然敢幫著逃跑!”
一個子嗓音驟然響起。
馬廄附近,出現一隊人馬,打首的子姿態高傲,說著呼延語。便是秩回真。
秩回雅向:“姐姐,求求你,別為難我們!”
秩回真斥道:“你閉!你也配向我求!”
“哪來的野,淨瞎。”
卿言諷刺開口,用的也是呼延語。
秩回真麵大變,“別以為且嘉喜歡你,你就可以這樣罵我!更何況,他們很快就不是王族了!”
卿言彎腰,隨手在地上抄起一塊石頭丟過去。
正中秩回真的腦門。
尖一聲,捂住了頭。
“不想苦就閉。”卿言警告。
又微微轉頭,對秩回雅道:“你去牽馬,我收拾他們。”
秩回雅點頭。
向馬廄小跑過去。
秩回真要過去,卿言清清嚨:“聽說你很喜歡烏勒且嘉,那你知不知道,烏勒且嘉每天晚上抱著我睡覺的時候,都會說些什麽?”
秩回真一愣,大怒道:“都給我抓住!好好教訓一頓!”
眾人向撲來。
卿言氣定神閑,活了一下手腳。
沒費多功夫,卿言就解決了所有人,最後,把秩回真從馬背上扯下來,按在地上。
秩回真故作高傲:“你打贏了我,那又怎麽樣?”
卿言挑眉,“我可不止是打贏你,我還會殺了你。”
秩回真一怔。
“啊!”
馬廄,突然傳來一聲尖。秩回雅的聲音。
卿言心口一跳,舉目去。
秩回雅正固執地牽著兩匹馬,向外奔來,就在的後,跟著兩個殺手。
“本來呢,我是想要殺你的。”秩回真得意地說。
“放了!”卿言高聲開口。
接下來還要說,不然,我就殺了秩回真。
可後半句話還沒說完,殺手的刀已捅進了秩回雅的膛。
卿言猛然睜大雙眼。
秩回雅還抓著駿馬的韁繩,向所在的方向。
殺手的刀拔了出去,才力一般,鬆開韁繩,落在地。
秩回真哈哈大笑。
卿言扭斷了的脖子。
撿起秩回真的劍,大步上前,利落將二人斬殺。
最後在秩回雅麵前蹲下來。
“你……我……”
秩回雅想要說話,可一開口,口中便不斷溢出鮮。
“噓,別說話。”卿言的聲音前所未有的溫。
秩回雅點點腦袋,抬起手,指向帶出來的駿馬,翕。
“我明白,我明白,”卿言鼻頭發酸,“我會回到綏都。”
秩回雅扯角,出了笑容。
沒再彈。
卿言閉了閉眼,忍去所有的淚水,牽住了駿馬的韁繩,側輕鬆上馬。
“阿菟!”
聽到烏勒且嘉的聲音。
抬眸,他得到消息,正急匆匆地趕來。
“別。”卿言聲音冷漠。
烏勒且嘉停下了,低聲下氣道:“阿菟,我知錯了,以後我不再鎖著你,你別走,好不好?”
卿言嗤笑:“烏勒且嘉,你真是個笨蛋。”
烏勒且嘉一愣。
“嗯嗯,全名卿令儀。是我的兒。”剛才卿言全都記了起來。
烏勒且嘉又是一愣。
“你不如好好算一算時間,”卿言目清亮,“也算一算你對我的了解。嗯嗯究竟是我和誰的兒。”
烏勒且嘉瞳孔驟然放大。
“現在,我要回去找我的兒。”
卿言一聲長嗬,縱馬奔馳。
後眾人意圖追趕。
烏勒且嘉抬起手,製止了他們。
烏勒宗挈走上前,“我有侄了!我得去看看!”
“你急什麽。”烏勒且嘉拽住他。
駿馬飛馳,卿言的影越來越遠。
他緩緩道:“這些年,乖寶被什麽人欺負了,得算賬。以後乖寶和阿菟來這兒,日子會是什麽樣,得好好謀劃。”
不久,卿言回到綏都。
呼延氏發,明麵上是烏勒一族兄弟反目,實際上,是秩回一族被殺了個幹淨。
“被殺”的烏勒宗挈抵達綏都,見到了心心念念的侄。
“奪位”的烏勒且嘉也到了綏都,假冒使臣,在一念居和卿言打了一架,接了個吻,還見到了寶貝兒。
他聽說,乖寶還是“祥瑞之”。
他不相信這個。
但是那天,們母抵達北地。
烏勒且嘉特意趕去迎接。
天昏暗,馬車上先下來煬,他不急不忙轉回去接人。
馬車裏先探出來一隻白如藕的手,放進煬的掌心,接著,明豔俏的臉蛋了出來。
出現後,忽有天刺破層疊的烏雲,照落下來。好巧不巧,正落在卿令儀的上。
似乎有些驚訝,向煬。
煬含笑誇獎,於是笑得更是明了。
眼見那一幕,包括烏勒且嘉在的許多人,都想,或許祥瑞之的傳聞,是真的。
(全文完)
猜你喜歡
-
完結1055 章

侯府小啞女
燕云歌自末世而來,重生侯府,她給自己定了個小目標:每天吃好喝好樂無憂!然而……她爹一門心思造反,她哥一門心思造反,她嫁個男人,還是一門心思造反。燕云歌掀桌子,這日子沒發過了!
272.1萬字8 16625 -
完結10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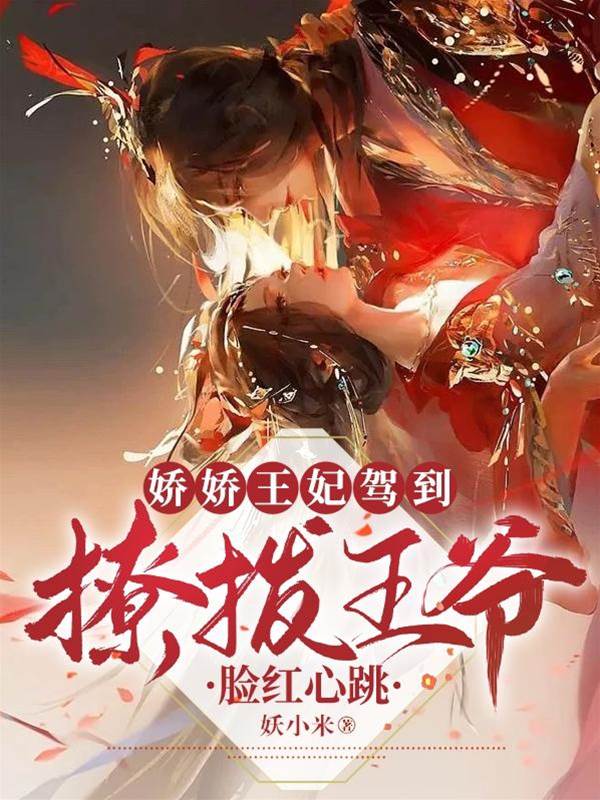
嬌嬌王妃駕到,撩撥王爺臉紅心跳
水洛藍,開局被迫嫁給廢柴王爺! 王爺生活不能自理? 不怕,洛藍為他端屎端尿。 王爺癱瘓在床? 不怕,洛藍帶著手術室穿越,可以為他醫治。 在廢柴王爺臉恢復容貌的那一刻,洛藍被他那張舉世無雙,俊朗冷俏的臉徹底吸引,從此後她開始過上了整日親親/摸摸/抱抱,沒羞沒臊的寵夫生活。 畫面一轉 男人站起來那一刻,直接將她按倒在床,唇齒相遇的瞬間,附在她耳邊輕聲細語:小丫頭,你撩撥本王半年了,該換本王寵你了。 看著他那張完美無瑕,讓她百看不厭的臉,洛藍微閉雙眼,靜等著那動人心魄時刻的到來……
183.7萬字8.18 101640 -
完結372 章

穿成短命白月光后,和反派HE了
桑遠遠穿進一本古早玄幻虐戀小說裏,成了男主那個紅顏薄命的早逝白月光。男主愛她,男配們也愛她。女主因爲長了一張酷似她的臉,被衆男又愛又虐又踩,傷身又傷心。和男主的感情更是波折重重狗血不斷,虐得死去活來,結局還能幸福HE。桑遠遠:“不好意思本人一不想死二受不得虐,所以我選擇跟反派走。打擾,告辭。”反派長眸微眯,姿態慵懶,脣角笑意如春風般和煦——“我的身邊……可是地獄呢。”她沉思三秒。“地獄有土嗎?”“……有腐地。”“有水嗎?”“……只有血。”他想看她驚惶失措,想等她尖叫逃離,不料女子呆滯三秒之後,雙眼竟然隱隱放光——“正好試試新品種!”“……”他在最深沉的黑暗中苟延殘喘,從來也沒想到,竟有一個人,能把花草種滿一片荒蕪。
57.1萬字7.92 9525 -
完結313 章
亡國后成了反賊的寵婢
姜嶠女扮男裝當了幾年暴君。叛軍攻入皇城時,她麻溜地收拾行李,縱火死遁,可陰差陽錯,她竟被當成樂伎,獻給了叛軍首領霍奚舟。姜嶠捂緊馬甲,計劃著再次逃跑。誰料傳聞中陰煞狠厲、不近女色的霍大將軍竟為她破了例。紅燭帳暖,男人摩挲著她眼角的淚痣,眸色暗沉,微有醉意,“今夜留下。”*姜嶠知道,霍奚舟待她特殊,只是因為她那雙眼睛肖似故人。無妨,他拿她當替身,她利用他逃命。兩人各有所圖,也是樁不虧的買賣。直到霍奚舟看她的眼神越來越深情,還鄭重其事地為允諾要娶她為妻,姜嶠才意識到,自己好像是在作繭自縛——
49.2萬字8 685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