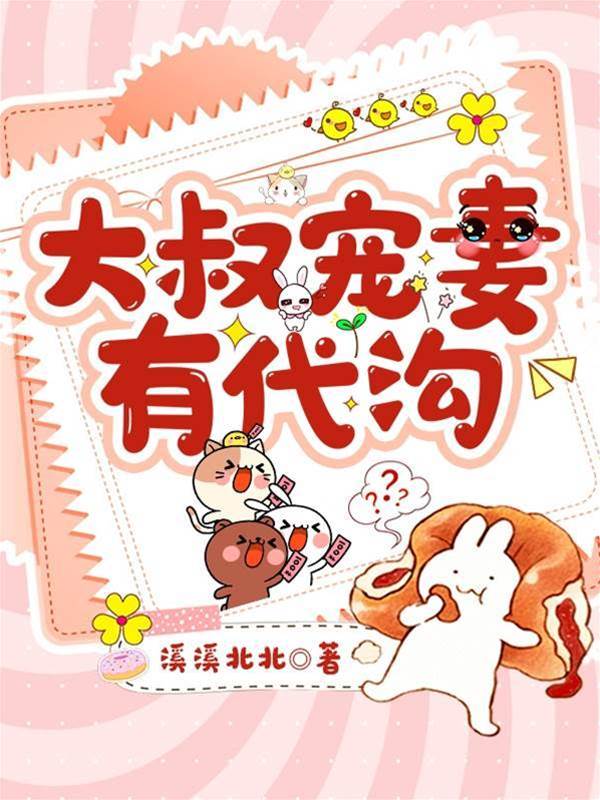《偷吻薔薇》 第77節
靜聲看了一會兒,第一次發現“乖巧”這個詞竟然也可以用在他上,毫不違和。
那雙總是讓難以招架的眼睛閉上了,別的地方的優越就更為凸顯。
從眉峰,到眉心,到鼻梁,到鼻尖,再到瓣,到下頜......
無一不在拉扯著的視線流連。
全長在心坎上。
忽然覺得嚨發幹,慌忙撇開視線去盯著窗戶,隔了好一會兒才慢吞吞轉回來。
終於想起自己是上來做什麽的了。
可臨到頭,看他睡得這麽沉,又有點舍不得吵醒他了,還想將他眉心淺淺的褶平,讓他能睡得更安穩些。
卻不曾料到指腹才將將到那片皮,陡然間被大力握住手腕,手下的人驀地睜開了眼睛。
謝薔甚至來不及為他猝然的轉醒吃驚,就在進那雙眼睛的瞬間,整個僵在原地。
很難形容那裏麵都有些什麽。
驚惶,不安,消沉,黯淡......
他像一條獵龍失去了它得來不易的寶藏,在緒崩塌的瞬間人意外撞見,來不及躲,也來不及藏。
謝薔的緒也跟著他跌落穀底,落古井深潭,墜墜下沉,直到冰涼。
“怎麽了......”
好不容易找回自己的聲音,很輕,很小聲:“做噩夢了嗎?”
謝洵意看著,聲音嘶啞疲倦:“夢到你回法國了。”
他一直握著的手沒有鬆,現實與夢境沒能徹底轉換,怕一鬆手,人就不見了。
一時間誰也未在開口。
窗戶是關上的,從門口流進來的冷空氣還來不及與室置換,房間裏很暖和。
本應該是舒服至極的環境,然而謝薔隻覺得自己是空空的,猶如一片飄在半空的浮,無措迷茫都不由己控。
直到青輝宏亮的聲音從樓下傳來:“薔薔!人弄醒沒?趕下來吃午飯啦!”
謝薔看見那雙眼睛的主人在自己麵前回了神。
不過一眨眼的功夫,外泄的緒就被悉數收斂幹淨,恢複一貫的清冷深邃,仿佛剛剛一切隻是謝薔的錯覺。
“已經中午了?”
謝洵意閉了閉眼,作自然地鬆開謝薔坐起來,又了下鼻梁,睡得有點頭暈。
謝薔神怔忪,點頭似乎隻是下意識的作。
“走吧。”謝洵意從床上下來,起時順手了把腦袋,依舊是從容帶笑的語氣:“小謝老師,別發呆了。”
到山上的第一頓午飯,很盛。
然而謝薔嚐不出幾個味道。
“不好吃?還是吃不習慣?”謝洵意低聲問。
謝薔搖搖頭,在謝洵意給夾菜時,忍不住拉住他的袖口了一聲:“哥哥......”
想說什麽的。
可是周圍人太多了,也吵得分不出頭緒,讓隻能在謝洵意詢問的目中悶悶搖頭,鬆了手:“沒事。”
謝洵意蹙眉:“不舒服?”
謝薔:“有點困了。”
謝洵意:“那就吃完上樓睡一覺。”
謝薔嗯了聲,低頭去夾碗裏的菜。
薑苒和許湘回籠覺已經睡飽了,飯後留在院子裏和其他老師玩牌消食。
謝薔滿腹悵然,本以為自己會在床上輾轉反複,事實卻是沾著枕頭很快就睡著了。
並且在夢裏,又回到了那人沉睡的床邊。
不再是僅用指尖的試探,夢裏的膽子大著,遵從本心地俯去親他,卻又在即將得逞之際被當事人逮個正著,用力拉懷抱。
而睜開眼,一切又煙消雲散。
邊都是空落落的,也沒有抱。
厚重的失落瞬間將席卷。
原來都是裝的。
什麽進度條,什麽大膽,什麽遊刃有餘,都是裝的。
明明看起來那麽無所不能的一個人,怎麽會一個夢就能輕而易舉將他擊潰呢。
呆坐著,突然好後悔啊。
為什麽在他那樣看著時,沒有立刻抱住他呢。
然而世上沒有後悔藥,它就通通自行轉化了想念,指引著穿過廊下往前走,走到距離那個房間僅有幾步,走到聽見人聲,聽見的名字。
“換我是薔薔,能被你墨跡死。”
“這招不行,你就不能換別的變通一下,找點歪門邪道,不是,找點偏方捷徑試試嗎?”
“早知道昨晚那老師讓我跟換位置我就換了,說不定你們互一下,薔薔看著吃了醋,事就了。”
青輝話裏話外滿是恨鐵不鋼:“你腦子多靈,帶過你的老師教授那都是能掛在上念叨到退休的,會連這個都想不到?”
“你這郵件怎麽這麽長?”
“還有這個火腸裏怎麽有玉米啊,算了回頭給外麵野貓吃。”
謝洵意不鹹不淡反問他:“你吃過醋?”
青輝:“沒啊,我都沒談,吃什麽醋?”
謝洵意:“既然沒有,就別瞎建議了。”
“嘿,怎麽就是瞎建議了?”
青輝不服:“你都沒試過,怎麽就知道不行?你們現在這不上不下的,我看著都難。”
“你自己克服一下。”
謝洵意淡淡:“吃醋不是什麽好玩的事,我舍不得讓薔薔難。”
青輝:“......”
青輝:“嘶!我說你這個鐵腦殼——”
“薔薔,醒啦!快下來咱們去拜許願樹了!”薑苒的聲音從樓下傳來,正好打斷青輝。
他朝外了一眼,拉開門走出房間,看見薑苒和許湘在院子裏等著,謝薔下去就被薑苒挽住手。
“薑老師,什麽許願樹啊?”他問:“我們能去嗎?”
薑苒笑嘻嘻拒絕:“不行,鎮民說了,這樹有靈,隻能孩兒拜!”
*
*
出了民宿,沿著青石大道往前走一程,買上許願牌再拐進小徑走個幾百米,鎮民口中的許願樹就到了。
一片山坡,一棵大樹,一座半人高的土地廟,還有一個清理廟殘枝落葉的老。
樹確實很大,是民宿院子裏那棵的兩倍還不止,凡是手能夠到的枝椏上都被掛滿了許願牌。
可惜樹幹也沒掛個品種介紹什麽的,來的一群老師誰也不認識這是什麽樹。
“拜什麽?”
“拜升發財?”
“拜一夜暴富?”
“拜......”
“你們家家手裏頭拿個姻緣牌牌,肯定是拜姻緣嘛,許好了就掛上,等起樹娘娘幫你們給意中人傳過去。”
說話的是那位老,是帶著山腔的芙城話。
土地廟清掃完了,坐在小廟旁邊的石頭上,初冬的天氣也出了一頭汗,從兜裏掏出一張藏青的帕子邊邊休息。
而們這才注意到剛買的牌子除了正麵有花紋,背麵還有漢字分類。
除了薑苒挑中一張求子牌,其他全是桃花牌。
薑苒:“看來我運氣不錯,那我先來了,求子求子,求我兒子趕滾回來,不然老娘就要背著他找第二春了!”
許湘直接把牌子往樹梢上一扔:“我不需要男人。”
小雲老師:“我有老公了呀,可惜。”
陳老師:“那我合適,我沒男朋友。”
“巧了,我也。”
“我就直接開始了。”
謝薔捧著願牌,耳邊聽見的盡是好的祈願:
“高一點,帥一點?”
“閱曆富,學識淵博。”
“事業有,我就行。”
“全心全意對我好......”
老笑瞇瞇看著們,又搖著帕子向天,張口念:“樹,樹娘娘,守個山包送吉祥,來是青米背一,走是鴛鴦配凰。”
“木凳凳,木床床,燕子一雙上房梁,牛棚羊房不嫌髒,湊一行做一行,等又等,不慌忙,好郎戴帽坐公堂......”
曠野之下,大山之中。
老人滄老纏綿的誦在群山低穀中回,又被山巔順流而來的風帶去更遠的地方。
謝薔長發被拂得飛揚,冷涼的溫度從口鼻灌進。
仰頭看著樹,巨大盤錯的枝節倒映在黝黑的瞳孔,裝一方玲瓏的浩瀚。
許願牌掛上去的瞬間,似乎一切都在此刻清晰了。
遊般的呼吸變得急促,悵然迷茫的雙眸終於在浩瀚中被點亮。.思.兔.網.
一把抓下許願牌,在薑苒的喊聲中全力往回跑。
不等了。
很慌,很忙。
既然已經堅定地選擇了,為什麽總要讓他等呢?
擁有所有人的夢寐以求,為什麽還要猶豫呢?
明明在心裏,他早就是最特別的那個了。
他簡直燦爛得像偉大世界裏的一束,牽著的緒,讓連瑣碎小事都想分,想和他一起去許多許多地方,做許多許多事。
而現在,更想要他可以大膽地做他想做的事!
他有坦然赤城的喜歡,也又最熱烈純粹的意。
畢竟對別人的告白轉頭就能忘,可是對他時,可是連求婚都在考慮!
從小路到大路,青石板載著的步伐一路延。
盡頭是小樓門前,屋簷樹蔭下的空地上,三五隻野貓的中間,謝洵意蹲在那裏,不不慢揪著食喂它們。
很快,小洋娃娃跑過來了,緩了會兒氣,又自顧自蹲在他旁邊。
“好多小貓。”歎。
猜你喜歡
-
完結165 章
神秘老公不見面
為了回報家人十八年的養育之恩,她必須要代嫁,而那個男人半身不遂并燒的面目全非。 新婚之夜,她被灌下一碗藥,只能感覺到強壯的身體在她身上...... 從此,她日日夜夜伺候那個面目不清不能自理的男人! 傳說,霍家怪事之多,尤其是夜深人靜之時! “明明警告過你,晚上不要隨便走動,你看見不該看的,就要為此付出代價!” 他帶著邪佞的笑容緩緩而來將她逼迫于墻角。 烏子菁手執一張照片,同一張臉,卻出現在三個人身上? 究竟誰才是自己的老公,夜夜與她歡愛的又是誰?
40.2萬字8.44 62589 -
連載229 章

穿成影帝的炮灰前妻
楊千千是娛樂圈著名經紀人,她工作非常努力,最後她過勞死了。 然後她發現自己穿成了書裡和自己同名的一個炮灰,男主的契約前妻。 書裡原主因為不想離婚而下藥男主,然後原主懷孕,她以孩子為籌碼想要得到男主的感情,可是最後被男主以虐待兒童送進了監獄,最後也死在了監獄。 現在楊千千來了,對於男主她表示:對不起,我不感興趣。 楊千千穿書後的想法就是,好好工作,好好帶娃,至於孩子爹……親爹沒有那就找後爸!!! 某影帝:後爸?不可能的,這輩子你都別想了,這親爹他兒子要定了!!!
21.1萬字8 18925 -
完結517 章

婚不設防:帝少心尖寵
日久生情,她懷了他的孩子,原以為他會給她一個家,卻冇想到那個女人出現後,一切都變了。靳墨琛,如果你愛的人隻是她,就最好彆再碰我!
92.1萬字8 67367 -
完結1023 章

離婚後陸總他真香了
三年前的一場鬨劇,讓整個A市都知道了許洛婚內出軌,給陸澤臻戴了一頂綠帽子。三年後再次相見,陸澤臻咬牙切齒髮誓要報複,許洛冷笑不在乎。就在眾人都以為這兩人要刀風劍雨,互相對打的時候,一向凜冽囂張的陸總卻像是被下了蠱一樣單膝跪在許洛麵前,滿臉柔情:“許洛,你願意再嫁給我一次麼?”
189萬字8 37166 -
完結54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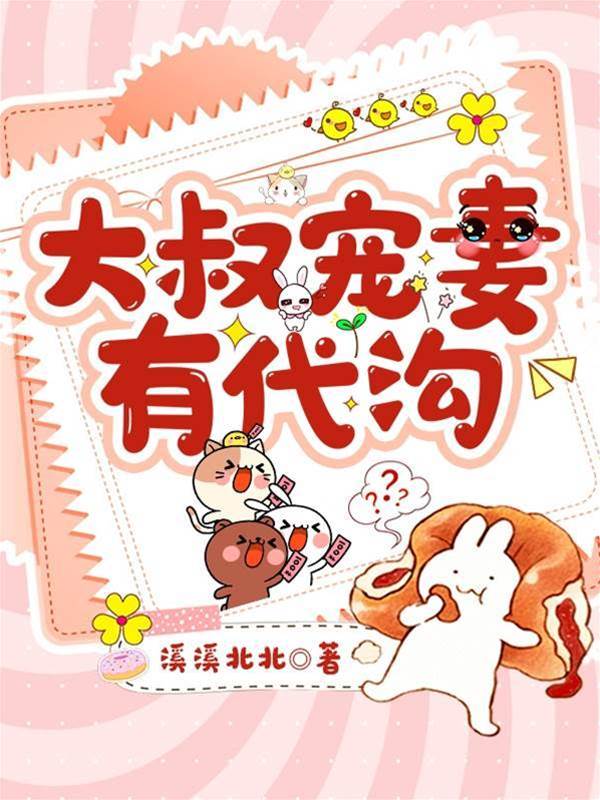
大叔寵妻有代溝
等了整整十年,心愛的女子終于長大。略施小計民政局領證結婚,開啟了寵妻之路。一路走下,解決了不少的麻煩。奈何兩人年紀相差十歲,三個代溝擺在眼前,寵妻倒成了代溝。安排好的事情不要,禮物也不喜歡,幫忙也不愿意… “蘇墨城,不是說,你只是一個普通的職員嗎?怎麼現在搖身變成了公司的總裁。” “蘇墨城,不是說,以前你根本就不認識我嗎,那你父親和我母親之間怎麼會是這種關系?”
55.3萬字8 5196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