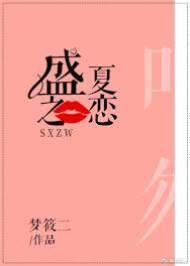《熾吻》 第六章 向我太太道歉
“二代艙的誌願者申請表,這份令我有些為難,想讓你們拿個主意。”
說罷,時序把東西遞到了蔣魏承手上。等他們兩個都看完以後,時序輕咬著等他們說話。
蔣魏承看了眼時序,問:“你怎麽想的?”
這份申請表本沒有問題,但申請的家庭份卻有一點特殊,不巧正是他們都認識的,是個有一定地位的明星家庭。正常來說,都是打過道的關係,如果他們真的想把家中的孩子送來參與這個實驗,招呼一聲就好了,但他們這麽正經地遞了申請表,反而讓人不得不謹慎對待。
時序支著下道:“有利也有弊,他們家願意參與,有效果的話就是最好的廣告,不過同等的,也會讓整個實驗階段從開始就備矚目,任何缺陷都會被無限放大,對我們來說力不小。”
說得很準,蔣魏承眼中掠過讚許,接著的話說:“既然是送上門的免費宣傳,那就接,你的抗能力應付這個應該足夠。”
杜忱本來還躍躍試想發言呢,可一聽蔣魏承的話,又看他那一副篤信時序的樣子,杜忱隻覺得自己猝不及防間被喂了一口狗糧,頓時不想開口了。
時序心裏其實也是想通過的,但不是從蔣魏承那個角度去想的,而是那個孩子的況和時冬冬差不多,但征又完全不同,很有參考價值。
既然蔣魏承發了話,也不糾結了,草草吃完飯,就想盡快回去將名單落定,早點進下個階段。
看著時序匆匆返回工作崗位,被落在後麵的兩個男人表各異,隨後杜忱拍了拍蔣魏承的肩膀,很替他慨:“你老婆看起來比你更工作狂啊。”
蔣魏承嫌棄地撣開杜忱的手,看了看時序闊步離去的背影,說了句:“不好養。”
他在談公事之餘可沒略過時序對他夾的那片鬆茸的反應,是都不的。除了鬆茸,桌子上五道菜隻吃了兩道,挑食程度可見一斑。
時序回了辦公室在午休的時間把擇定的誌願者全部整理了出來,下午一上班就把名單給了助理。助理翻了翻名單,意外地在上麵看到了一個並沒有出現在申請表的名字,錯愕地看了看時序,時序似乎知道在意外什麽,笑著說了句:“時冬冬的詳細資料晚點我發給你,這個實驗他也參與。”
助理愣愣地應好,忙著去跟進後續的事項。時序下班前將團隊的辦公區域都走了一遍,實驗區十臺嶄新的二代艙靜靜待命,似乎準備召喚一個奇跡。
等時序回到蔣氏莊園的時候,已經是晚上九點多了。蔣氏莊園一如往常清淨,但時序此時卻發現了它的缺點,那就是離現在上班的地方太遠了,一個多小時的車程,有這麽多時間做點什麽不好,真不理解為什麽蔣魏承每天那麽忙碌卻還要住在這裏,白白把寶貴的時間浪費在通勤上。
時序進門的時候蔣魏承已經在家裏了,坐在沙發上拿著一大幅圖紙在看。時序沒力好奇他在看什麽,倒是目牢牢鎖定唐嬸,語氣帶著點自己都沒發現的委屈:“唐嬸,我。”
唐嬸聽完時序的話就看了一眼蔣魏承,心想先生還真是料事如神,事先就代了準備一些宵夜。唐嬸趕忙去了廚房,給時序熱起先前備下的點心。
蔣魏承端坐在沙發上,看著手裏的設計圖一不,心裏卻在想,就中午吃的那點東西,到現在不才怪。
或許是了一天腦子的緣故,到現在還沒吃晚飯的時序是真的得難,也不管蔣魏承就在沙發坐著,走過去拿自己放在茶幾上的曲奇餅幹墊肚子。
時序叼著曲奇路過蔣魏承的時候挪眼看了看他手裏的設計圖,隨口就問:“你打算裝修莊園?”
蔣魏承眉都沒抬一下:“要把一個圓頂改玻璃頂。”
時序又看了一眼蔣魏承手上的圖紙,咂咂,蔣氏莊園的主建築有兩個圓頂,穹蒼式結構,難蓋也難拆,他這麽費工夫要改屋頂,時序隻能說,有錢人的好理解不來。
不過家裏裝修倒是一個很好的借口,時序手上的曲奇屑,道:“家裏要裝修,幾天肯定完不了工,時冬冬怕喧鬧,正好實驗馬上要開始了,我打算這陣子帶時冬冬去我市中心的公寓住。”
前幾天就在盤算怎麽和時序合理分居以保證睡眠質量的蔣魏承對的提議毫無異議,當即表示同意。
等他邁著步子往樓上走的時候,他在樓梯的拐角停了停,方才時序說的是……家裏?
家,真是陌生的詞語。
蔣魏承收起臉上的哂笑,緩步走向了臥室。
一個小時後,吃飽喝足並把自己洗刷幹淨的時序帶著一暖意走進房間,蔣魏承還沒睡,靠坐在床頭看書。時序掀開被角坐了進去,伴著蔣魏承書頁翻的聲音刷著自己的社件。說起來,和他近距離接這麽多天,時序還真的從沒看過他在休閑時間過手機,大部分時間就是捧著本書,也不知道是在找哪個如玉。
時序餘看他一眼,蔣總的生活這麽樸實無華?是霸總中的另類沒錯了。
時序收回自己的目,不防他已經看了過來。表麵從容地放下手機,客套地和他道了句“晚安”,隨後將自己藏於大床一角,努力當個鵪鶉。
一不之餘還不忘教育自己:十次看他九次被抓包,時序你怎麽不長記!
就在時序迷迷蒙蒙即將陷夢鄉的時候,邊的人放下了書關了閱讀燈,房間霎時陷黑暗,所有的也被悄悄放大。時序明顯覺到邊人躺了下去,然後在一片黑暗中,時序聽見一道低沉卻輕的聲音。
“晚安。”
全新的一個工作日,杜忱正悠哉地在公司地庫停好車,就看見隔著三個車位的時序匆匆忙忙地下了車,踩著高跟鞋跑出了一百米衝刺的架勢。
杜忱覺得很有意思,快速掏出手機錄了個短視頻發給蔣魏承,末了還不忘發了一段語音揶揄:“你老婆這麽崗敬業的人居然遲到,你耽誤的吧?”
這麽無聊的問題蔣魏承一般都懶得回複,倒是把時序踩著高跟鞋狂奔的視頻看了兩遍,有些好笑開始在他麵前解鎖的這些全新的麵貌。
在今天以前,蔣魏承從來都不覺得時序是那種急子的人,大概是的行事作風一直給他一種沉穩從容的覺。
直到今天早晨不到六點就起床開始收拾行李,打定主意今天就要搬到市中心。雷厲風行的樣子一度讓唐嬸和阿茹誤會他們昨晚發生矛盾,蔣魏承沒有解釋的習慣,卻被迫承了唐嬸和阿茹的目審視。
現在因為自己的行為遲到,還要連累他被杜忱誤會。
時序本來也是沒打算那麽急的,但不知道昨天晚上究竟是哪筋不對,覺躺在自己邊的蔣魏承存在格外強,天知道別扭了多久,思前想後還是覺得趕分開住比較好。
時序到辦公室以後已經心無雜念,的助理工作效率極強,或許是也知到了的急迫,以最快的速度通知了參與實驗的九個誌願家庭,並約定了在今天進行麵談與相關文件的簽署。
時冬冬的那份誌願書是最早送到時序手邊的,時序之前就在線上參與過誌願書的擬定,誌願書到手之後幾乎是毫不猶豫就簽署了。
自己沒有很大的覺,團隊員知道以後卻備鼓舞。如今整個團隊都是石過河,在時序這三個月都不在他們邊的前提下,如今的行為很大程度上是對這個團隊信任的一種表現,。
同樣心激的還有收到實驗室通知的誌願家庭,除卻那個明星家庭以外,剩下的八個家庭中,有六個都屬於低收家庭。對於低收家庭來說,家中有一個這樣的病兒,其實是非常大的力,他們沒有足夠的資金去治愈孩子,唯一能做的就是盡可能地多打幾份工多賺一點錢,在糊口的同時盡可能讓患兒過得好一些。
在接收到通知以後,大部分患兒家庭早早到了,坐在會客室按捺著張的心等待。時序路過會客室時側目看了一眼,那些家長的麵孔或年輕或年老,卻都有一個飽經滄桑的共同點。
時序準備走進會客室的時候,最後一個明星家庭也姍姍來遲。時序不關注娛樂圈,倒是從趙恬恬那裏聽過,這個三十出頭的著名演員在事業巔峰期宣布結婚生子,兩年以後公布離婚和孩子生病的消息,後來一邊工作一邊照顧孩子,苦盡甘來收獲無數,概括起來就是很勵誌。
“蔣太太,你好。”夏瑩率先出手。
時序禮節地握了握的手:“你好夏小姐,實話說看到你的申請我很意外。”
猜你喜歡
-
完結2295 章

都市至尊聖醫
一代武神葉修,靈魂重歸故鄉, 歸來時,重生日,兩世仇人,以牙還牙! 上一世,他慘遭綠茶未婚妻殘害,含恨而死。 這一世,守護親人,登頂神位! 逆天功法,至尊寶具,最強修為,唾手可得! 縱橫逆天霸血,登上至尊神座。 葉修微微一笑,“有些人血中有風,注定要漂泊一生······”
427.2萬字8 35551 -
連載1085 章

財閥小千金:老公,我吃定你了
首富唯一繼承人還需要聯姻?還是嫁給穆樂樂的死對頭?! 穆樂樂不舍得氣死爺爺,但舍得氣死老公! “總裁,太太新婚夜去酒吧。” 晏習帛:“卡停了。” “總裁,太太準備給你帶綠帽子。” 晏習帛:“腿砍了。” “總裁,太太準備和你離婚。” 辦公室一瞬間的沉默,晏習帛問:“她想懷四胎了?” 最初,穆樂樂用盡了各種辦法想離婚,后來,她在追逐離婚的道路上,逐漸迷失了自己。 本以為,穆家半路撿來的孤兒包藏禍心,欲要獨霸穆式集團。后來才發現,他煞費苦心只為了她。 穆樂樂當初寧可相信...
185.5萬字8.18 24186 -
連載400 章

訂婚宴,陸總偷偷勾她尾指
[又名:訂婚宴,被前任小叔親到腿軟]、[京圈佛子強勢上位!]京圈太子爺陸野的未婚妻顧言驚豔、勾人、脾氣好,圈內皆知有陸野的地方必有顧言,某天,聽說顧言提了分手。陸野散漫,“說了她兩句重話,不出三天,她會自己回來。”三天又三天。陸野醉酒沒人接,忍不住撥了顧言號碼,竟然被拉黑了。有八卦拍到顧言被神秘男人送回家,陸野驀地心裏空了一塊。後來,聽說陸野不顧暴雨狼狽,偏執的在前女友家門口站了一夜。第二天,那扇門終於打開。“言言!我想你…”一抹頎長的身影裹著浴巾走來。“小叔?……言言?”那個驕矜尊高的男人攬顧言入懷,睨向陸野,“你該改口了。”—那晚,顧言把陸野的小叔給睡了,第二天她又怕又後悔,轉身就逃。她辭了工作,換了住處。電梯遇到他,她假裝等下一趟。直到她在酒吧與人相親,直接被人擄走。逼仄的小巷,沉重的氣息侵入,強吻,“再跑,腿打斷。”—他一步步誘她深陷,怎麼可能逃出他手掌心。
70.5萬字8.18 27881 -
完結17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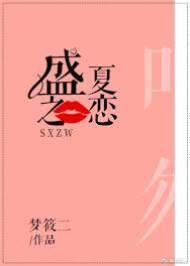
盛夏之戀
那天,任彥東生日派對。 包間外走廊上,發小勸任彥東:“及時回頭吧,別再傷害盛夏,就因為她名字有個夏沐的夏,你就跟她在一起了?” 任彥東覷他一眼,嫌他聒噪,便說了句:“煙都堵不住你嘴。” 發小無意間側臉,懵了。 盛夏手里拿著項目合同,來找任彥東。 任彥東轉身,就跟盛夏的目光對上。 盛夏緩了緩,走過去,依舊保持著驕傲的微笑,不過稱呼改成,“任總,就看在您把我當夏沐替身的份上,您就爽快點,把合同簽給我。” 任彥東望著她的眼,“沒把你當替身,還怎麼簽給你?” 他把杯中紅酒一飲而盡,抬步離開。 后來,盛夏說:我信你沒把我當替身,只當女朋友,簽給我吧。 任彥東看都沒看她,根本就不接茬。 再后來,為了這份原本板上釘釘的合同,盛夏把團隊里的人都得罪了,任彥東還是沒松口。 再再后來,盛夏問他:在分手和簽合同之間,你選哪個? 任彥東:前者。 那份合同,最終任彥東也沒有簽給盛夏,后來和結婚證一起,一直放在保險柜。 那年,盛夏,不是誰的替身,只是他的她。
25.4萬字8.18 755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