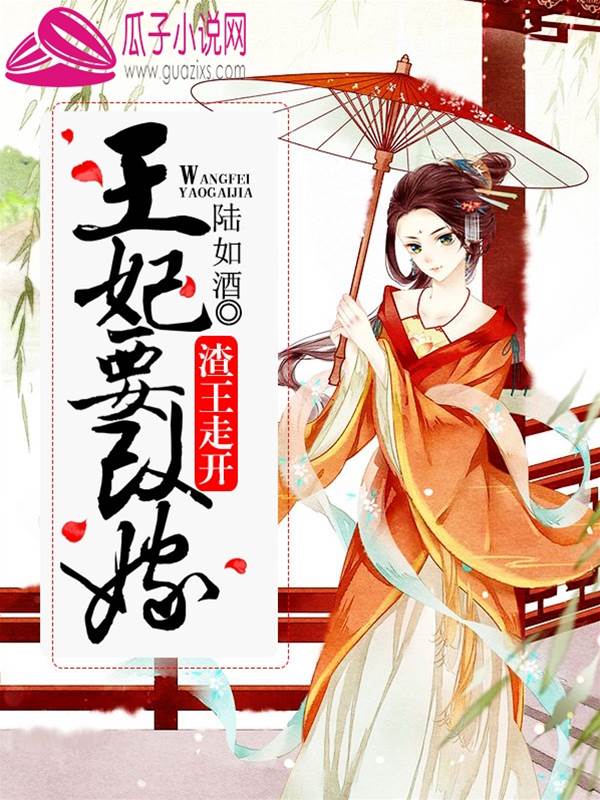《白發皇妃》 第85章 沉痛代價(2)
回了大帳,剛掀開簾幕,便見到宗政無憂正來回踱步,他看上去有些煩躁不安,見回來,便皺眉迎上,拉住冰涼的手,面一沉,“你去哪里了?這會兒才回。”
漫夭淡淡道:“去外頭走了走。”
宗政無憂牽著在桌邊坐下,微微扯出一個笑容,問道:“這個時辰,你怎麼在這里?”
宗政無憂作一滯,轉過頭來看,眼沉如水,眉頭皺,問道:“我不該在這里?那我應該在哪里?”竟然把他去昭云那里當了習慣!
漫夭撇開頭,輕聲問道:“昭云還沒吃飯吧?”
宗政無憂沒回答,端起一碗盛好的湯遞給,淡淡道:“了自然會吃。”
漫夭沒接他手中的碗,蹙了眉頭,道:“如果不吃呢?”
宗政無憂似是心不好,有些不耐,“不吃就著。總有一天會吃。”
這什麼話?那是昭云,是一個為他可以付出命的子,他居然如此淡漠,仿佛與己無關。怔怔的著他,未曾多想,就口而出:“你怎麼這樣冷酷無?是因為我們才變這副模樣!”
一句“冷酷無”,令宗政無憂面陡然一變,砰的一聲,他突然重重放下碗,碗里的湯經不住劇烈的震,幾乎灑出一半,濺得滿桌子都是。他看也不看,只鎖著眉心,薄抿一條直線,目定定地著,那眼神似是要看進心底里去。他的手在不知不覺間握,手上的青筋一一緩緩呈現,像在極力忍著什麼。
漫夭一顆心猛地揪了起來,懊惱地皺眉,到底在說些什麼?!
看著他眼底埋藏的悲傷和痛楚,那樣深切而沉重,只覺心口窒痛,張著,抖著說不出話來。
兩相靜默,過了半響,宗政無憂都沒有接口。他只是定定的著的臉、的眼,一句話也不說。
漫夭忽然有些害怕他沉默得像是不存在般的表,緩緩手去握他的手,只覺得他的手冰涼而僵。心一,那些煩的躁意退去,清楚的意識到,在這個世界,能這般輕易傷到他的,除了再無旁人。而這個世上,誰都可以說他冷酷無,唯獨沒有這個資格!
鼻子遽然一酸,突然撲到他懷里,雙手摟住他的腰,連連道:“對不起!對不起……”
宗政無憂看著無助的模樣,心頭一,緩緩垂眸,抬手上單薄的脊背,聲音低沉道:“阿漫!昭云出事,我們是有責任,但你想讓我怎麼做?一直這樣陪著、哄著、給希?那不是幫,那是害!你明白嗎?”這幾日,已經夠了!如果因昭云所到的傷害,想用他來補償,那他在眼里,了什麼?
漫夭在他懷里用力點頭,懂,都懂。微仰起臉龐,輕聲道:“可是,我們總不能就這樣不管啊!”
宗政無憂臉稍微緩和,抬手用指尖輕輕拭去眼角垂懸的淚,白的幾近明的臉龐仿佛一即碎。他既心疼又無奈地嘆道:“阿漫,我希你自私些!”人生太短暫,趁他們還在一起,就該好好珍惜相守的日子。他不允許任何人,破壞他最后的幸福。他說過,這一生,寧負天下,也絕不負!
“昭云的事你別管,給我。”
點頭,伏在他懷里,心間發。
暴風雨來臨的前夜,總是十分安靜。而這一夜的拂云關和紫翔關,沒有軍隊的練聲。
萬和大陸蒼顯一七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對于紫翔關、對于南北朝而言,這是一個特殊的日子,一個令天地變神鬼共泣的日子,它將被后世之人所記住。而那一日,為紫翔關數十萬人永遠揮之不去的夢魘,它改變了持續多日的勢均力敵的形勢對局。
這日早晨,已過辰時,天有些晦暗不明,天空黑的烏云攏聚不散,仿佛要蓋頂而來,大地承載著一片抑之氣。
南朝在拂云關的二十余萬大軍傾巢而出,帝王親臨,皇妃在側。
萬馬奔騰,塵煙四起,浩磅礴的氣勢震響了兩座城池。
天空的烏云似乎也被這氣勢所震散,出碧藍如洗的天空,澄燦灑下,照耀著年輕帝王上的金黃鎧甲,反出刺目的耀眼輝,合著他上與生俱來的王者之氣,讓人不敢仰視。而帝王旁的子一白飄揚,銀發飛舞,在飛奔的駿馬之上,玉容一片肅穆,使人不自覺打心底里升起一種油然的敬畏。
在他們前方,是七千玄鐵騎,領頭的修羅七煞面上的紅魔面在下散發著嗜一般的,映著兩旁特制的青銅戰車,紅如,青如刃。
紫翔關。
城墻高逾十丈,堅固如鐵桶。城墻上,北軍主帥聞訊率領麾下大將登城遠眺。
只見城門數十丈開外,漫天的沙塵彌漫下,一眼不到頭的鐵甲雄獅,氣勢恢弘無比。那金黃繡有“南”字的飛揚旗幟下,一眼便能看到那眾人圍繞中的一男一,皆是白發,他們高坐馬背,軀筆直,明明所地勢比這城墻低矮許多,可他們投遞來的目卻并非仰視,而是仿佛立在他人無法企及的高,低眸俯瞰大地蒼生般的表。
過塵煙,在他們上攏了一層金輝,男子盔甲芒耀目,渾散發著渾然天的王者氣勢,子白如雪銀芒刺眼,神圣不可侵犯,給人一種天神降臨討伐凡間的錯覺。他們目凌厲,越過數十萬人空直而來,讓人忍不住戰栗。
一名將軍道:“果然是南帝親臨,且拂云關南軍傾巢而出,看來南帝此次是鐵了心要拿下紫翔關!李將軍,陛下不在,這可如何是好?”
李將軍面凝重道:“傳本將令:死守城池。任何人不得擅自出城迎戰,違令者,軍法置!”
“是。”有人領命退下。
“李將軍,你看,那是什麼?像是馬車,南帝打仗還帶著這麼多馬車干什麼?”一名將軍指著南朝大軍兩側閃耀著青的馬車問道。
那馬車以青銅打造,周正四方,禿無裝飾點綴,看上去有些怪異,不像戰車也不像拉人的馬車。李將軍看后,疑地皺起眉頭。
這時,那些散著青的馬車忽然了,從大軍兩側如青龍一般直奔大軍最前方并攏,在大軍之前連一排。馬車前方有一塊擋板,一人之高,青銅實頂,刀槍不。前方正中
有一個極小的圓孔,而后方車門上則有一個小窗子,從外頭看過去,里面黑漆漆一片,誰也不知道車究竟是人是。
一名將軍疑道:“我打了這麼多年的仗,還從沒見過有頂棚的戰車!”
一名謀士拈著胡子,思索道:“這戰車是有些奇怪,整用青銅打造,看起來是好看,也堅固結實,可是車太沉,四匹馬拉著也跑不快。他們,為什麼要制造這種戰車呢?”
又一人道:“什麼戰車啊?連個站人的地方都沒有!我看吶,這就是他們準備用做打不過時逃跑用的,逃命車還差不多。”
另一人擺手道:“管它什麼戰車不戰車呢,只要我們不出城迎戰,他們什麼車也沒用……”
南軍陣營之中,宗政無憂穩坐馬背,面深沉,眼冷漠邪侫,而漫夭神淡漠,看不出表,只眼眸冷凝堅定,著對面城池,有著勢在必得的決心。見城墻上敵營將帥現,他們二人對一眼,無需言語的默契在二人之間流轉。
臨行前,他們約定好,負責破城,他負責破敵。
宗政無憂向前方排列整齊的戰車,目幽深,似有所期待。
九皇子一銀盔甲,手里拿著劍,面十分正經,看上去倒有幾分將帥模樣。他抬頭看了眼那高聳堅固的城墻,微微湊過來,有些懷疑的小聲問道:“七嫂,你確定我們不需要梯子就能攻進城去嗎?你看這城墻說也有十丈高了吧,這可是有名的難以攻破的城關啊!”
漫夭掉頭看他,微微挑眉道:“這麼高的城墻,你覺得梯子能夠得著?”
九皇子道:“那也比沒有強啊!無相子,你說是不是?”
無相子亦是一銀盔甲,俊秀面容之上那道直抵鼻梁的疤痕在大軍沖天的殺氣下為他增添了幾分凜冽的氣勢。他聞言,轉過頭來,微微笑道:“娘娘說用不著梯子,那就必然用不著。”
宗政無憂側目,掃了九皇子一眼,九皇子嘿嘿干笑了一聲,忙道:“七嫂,我不是不信你,我只是好奇,你的武到底是什麼啊?是那些馬車嗎?可是……我怎麼看不出這馬車有什麼用呢?它又不能打仗,這人要是坐進去,連敵人都看不見,還怎麼打呀?”想不明白,他怎麼看也還是覺得奇怪。偏偏七哥對此深信不疑,連問也不問一聲。
猜你喜歡
-
完結336 章

狂妃來襲:丑顏王爺我要了
殺手之王穿越而來,怎可繼續受盡屈辱!皇帝賜婚又怎樣,生父算計姨娘庶妹心狠又怎樣?淪為丑顏王爺未婚妻,她嗤笑:“夫君如此美如天仙,不知世人是被豬油蒙了眼嗎?”“女人,嫁于我之后,你還以為有能力逃離我嗎?”…
89.5萬字8 120883 -
完結905 章

空間娘子要馭夫
二十一世紀神醫門后人穿越到一個架空的年代。剛來第一天被浸豬籠……沒關系,她裝神弄鬼嚇死他們……又被打暈喂狼?沒關系,她拉下一個倒霉蛋……只是,這個倒霉蛋貌似很有性格,白天奴役她,晚上壓榨她……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五年翻身得解釋。雙寶萌娃出世…
127.8萬字8 22638 -
連載52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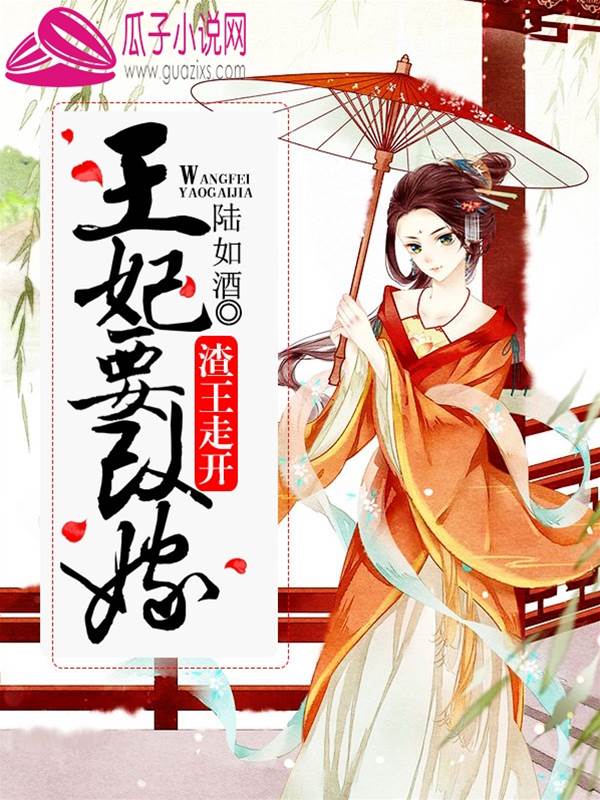
渣王走開:王妃要改嫁蘇妙妗季承翊
蘇妙,世界著名女總裁,好不容易擠出時間度個假,卻遭遇遊輪失事,一朝清醒成為了睿王府不受寵的傻王妃,頭破血流昏倒在地都沒有人管。世人皆知,相府嫡長女蘇妙妗,懦弱狹隘,除了一張臉,簡直是個毫無實處的廢物!蘇妙妗笑了:老娘天下最美!我有顏值我人性!“王妃,王爺今晚又宿在側妃那裏了!”“哦。”某人頭也不抬,清點著自己的小金庫。“王妃,您的庶妹聲稱懷了王爺的骨肉!”“知道了。”某人吹了吹新做的指甲,麵不改色。“王妃,王爺今晚宣您,已經往這邊過來啦!”“什麼!”某人大驚失色:“快,為我梳妝打扮,畫的越醜越好……”某王爺:……
99.7萬字8 12789 -
完結163 章

嫁三叔
顧長鈞發現,最近自家門口總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少年徘徊不去。一開始他以爲是政敵派來的細作。 後來,向來與他不對付的羅大將軍和昌平侯世子前後腳上門,給他作揖磕頭自稱“晚輩”,顧長鈞才恍然大悟。 原來後院住着的那個小姑娘,已經到了說親的年紀。 顧長鈞臉色黑沉,叫人喊了周鶯進來,想告誡她要安分守己別惹上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卻在見到周鶯那瞬結巴了一下。 怎麼沒人告訴他,那個小哭包什麼時候出落得這般沉魚落雁了? 周鶯自幼失怙,被顧家收養後,纔算有個避風港。她使勁學習女紅廚藝,想討得顧家上下歡心,可不知爲何,那個便宜三叔總對她不假辭色。 直到有一天,三叔突然通知她:“收拾收拾,該成親了。” 周鶯愕然。 同時,她又聽說,三叔要娶三嬸了?不知是哪個倒黴蛋,要嫁給三叔那樣凶神惡煞的人。 後來,周鶯哭着發現,那個倒黴蛋就是她自己。 單純膽小小白兔女主vs陰晴不定蛇精病男主
25.4萬字8.18 1645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